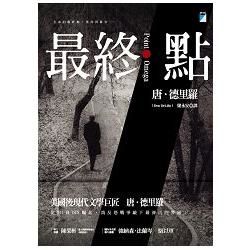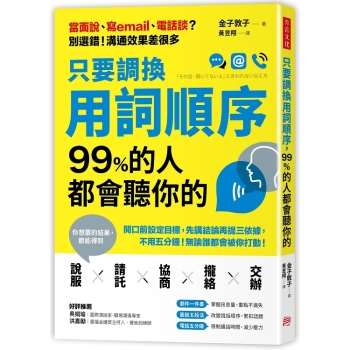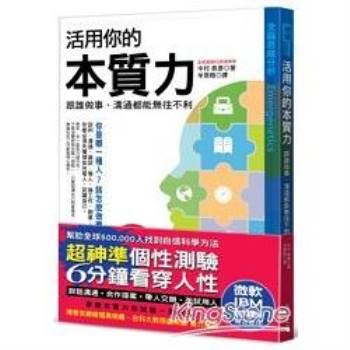生命的最終點,是回到最初……
美國後現代文學巨匠 唐.德里羅
從911到ISIS崛起,為反恐戰爭敲下最深沉的警鐘!
美國後現代文學巨匠 唐.德里羅
從911到ISIS崛起,為反恐戰爭敲下最深沉的警鐘!
「這是一部美麗的小說,是唐.德里羅最令人驚喜的作品……它穿透了死亡的迷霧,所展現的力道,遠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作家更加深刻。」──強納森.法蘭岑
他是個學者,長期受到國家政府重用,握有改變世界的機密。但在信念破滅之後,他隱居到沙漠,自我放逐。
一名年輕導演來找他,想為他拍攝紀錄片,他斷然拒絕。然而他又渴望陪伴,導演便留下來,等待說服他的時機。不久後,他心愛的獨生女也來了,卻是因為母親反對她所交往的對象,勒令她前來閉關。
他在無邊無際的荒漠,默默思索著人類存在的危機,以及哲學的「最終點」概念。直到這一天,女兒離奇失蹤,他驀然發現,什麼才是真正的「最終點」……
《最終點》為美國當代文學巨擘唐.德里羅最新作品。它直探人類理性的深淵,顛覆我們對「死亡與重生」、「消失與存在」的認知,甚至超越了其他同類主題作品的極限。
★美國文學巨擘唐.德里羅最新作品。
★與《身體藝術家》並稱為唐‧德里羅最後現代主義的小說。
名家好評
【臺大翻譯學程兼任助理教授】陳榮彬◎專文導讀。
【國內外名家】強納森‧法蘭岑,駱以軍◎強力推薦。
「《最終點》是一本故事情節極簡的小說……以電影為全書最重要的隱喻,雖然故事簡單無比,但字裡行間卻閃現了許多德里羅的思想結晶。」──陳榮彬
「唐‧德里羅是創造『慢速暴力』的大師。在寂靜的,這個運轉如常、他的故事人物和我們一樣無法改變什麼的世界,畫外音更高頻的瘋狂早已如瓷釉的細裂紋。他的小說人物和畫面總是菁英、整潔、準確、知性,但最後卻可以展演出更高高度的,現在這個世界根本秩序的黑暗之心,像孟克〈吶喊〉那樣無可救贖的絕望之臉,那必須進入到一種扇葉高轉速但突然一切恍如靜止的超人意志,才做得到。
原來一百年過去了,原來發生在極遠之域的屠殺、強暴、對恐怖的無感,在最慢速的播放中,我們只是被裹脅進一個無限延緩,每一細節都更拓印到人類驚悚承受的希區考克電影中。」──駱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