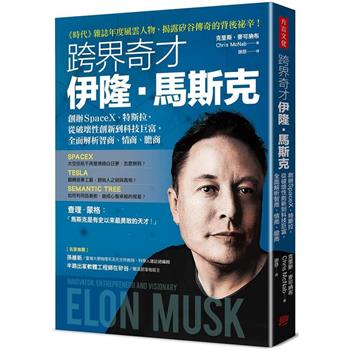我在傷害所有人。但我停不下來。
我明確的知道,這一生,我會被體內膨大的慾望或是愛給勒死。
我明確的知道,這一生,我會被體內膨大的慾望或是愛給勒死。
若非愛讓我們變成怪物,就是讓我們發現自己。
發現自己,也只是怪物而已。
★ 收錄2014時報文學獎首獎散文〈內褲‧旅行中〉。
★ 李桐豪、湯舒雯,熱辣辣專文推薦。
他寫花子,寫成貞子;寫愛寫成在鬧鬼,滿載心事的心室裡誰都在尖叫眼淚跳。
他寫旅行,其實是寫長大,一下就到路的盡頭了,卻怎樣都抵達不了自己。
他逼人承認愛與傷害的兩面性:以為愛到不可自拔,其實只是對傷害上癮。
純情又色情。歡快又哀傷。很迂迴,才命中核心,那麼髒,其實最乾淨。一會Drama Queen,一會林黛玉。極端跳TONE,完美融合,百無聊賴,全無禁忌,真怕他把什麼都寫完了。開啟散文新的可能性,新世代站出來,心很老,面如花開,所有的少年就此一夜/頁長大。
獻給這個世代愛的教養。
星星都要歸隊,添上他,這個世代的文學星圖就要完整。翻開陳栢青第一本散文集,有些人,遇到一次就夠了。有些愛,一讀再讀。有些長大,現在才要開始。
本書摘錄
「這年頭的愛情,搶的不是勝利者,是受害者。誰要聽成功的故事。愛是一個人的,但失去愛才是大家的故事。」──〈花子〉
「對花痴而言,初戀就是永恆。越遠越想追。註定得不到的,才是真的愛。」──〈花痴〉
「愛不是承諾,病才可以套牢,或是枷鎖。山盟海誓,久病成良依,相靠相依。」──〈尖叫女王〉
「我們就是會愛上跟自己完全相反的東西。所以才想要離開。所以才試圖抵達。所以才有一個地方叫做故鄉,有一個地方名為遠方。」──〈自己的模樣〉
本書重點
◆ 台灣文壇新世代最受矚目的創作者。
◆ 收錄2014年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作品〈內褲‧旅行中〉。


 2016/12/22
2016/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