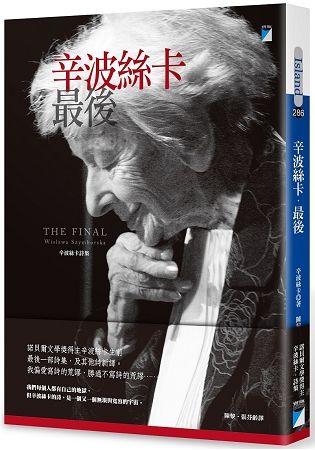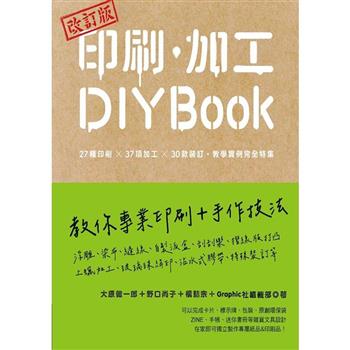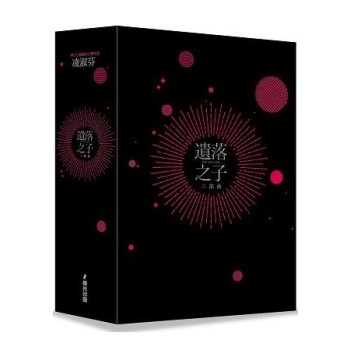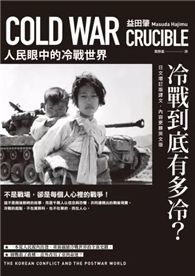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生前最後一部詩集,及其他詩新譯。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辛波絲卡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獄,
但辛波絲卡的詩,是一個又一個無垠與寬容的宇宙,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辭彙雖小,卻張著強而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
──一九九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時,辛波絲卡的得獎辭。
只要活著,我們每個人就都是從地獄歸來的倖存者。
辛波絲卡以獨特視角的敏銳喉嚨,為我們吶喊出人生承受的所有針尖。那些跌撞,瀕危,瘡孔等人生各種險灘,那些無常,死亡,時間,記憶,愛等亙古命題,辛波絲卡都以獨特的視角、清澈易讀的文字、精準的剪裁,細細織就。
但更高明的是,她讓細節成為煉火,滾燙於我們眉宇間;她不直接書寫同情與憐憫,也不輕易二分黑白,她只是在我們每個人的記憶沃土栽植新株,繁衍出一片療癒森林,一如人生將如碎屑飄落,但轉角陌生人的笑容卻讓我們暖。
對孩子而言:第一個世界末日。
對貓而言:新的男主人。
對狗而言:新的女主人。
對家具而言:樓梯,砰砰聲,卡車與運送。
對牆壁而言:畫作取下後留下的方塊。
對樓下鄰居而言:稍解生之無聊的新話題。
對車而言:如果有兩部就好了。
對小說、詩集而言——可以,你要的都拿走。
百科全書和影音器材的情況就比較糟了,
還有那本《正確拼寫指南》,裡頭
大概對兩個名字的用法略有指點——
依然用「和」連接呢
還是用句點分開。
──〈離婚〉
★本書特色:
◎2012年過世的辛波絲卡,她在人世88年,但寫出來的詩不到400首,她並不算是一位多產的詩人,因此她的每首詩都質精,耐讀且韻味深長。而此部詩集是她生前最後一部詩集,哪怕是處理死亡等令人憂傷的沉重題材,辛波絲卡在詩句間,更是充滿智慧、淡定與超然,也因此帶給讀者更多寬慰。
◎辛波絲卡堪稱是最平易近人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例如這部詩集中的〈不會發生兩次〉一詩,曾被搖滾歌手翻唱,波蘭爵士樂手Tomasz Stańko更曾與她合作,把詩變成音樂,在著名爵士廠牌ECM出版。
◎辛波絲卡也是一位能激發出更多人創作靈感的詩壇女神,例如奇士勞士基的〈紅色情深〉電影,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作者簡介:
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波蘭,一九九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給予她的授獎辭是:「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評委會稱她為「詩界莫札特」。
辛波絲卡被公認為當代最迷人、最偉大的女詩人之一。
辛波絲卡作品年表
詩集:
存活的理由(Dlatego zyjemy, 1952)
自問集(Pytania zadawane sobie, 1954)
呼喚雪人(Wolanie do Yeti, 1957)
鹽(Sl, 1962)
一百個笑聲(Sto pociech, 1967)
可能(Wszelki wypadek, 1972)
巨大的數目(Wielka liczba, 1976)
橋上的人們(Ludzie na moscie, 1986)
結束與開始(Koniec i poczatek, 1993)
瞬間(Chwila, 2002)
冒號(Dwukropek, 2005)
這裡(Tutaj, 2009)
足矣(Wystarczy, 2012)
散文集:
非強制閱讀(Lektury nadobowiazkowe, 1973)
非強制閱讀新輯(Nowe Lektury nadobowiazkowe: 1997-2002, 2002)
譯者簡介:
陳黎,一九五四年生,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二○○五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二○一二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二○一四年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二○一五年受邀參加雅典世界詩歌節,新加坡作家節及香港國際詩歌之夜。二○一六年受邀參加法國「詩人之春」。
張芬齡,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現代詩啟示錄》,與陳黎合譯有《辛波絲卡詩集》、《聶魯達雙情詩》、《死亡的十四行詩──密絲特拉兒詩選》、《達菲──世界之妻》、《拉丁美洲現代詩選》、《帕斯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小品文獎,並多次獲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
章節試閱
離婚
對孩子而言:第一個世界末日。
對貓而言:新的男主人。
對狗而言:新的女主人。
對家具而言:樓梯,砰砰聲,卡車與運送。
對牆壁而言:畫作取下後留下的方塊。
對樓下鄰居而言:稍解生之無聊的新話題。
對車而言:如果有兩部就好了。
對小說、詩集而言——可以,你要的都拿走。
百科全書和影音器材的情況就比較糟了,
還有那本《正確拼寫指南》,裡頭
大概對兩個名字的用法略有指點——
依然用「和」連接呢
還是用句點分開。
認領
你來了真好——她說,
星期四的墜機事件你聽說了嗎?
他們來看我
就是為了這事。
據說他在乘客名單上。
那又怎麼樣?說不定他改變主意。
他們給了我一些藥丸,怕我崩潰。
然後給我看一個我認不得是誰的人。
全身燒得焦黑,除了一隻手,
一塊襯衫碎片,一只手錶,一枚婚戒。
我很氣,因為那鐵定不是他。
他不會那樣對我的,以那副模樣。
那樣的襯衫店裡到處都是。
那手錶是普通款。
戒指上我們的名字
再尋常不過了。
你來了真好。坐到我身邊來。
他的確應該星期四回來。
但今年還有好多個星期四。
我會去燒壺水泡茶。
還要洗頭,接下來呢,
睡一覺忘掉這一切。
你來了真好,因為那裡好冷,
而他只躺在一個塑膠睡袋裡,
他,我指的是那個倒楣鬼。
我會燒星期四,洗茶,
我們的名字再尋常不過了——
維梅爾
只要阿姆斯特丹國家美術館畫裡
那位靜默而專注的女子
日復一日把牛奶從瓶子
倒進碗裡
這世界就不該有
世界末日。
不會發生兩次
同樣的事不會發生兩次。
因此,很遺憾的
我們未經演練便出生,
也將無機會排練死亡。
即便我們是這所世界學校裡
最魯鈍的學生,
也無法在寒暑假重修:
這門課只開授一次。
沒有任何一天會重複出現,
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夜晚,
兩個完全相同的親吻,
兩個完全相同的眼神。
昨天,我身邊有個人
大聲喊出你的名字:
我覺得彷彿一朵玫瑰
自敞開的窗口拋入。
今天,雖然你和我在一起,
我把臉轉向牆壁:
玫瑰?玫瑰是什麼樣子?
是一朵花,還是一塊石頭?
你這可惡的時間,
為什麼把不必要的恐懼摻雜進來?
你存在——所以必須消逝,
你消逝——因而變得美麗。
我們微笑著擁抱,
試著尋求共識,
雖然我們很不一樣
如同兩滴純淨的水。
離婚
對孩子而言:第一個世界末日。
對貓而言:新的男主人。
對狗而言:新的女主人。
對家具而言:樓梯,砰砰聲,卡車與運送。
對牆壁而言:畫作取下後留下的方塊。
對樓下鄰居而言:稍解生之無聊的新話題。
對車而言:如果有兩部就好了。
對小說、詩集而言——可以,你要的都拿走。
百科全書和影音器材的情況就比較糟了,
還有那本《正確拼寫指南》,裡頭
大概對兩個名字的用法略有指點——
依然用「和」連接呢
還是用句點分開。
認領
你來了真好——她說,
星期四的墜機事件你聽說了嗎?
他們來看我
就是為了這事。...
推薦序
我們在《這裡》──閱讀辛波絲卡生前最後一本詩集
陳黎‧張芬齡
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於一九九六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給予她的授獎辭是:「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評委會稱她為「詩界莫札特」,一位將語言的優雅融入「貝多芬式的憤怒」,以幽默來處理嚴肅話題的女性。她的詩作題材甚廣:大如死亡,政治或社會議題,小如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視的物品,邊緣人物,日常習慣,被遺忘的感覺。她用字精鍊,詩風明朗,沉潛之中頗具張力,她敏於觀察,往往能從獨特的角度觀照平凡事物,在簡單平易的語言中暗藏機鋒,傳遞耐人玩味的思想,以看似不經意的小隱喻為讀者開啟寬闊的想像空間,寓嚴肅於幽默、機智,堪稱以小搏大,舉重若輕的語言大師。
《這裡》一書出版於二○○九年,是辛波絲卡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詩集,收詩十九首(二○一二年問世的《足矣》收詩十三首,是死後出版之作;我們中譯的這本二○一○年由美國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公司出版的波蘭文與英譯雙語版詩集《這裡》,收詩二十七首,最後八首選自二○○五年詩集《冒號》)。雖有論者認為《這裡》一書未見驚人之作,謂讀此書似乎像重遊著名旅遊景點,未覺太多新魅力和神祕感,但絕大多數論者、讀者皆持正面評價,甚至以驚嘆語氣讚道:「為何她的詩總是越來越好?」在這本詩集裡,我們看到八十餘歲的辛波絲卡以其一貫精準、簡潔的語言,敏銳的觀察,生動的敘述方式,書寫所見所聞與所想所思。高齡詩人的想像力,幽默感和機智始終處於豐沛狀態,對世界依舊保持童真的好奇,犀利的嘲諷裡更增添幾許寬容的理解。讀這些詩,讓我們重溫辛波絲卡曾經帶給我們的驚喜與感動,的確是歡歡喜喜地到著名景點,進行了一趟內涵豐富的深度人生之旅。我們感受苦澀的人類經驗(譬如離婚,恐怖分子,認屍),我們探索夢境、回憶、微生物(有孔蟲)、迷宮、寫作靈感(點子)的本質與奧祕,我們在空間,也在時間旅行,我們見到了辛波絲卡喜歡的畫家維梅爾,黑人歌手艾拉.費玆潔拉,波蘭詩人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我們看到辛波絲卡與青少年時期的自己對望、交談,我們聽見辛波絲卡與主宰死亡的命運女神對話……。每一首詩就是一個小宇宙,只要我們和老年的辛波絲卡一樣仍然對世界充滿好奇和想像,就可以在小宇宙發現「空間寬裕,可恣意妄為」的新天地。
*
在這本詩集的第一首詩——也是標題詩——〈這裡〉,辛波絲卡發表了她居住地球多年的感言:地球有哀愁,剪刀,小提琴,感性,電晶體,水壩,玩笑和茶杯,還有其他地方缺乏的畫作,陰極映像管,餃子和拭淚用的紙巾;地球各地息息相關,許多地方彼此相鄰(「這裡有無數周圍另有地方的地方」),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卻也彼此交融成更大的群體(「將自己的孩子加入別人的孩子中」);無知的人類不斷為各種事件和現象「下結論,找原因」;人類會死亡是自然定律;幸好戰爭不是永無休止,有「中場休息」的時候,人類得以休養生息;人類可盡情做夢,因為進入夢境無須付費,幻想破滅時,才需付出傷心的代價,而向地球租用的身體就「以身體支付」,身體器官一一消耗殆盡之時,便是租賃關係結束之時;居住於自轉、公轉的地球上,如同免費搭乘行星旋轉木馬,安穩妥適,無虞風雨吹襲。在地球上居住了八十多年、經歷磨難和戰亂、看盡悲歡離合的辛波絲卡對地球毫無怨尤,反而以近乎童稚的天真想像和口吻述說居住地球的諸多好處,語帶感激和諒解。這或許是辛波絲卡熱愛生命的極致表現——情到深處無怨尤。
只要換個角度,地球上有太多美好的事物足以與其陰鬱或陰暗面抗衡,譬如一幅充滿生之氣息的賞心悅目畫作:「只要阿姆斯特丹國家美術館畫裡/那位靜默而專注的女子/日復一日把牛奶從瓶子/倒進碗裡/這世界就不該有/世界末日。」(〈維梅爾〉)。譬如對刺客或炸彈客這類危險人物的另類想像:撇開他們的職業不談,他們平常也禱告,洗腳,餵鳥,為小傷口止血,講電話,買衛生棉、眼影和花(如果是女性的話),開玩笑,喝柳橙汁,晚上不出任務時會看星空,聽輕音樂入眠,與一般人無異,也無害(〈恐怖分子〉),這樣的人為何會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其善良的人性何以向邪惡臣服,或許是辛波絲卡沒說出口的困惑。譬如一夜狂風來襲,樹葉落盡,只剩一片孤葉尚存,你不必感慨大自然趕盡殺絕的粗暴無情,該學習辛波絲卡,不僅將孤葉看成是大難過後倖存的活口,還能笑看無知的它,自得其樂在枝椏上搔首弄姿的滑稽模樣,並將此一景象解讀為暴力在人類面前展現的「小幽默」(〈例子〉〉)。譬如一心祈禱來世投胎成為白種女孩或身材苗條的黑人女歌手,殊不知她想改變的今生弱點,在上帝眼中卻是值得歡喜的「黑鬆弛劑,歌唱的圓木頭」(肥胖的身材外加黑人歌唱的天賦,讓艾拉成為療癒心靈的歌手艾拉)。我們應該感激仁慈的上帝否決了艾拉的願望,為人間的未來留下美好的音樂種子(〈艾拉在天堂〉)。
但辛波絲卡絕非天真爛漫的樂觀主義者,她對生命的本質有深切的體會。在〈迷宮〉一詩,她不厭其煩地為讀者解說迷宮的複雜設計以及破解迷宮的要領。整首詩有多處句子與句法大同小異,像是枝椏不斷岔出,抉擇無所不在,看似峰迴路轉,實則危機四伏:
一條路接一條路,
但卻沒有退路。
可以走的唯有
在你前面的路,
那兒,彷彿給你安慰,
一個彎角接一個彎角,
驚奇後還有驚奇,
景色後還有景色。
你可以選擇
在哪裡或不在哪裡,
跳過,繞道,
但不可以視而不見。
……
一座懸崖驟現,
懸崖,但有條小橋,
小橋,卻搖搖晃晃,
搖晃,但僅此一條,
因為別無他條……
迷宮,正是人生的隱喻:希望、錯誤、失敗、努力、計畫和希望會在某處交會而後分道揚鑣;人生沒有退路,因為無法重來;你可憑直覺、預感、理智、運氣做出選擇;幸福和辛苦只一步之隔,不快樂如影隨形地跟著快樂……。此詩道出了苦樂參半而苦又多於樂的人生本質,每個人都有自己專屬的迷宮,不假外求的迷宮出口。反覆讀之,發現此詩彷如一首安魂曲或連禱文,以節制——有時甚且近乎單調——的語言,讓我們在跟隨詩人遊歷其為我們打造的人生迷宮之樣本屋後,得以安心、耐心地面對、接納暗藏於迷宮角落的黑暗、困惑和狂喜。
*
對於創作者而言,「如何表達」和「表達什麼」同等重要。辛波絲卡似乎總是能自日常生活中找到出人意表的方式去呈現她的題材,傳達令人驚喜的意念。在〈離婚〉一詩,她不從當事人著手,反而從貓的、狗的、家具的、汽車的、鄰居的、等待被均分的書籍的角度切入,只在最後畫龍點睛式地觸及兩人的狀態。在〈不讀〉一詩,她嘲諷現代人幾乎都不閱讀了,一如旅行帶回的不是深刻的回憶,而是印象模糊的投影片。說話者是這個年代的典型代表,她希望像販售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書店,可隨書附贈遙控器,讓她可隨時將閱讀頻道轉換到體育或有獎徵答的娛樂節目,她甚至希望可以概述或簡化或圖解長篇鉅作,還笑稱寫那麼多冊書的人八成是因為長年臥床,行動不便,除了書寫,無事可做吧!辛波絲卡感慨:「我們的壽命變長,/精確度卻減少/句子也變得更短。」短短數語道出現代人的通病——講求速度,思想空洞,生命的長度增加,厚度與深度卻變得短小輕薄。〈在熙攘的街上想到的〉有著頑童式的幽默。她在街上看到許多臉孔,發現有些人長得像阿基米德,凱薩琳女皇,法老王,野蠻的汪達爾人,蒙特祖馬,孔子,尼布甲尼撒,賽密拉米斯等歷史人物,居然認為這是怠工的大自然為了滿足地表上數十億人口的需求所想出的偷懶方法:自遺忘的鏡子打撈沉沒已久的臉孔,「把曾經用過的臉/放到我們臉上」。於是,每當發現某些人長得像某些人時,我們便會想起這首絕妙好詩,想起此刻大自然可能正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打盹偷懶而發出會心微笑。在〈希臘雕像〉一詩,偷懶的時間反而對保存人類文化有所貢獻。通常雕像都經不起大自然(風吹日曬雨淋)的摧殘,隨著時間推移,各部位逐漸殘缺、剝離,最終化為砂礫。但詩中所提到的這尊大理石希臘雕像雖然年代久遠,日漸殘破,卻依然保有軀體,為僅餘的優雅和莊嚴而苦撐著,辛波絲卡說這得感謝時間「提早結束工作」。以此邏輯繼續推想,我們希望時間失憶,忘記尚待完成的工作,讓雕像逃過化為烏有的劫數。〈憑記憶畫出的畫像〉一詩的說話者用了三十多個問句企圖釐清這張「一切似乎吻合卻無相似之處」的畫像和真實人物究竟差異何在:姿勢?色調?穿著?場景?人際關係?生活作息?社交關係?內心想法?……這些自說自話的問題沒有任何答案,辛波絲卡用一句話破解:「那麼前景該畫什麼呢?/喔,什麼都行。/只要是一隻/剛好飛過的鳥。」即便融入所有考量,讓畫像變得更傳神,都只是模擬受限的人生,無法像隻飛鳥自由翱翔。
*
辛波絲卡擅用提問,對話,或戲劇獨白的手法切入主題,將抽象的概念具象化,生動又深刻地傳遞她想表達的訊息。譬如〈認領〉一詩以戲劇獨白的手法,講述一個女人的丈夫遭遇空難,她去認屍回來後與來訪朋友的談話。她拒絕相信那個屍肉焦黑的倒楣鬼與自己有任何關聯,一再強調那只是同名同姓的人,故作輕鬆、鎮定地說要去燒水泡茶,洗頭,然後睡一覺忘掉這件事。她找各種理由自欺欺人,自我安慰。但倒數第二行的口誤:「燒星期四,洗茶」,暴露出她內心隱忍的傷痛與焦慮不安,她拒絕承認,但心裡明白丈夫已死是難以逃避的殘酷現實。詩裡無任何悲傷的字眼,讀者卻對該女子的遭遇有著許多不捨。這種既深入又抽離的詩的張力,辛波絲卡拿捏得宜。在〈與阿特洛波斯的訪談〉一詩,辛波絲卡以輕鬆的氛圍觸及嚴肅的政治話題。她訪問命運三女神中負責剪短人類壽命紗線的阿特洛波斯(死神的分身),向她提出若干問題。在問答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人類之所以死亡人數眾多,不僅僅因為命運女神阿特洛波斯是個工作狂,還因為她在人間有許多自動自發的幫手——發動戰爭的各種獨裁者,數不清的狂熱分子。「多虧了他們,我才能跟上潮流」,暗示隨著武器的不斷精進,戰爭的死亡人數倍增。訪談最後,阿特洛波斯拒絕回答與退休相關的提問,還一派輕鬆地道別,這可讓我們一點也輕鬆不了。在〈點子〉一詩,辛波絲卡以擬人化和戲劇獨白的手法,描述寫作靈感的到訪與離去的過程。點子來找她,希望她能將之書寫成詩,而她有太多的顧慮:精練的短詩難寫,能力和才氣不足,難以完整呈現諸多特質……。最後點子只能嘆氣,消失無蹤。相信有寫作經驗的作家讀完此詩,必然會心一笑。在〈與回憶共處的艱辛時光〉,回憶被形塑成老愛舊事重提、翻舊帳而且操控慾極強的強勢女人,她逼你認錯,形同綁架地強迫你只能與她生活在上鎖的陰暗房間,你若提出分手,她會露出憐憫的微笑,因為她知道你若離開她,會飽受折磨——她已然成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辛波絲卡用這樣的關係影射籠罩於回憶陰影的人類的普遍困境:無論面對或逃離,都辛苦。
*
對於描寫的對象和想呈現的主題,辛波絲卡往往表現得若即若離,不帶強烈情緒,也不完全冷漠超然;即便深切關注,也必定巧妙地騰出距離。譬如在〈事件〉一詩,辛波絲卡以冷靜的旁觀者口吻,描述一則發生於熱帶草原即將演變成弱肉強食的血腥事件:母獅追獵羚羊,羚羊被樹根絆倒,由優勢轉居劣勢。我們接著會聯想到在「動物星球」頻道看到的羚羊被撕裂、吞噬的殘忍畫面,但辛波絲卡就此打住,話鋒一轉,要讀者不必扮演法官的角色去論斷誰是誰非,這本是大自然生態舞台上演的生活劇,所有的演出者(天空,大地,時間,羚羊,母獅,黑檀木),與透過望遠鏡觀看的人類都是無辜的。她列出若干拉丁文學名,就是刻意讓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為習以為常的事物提供新的觀點。又譬如〈離婚〉一詩,前八行以簡短的片語,明快的節奏,言簡意賅地界定離婚,但在最後幾行卻大有玄機:「還有那本《正確拼寫指南》,裡頭/大概對兩個名字的用法略有指點——/依然用『和』連接呢/還是用句點分開。」共同生活多年的兩人離婚,物質層面的東西或可瀟灑地達成某種還算公平的協議,精神層面的東西就得費心思量一番了。離婚的兩人當真從此一拍兩散(「用句點分開」),還是仍潛藏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牽絆(「依然用『和』連接」)?辛波絲卡留給讀者線索各自想像、解讀。〈公路事故〉是另一佳例。半個鐘頭前高速公路發生了一樁事故,不在現場、與發生事故者無關之人,或尚未獲得通知的親屬,繼續過著原本的生活,吃飯的吃飯,打掃的打掃,看電視的看電視,哭的哭,吵的吵,鬧的鬧……。唯一讓人聯想起車禍的或許是自車禍現場飄來的雲朵:「若有人站在窗口/望向天空,/他可能會看到自車禍現場/飄來的雲朵。/雖已碎爛零散,/對它們卻稀鬆平常。」「已碎爛零散」的雲朵,或許暗喻車禍現場肉體模糊的慘狀,或許暗喻渙散憔悴的心神狀態。無時無刻不俯瞰在地球上所上演的悲劇的雲朵,對此早已見怪不怪。比起因為無知才得以不受苦的人類,大自然「稀鬆平常」的冷靜、超然或冷漠,或許是一種值得人類羨慕的功力。
在處理死亡或憂傷的題材時,辛波絲卡很多時候是以大自然為師,以超然、抽離的眼光觀照人世。〈第二天——我們不在了〉讀來像是每日例行的氣象預報:今天天氣陰晴不定,涼爽多霧,可能放晴,但時有強風,也可能出現暴雨。在最後一節,預報員善意提醒聽眾:雖然明日豔陽高照,出門時最好還是攜帶雨具,以備不時之需。而此一提醒針對的對象竟是第二天「還活著的人」,這讓原本對標題感到納悶的我們,頓時豁然開朗:原來辛波絲卡以多變的氣候暗喻無常的人生,今日健在的我們有可能明天已不在人世。這樣的主題屢見不鮮,但以如此簡潔的語言,淡定的口吻和超然的態度處理如此嚴肅沉重的題材,是辛波絲卡的拿手絕活,一如她在其他許多作品裡所展現的。
*
此書所譯《冒號》一輯中〈事實上每一首詩〉一詩,具體而微地揭示出辛波絲卡的詩觀:
事實上每一首詩
或可稱為「瞬間」。
只要一個詞組就夠了,
以現在式,
過去式,甚至未來式;
這樣就夠了,文字所承載的
事物
會開始抖擻,發光,
飛翔,流動,
看似
固定不變
卻有著變化有致的影子;
……
如果在書寫之手下方出現,
也許,一樣名之為
某人風格的東西;
如果以白紙黑字,
或者至少在腦中,
基於嚴肅或無聊的理由,
放上問號,
且如果答之以——
冒號:
詩是留白的藝術,詩歌文字必須自身俱足,自成一格,詩人發掘問題,但不提供特定答案。詩末的未完待續(「冒號:」)可由詩人,也可由讀者,繼續書寫。
辛波絲卡在諾貝爾文學獎致詞時曾說:「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回應這句話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便開始猶豫,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屏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他們這份對自我的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的成果,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因為對世界永保感到驚嘆的好奇心,因為將作品視為有待持續修改的未成品,辛波絲卡的詩始終蘊含新意和感動,她絕對是沒有新鮮事的太陽底下,最新鮮,也永久保鮮的詩人。在她「書寫之手下方」,已確然出現一樣,讓中文世界(以及全世界)讀者驚豔的,名之為「辛波絲卡風格」的東西。
──二○一六年八月.台灣花蓮
我們在《這裡》──閱讀辛波絲卡生前最後一本詩集
陳黎‧張芬齡
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於一九九六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給予她的授獎辭是:「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評委會稱她為「詩界莫札特」,一位將語言的優雅融入「貝多芬式的憤怒」,以...
作者序
詩人與世界──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辭
辛波絲卡
據說任何演說的第一句話一向是最困難的,現在這對我已不成問題啦。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後一行——對我都是一樣的困難,因為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理當談詩。我很少談論這個話題——事實上,比任何話題都少。每次談及,總暗地裡覺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講將會十分簡短,上桌的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較容易受到包容。
當代詩人對任何事物皆是懷疑論者,甚至——或者該說尤其——對自己。他們公然坦承走上寫詩一途情非得已,彷彿對自己的身分有幾分羞愧。然而,在我們這個喧譁的時代,承認自己的缺點——至少在它們經過精美的包裝之後——比認清自己的優點容易得多,因為優點藏得較為隱密,而你自己也從未真正相信它們的價值……在填寫問卷或與陌生人聊天時——也就是說,在他們的職業不得不曝光的時候——詩人較喜歡使用籠統的名稱「作家」,或者以寫作之外所從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稱來代替「詩人」。辦事官員或公車乘客發現和自己打交道的對象是一位詩人的時候,會流露出些許懷疑或驚惶的神色。我想哲學家也許會碰到類似的反應,不過他們的處境要好些,因為他們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職業冠上學術性的頭銜。哲學教授——這樣聽起來體面多了。
但是卻沒有詩教授這樣的頭銜。這畢竟意味著詩歌不是一個需要專業研究,定期考試,附有書目和註解的理論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場合授予文憑的行業。這也意味著光看些書——即便是最精緻的詩——並不足以成為詩人。其關鍵因素在於某張蓋有官印的紙。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俄國詩壇的驕傲、諾貝爾桂冠詩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就曾經因為這類理由而被判流刑。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未獲官方授予當詩人的權利。
數年前,我有幸會見布洛斯基本人。我發現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他是唯一樂於以詩人自居的。他說出那兩個字,不但毫不勉強,相反地,還帶有幾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為他憶起了年輕時所經歷過的不人道羞辱。
在人性尊嚴未如此輕易遭受蹂躪的較幸運的國家,詩人當然渴望被出版,被閱讀,被了解,但他們絕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眾和單調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世紀的前幾十年,詩人還竭盡心力以其奢華的衣著和怪異的行徑讓我們震驚不已,但這一切只是為了對外炫耀。詩人總有關起門來,脫下斗篷、廉價飾品以及其他詩的裝備,去面對——安靜又耐心地守候他們的自我——那白皙依舊的紙張的時候,因為到頭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偉大科學家的電影版傳記相繼問世,並非偶然。越來越多野心勃勃的導演,企圖忠實地再現重要的科學發現或傑作的誕生的創造過程,而且也的確能幾分成功地刻畫出投注於科學上的心血。實驗室,各式各樣的儀器,精密的機械裝置重現眼前:這類場景或許能讓觀眾的興趣持續一陣子;充滿變數的時刻——這個經過上千次修正的實驗究竟會不會有預期的結果?——是相當戲劇化的。講述畫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頗具可看性,因為影片再現一幅名作形成的每個階段,從第一筆畫下的鉛筆線條,到最後一筆塗上的油彩。音樂則瀰漫於講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樂家耳邊響起的幾小節旋律,最後會演變成交響曲形式的成熟作品。當然,這一切都流於天真爛漫,對奇妙的心態——一般稱之為靈感——並未加以詮釋,但起碼觀眾有東西可看,有東西可聽。
而詩人是最糟糕的,他們的作品完全不適合以影像呈現。某個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發上,靜止不動地盯著牆壁或天花板看;這個人偶爾提筆寫個七行,卻又在十五分鐘之後刪掉其中一行;然後另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誰會有耐心觀賞這樣的影片?
我剛才提到了靈感。被問及何謂靈感或是否真有靈感之時,當代詩人會含糊其詞。這並非他們未曾感受過此一內在激力之喜悅,而是你很難向別人解說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幾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我也躲閃規避。不過我的答覆是:大體而言,靈感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屬特權;現在、過去和以後,靈感總會去造訪某一群人——那些自覺性選擇自己的職業並且用愛和想像力去經營工作的人。這或許包括醫師,老師,園丁——還可以列舉出上百項行業。只要他們能夠不斷地發現新的挑戰,他們的工作便是一趟永無終止的冒險。困難和挫敗絕對壓不扁他們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問會自他們解決過的問題中產生。不論靈感是什麼,它衍生自接連不斷的「我不知道」。
這樣的人並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因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們選擇這項或那項職業,不是出於熱情;生存環境才是他們選擇的依據。可厭的工作,無趣的工作,僅僅因為待遇高於他人而受到重視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厭,多無趣)——這對人類是最殘酷無情的磨難之一,而就目前情勢看來,未來似乎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因此,雖然我不認為靈感是詩人的專利,但我將他們歸類為受幸運之神眷顧的菁英團體。
儘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許存有某些疑惑。各類的拷問者、專制者、狂熱分子,以一些大聲疾呼的口號爭權奪勢的群眾煽動者——他們也喜愛他們的工作,也以富創意的熱忱去履行他們的職責。的確如此,但是他們「知道」。他們知道,而且他們認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們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為那或許會減弱他們的主張的說服力。任何知識若無法引發新的疑問,便會快速滅絕:它無法維持賴以存活所需之溫度。以古今歷史為借鏡,此一情況發展至極端時,會對社會產生致命的威脅。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詞彙雖小,卻張著強而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如果牛頓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園地面上的那些蘋果或許只像冰雹一般;他頂多彎下身子撿取,然後大快朵頤一番。我的同胞居禮夫人倘若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或許到頭來只不過在一所私立中學當化學老師,教導那些家世良好的年輕仕女,以這一份也稱得上尊貴的職業終老。但是她不斷地說「我不知道」,這幾個字將她——不只一次,而是兩度——帶到了斯德哥爾摩,在這兒,不斷追尋的不安靈魂不時獲頒諾貝爾獎。
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回應這句話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便開始猶豫,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摒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他們這份對自我的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成果,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
有些時候,我會夢想自己置身於不可能實現的處境,譬如說,我會厚顏地想像自己有幸與那位對人類徒然的努力發出動人噫嘆的《舊約‧傳道書》的作者談天。我會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躬,因為他畢竟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至少對我而言。然後我會抓住他的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你是這麼寫的,傳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誕生於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你所創作的詩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無人寫過。你所有的讀者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的人無法閱讀到你的詩。你現在坐在絲柏樹下,而這絲柏自開天闢地以來並無成長,它是藉由和你的絲柏類似但非一模一樣的絲柏而成形的。傳道者,我還想問你目前打算從事哪些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將你表達過的思想做進一步的補充?還是駁斥其中的一些論點?你曾在早期的作品裡提到『喜悅』的觀點——它稍縱即逝,怎麼辦?說不定你會寫些有關喜悅的『太陽底下的新鮮』詩?你做筆記嗎?打草稿嗎?我不相信你會說:『我已寫下一切,再也沒有任何需要補充的了。』這樣的話,世上沒有一個詩人說得出口,像你這樣偉大的詩人更是絕不會如此說的。」
世界——無論我們怎麼想,當我們被它的浩瀚和我們自己的無能所驚嚇,或者被它對個體——人類、動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所激憤(我們何以確定植物不覺得疼痛);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為行星環繞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蒼(我們剛剛著手探測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舊死沉?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座我們擁有預售票的無限寬廣的劇院(壽命短得可笑的門票,以兩個武斷的日期為界限);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但「令人驚異」是一個暗藏邏輯陷阱的性質形容詞。畢竟,令我們驚異的事物背離了某些眾所皆知且舉世公認的常模,背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明顯事理。而問題是:此類顯而易見的世界並不存在。我們的訝異不假外求,並非建立在與其他事物的比較上。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個字詞的日常言談中,我們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軌」之類的語彙……但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裡,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個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雲;任何一個白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看來艱鉅的任務總是找上詩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日於斯德哥爾摩
詩人與世界──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辭
辛波絲卡
據說任何演說的第一句話一向是最困難的,現在這對我已不成問題啦。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後一行——對我都是一樣的困難,因為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理當談詩。我很少談論這個話題——事實上,比任何話題都少。每次談及,總暗地裡覺得...
目錄
這裡(2009)
這裡14
在熙攘的街上想到的19
點子23
少女26
與回憶共處的艱辛時光30
小宇宙33
有孔蟲37
旅行前39
離婚41
恐怖份子42
例子44
認領45
不讀47
憑記憶畫出的畫像50
夢54
驛馬車上58
艾拉在天堂62
維梅爾64
形上學65
冒號(2005)
缺席68
公路事故71
第二天——我們不在了73
事件75
與阿特洛波斯的訪談78
希臘雕像84
迷宮87
事實上每一首詩92
瞬間(2002)
話筒98
回想100
初戀102
小談靈魂104
結束與開始(1993)
悲哀的計算110
無人公寓裡的貓114
橋上的人們(1986)
奇蹟市集118
巨大的數目(1976)
老歌手124
讚美自我貶抑125
烏托邦127
可能(1972)
復活者走動了132
一群人的快照134
從容的快板137
幸福的愛情140
一百個笑聲(1967)
火車站144
砍頭148
來自醫院的報告151
眼鏡猴153
鹽(1962)
健美比賽158
詩歌朗讀160
水162
呼喚雪人(1957)
不會發生兩次168
坦露171
紀念174
致友人177
清晨四點180
自問集(1954)
戀人們184
未出版作品(1944-1948)
走出電影院188
滑稽的情詩190
足矣(2012死後出版詩集)
在機場194
手195
鏡子196
給我的詩的詩198
【附錄一】我們在《這裡》──閱讀辛波絲卡生前最後一本詩集/陳黎‧張芳齡200
【附錄二】詩人與世界──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辭/辛波絲卡214
辛波絲卡作品年表221
這裡(2009)
這裡14
在熙攘的街上想到的19
點子23
少女26
與回憶共處的艱辛時光30
小宇宙33
有孔蟲37
旅行前39
離婚41
恐怖份子42
例子44
認領45
不讀47
憑記憶畫出的畫像50
夢54
驛馬車上58
艾拉在天堂62
維梅爾64
形上學65
冒號(2005)
缺席68
公路事故71
第二天——我們不在了73
事件75
與阿特洛波斯的訪談78
希臘雕像84
迷宮87
事實上每一首詩92
瞬間(2002)
話筒98
回想100
初戀102
小談靈魂104
結束與開始(1993)
悲哀的計算110
無人公寓裡的貓114
橋上的人們(1986)
奇蹟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