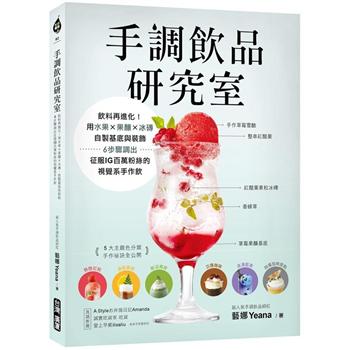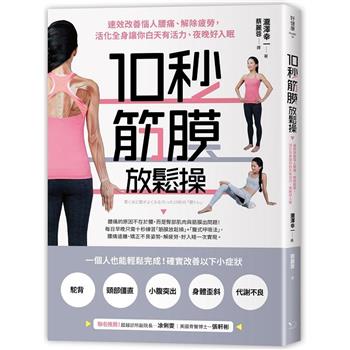推薦序
超感覺的異物志
李蘋芬(詩人,政大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一
張詩勤是我輩寫作者中格外殊異的品類。其詩恐怖,詩中的人非人,物皆變態,語言看似潑灑,任意流蕩,實則張弛有度,一首詩有多層次反轉。
《森森》的出現,為怪物詩學召來利刃、手槍、控制面板。人坐在那裡,平白無故的自體燃燒,和肉身一同焦黑得發亮的椅子,遂成為詩的起始。設想死亡並親近之,是詩人書寫的核心,生死本為大命題,因過度談論而反覆熟爛,談生不容易,但以藝術來預演死又太輕易。即使如此,〈活兆〉仍位居此大題的前鋒:
那一次那麼袒裸
結果多麼好
在潮濕的植物與泥土氣味中
也沒有承認
結果多麼好
不,我是承認了
羅曼史的送葬
你的死狀,有點像機械
讓我操作
反覆實驗
以藝術把玩死(詩集中有以下相關詞語:死胎、死意、生死、死亡電波),是為了超越表象,為了清醒認識人們所迴避的。從「沒有承認」、到「我是承認了」,指出羅曼史的消亡:透過反覆想像「你」的死亡,我明白了,心滿意足地看著「你」變形為非人的東西,正是世上最好的事。這告白何其裸露。
二
開篇的〈那裡〉寫著:「『死在這裡』像是我的絕望/也像你的決心」,預示這將是一部在死灰中被拋擲而生的書。
張詩勤詩中的肉身,若非離析,就是奇形異狀的扭曲。當你以為這樣的詩形似伊藤潤二直指人心的恐懼,那其實是浦澤直樹,人與怪物與機器之間的界線漸趨模糊。翻過一頁,閃神間卻置身在安部公房的超現實異境。
解詩的人走入魔障,痛而且舒服,窺見這森森異物有一具田村隆一的靈魂。如其〈四千之日和夜〉:「為了產生一首詩/我們必須殺死/殺死很多東西」(陳千武譯),這位戰後詩人將恐怖看作偉大的動機,恐怖即是「不安」,原動力來自慾望,使人對世界勃然大怒,也因憂歡而歌唱。這份「恐怖」,不妨作為閱讀《森森》的一個視點,窺看充沛的死意、強悍的殺意如何出沒其中。
大量迴行與高度象徵,都讓這些句子不易切分出奪人眼球的小段落,整部詩集就是一座蒐集人類慾望的聚合體。如此難以歸類,不就是詩人有意設計的機關嗎?也印證了她宣告的自我博物化:「搜集而非被搜集,示現而非被看。」《森森》更比前作多出一份臟器外露的灼熱誠意,如〈瀕幽體驗〉寫外星人來接「我」的時候:「參觀不可見的內部/也打開我的內部」,打開自己的內部,意味著抵抗被展覽,奪取「主動被看」的位置。
三
許多詩句的推衍看似即興,即興之極致,竟能成瘋成魔。為了達到任意、暢快且可讀的即興,需要仰賴詩人對語言(作為一種機器)的高度精熟、思維之通透與抗俗。如長詩〈馴化種〉:
真正的空洞在凝視我時
找到一種遠端遙控的手法
我在與空洞拔河時
學習操縱清醒夢的技術
我們都透過一片設計複雜的面板
組織自己的負片
我想我懂得它
它懂我想著它
我們才是那種真正的傳送
憑藉思維的運作,詩人的荒謬劇場以身體的虛像來搬演,並以此虛像辯詰真實。
本真性是一場幻術嗎,肉體我與精神我何者為真?網路與現實,可見與不可見。詩中隱含這樣的問題:電波傳送原初場景裡的「痛的概念」,設若它為假,那麼精神上所感到的「空洞」就足以為真嗎?或者,電波是一種對精神的模擬,最寬泛意義上的賽博格。
詩這樣結尾:「捏碎它捏碎我的意識讓它們在雨中溶解/丁點不剩像從來不在」,人非人,物已變態。彷彿重回一九八二年《銀翼殺手》的雨中獨白,大雨不能毀滅意志,無論意志的原初是何處。
四
不只是關於死。
張詩勤憶及童年讀物《寰宇蒐奇》,一九九○年代的盜版,卻無礙其真實的(偽)怪物盛典,那麼弔詭,如〈受造〉裡寫非人的認同:「相簿裡迥異的物種/臉盆裡的鰻魚或泥鰍/我的確出現過/不是人類的心安不在場的自在/被象徵被寫下來」;〈前一刻〉中存在主義式的拒斥感:「發現自己是完整的人的震驚與不適」。
我想起自己兒時的某階段,也曾被《寰宇蒐奇》餵養長大,太過熱心地參與這場既受控又失控的九○年代嘉年華(在相片中徒增兩雙手的孩童。暴死的親人還魂於隔壁的隔壁城鎮。人與獸的重組)。
現在我們可以這麼說了嗎?蒐奇使我們成為詩人。透過詩而能自白,原來人之所以迷戀恐怖,是出於對自身稍不留神就成為怪物的想像(以及期待)。
詩這一文類適合切分個體的經驗,搜羅事件與時間的碎片,予以重塑,使之逸離普通狀態,超出原本經驗,一如〈薄瓷〉所寫:「他卻仍在承接我盛裝我/仍在不自覺噴湧/我感到沒有終點/那觸感超出經驗」。肉塊上的死灰復生,電波與流彈擠滿荒野,詩人為個人的感覺史歸檔,儘管它早已超出五官的感覺。
後記
森森然寰宇/予蒐奇
一
我一直記得那本童年讀物叫做《寰宇蒐奇》。實際翻箱倒櫃的結果,確認其中一本叫做《瀛寰探秘:世界大蒐奇》,另一本則叫做《寰宇蒐奇叢書:世界之謎》,都是九○年代出版的。據說這類書風行的起點是一九七八年香港讀者文摘出版的《瀛寰搜奇》。雖然從書名可以感受到後出者的致敬之意,但內容卻只有刻意放大和誇張化那些怪力亂神的部分。對不到十歲的我來說,這種書籍就是我的「世界」。總有一天我會與植物溝通、培養出超能力、見到幽浮和外星人,因持有來路不明的鑽石而受到詛咒、掉進時空亂流或誤闖百慕達三角洲……
如此森羅萬象,既恐怖又迷人。我相信小孩子看這種書、聚在一起講鬼故事、玩錢仙、跑到鬼屋或廢墟夜遊、爬高、玩火……出自的不過是人類原初的好奇心。冒險遂得以發現──這是一個多麼傲慢的概念,足以對應人類的歷史。將好不容易發現到的奇異事物集合在一起,開一場博覽會吧。《寰宇蒐奇》幾乎是這種帝國式意圖的重現。
二
《寰宇蒐奇》的迷人在於它奇異但是遙遠;恐怖則在於,對於孩子而言,書中恐怖照片裡的鬼臉就跟它實際存在於「現場」是一樣的。這本書的存在就等於不應存在於此處的恐怖事物的現形。於是,放置這本書的書架周圍、表情似笑非笑的日本娃娃周圍、不知道誰送的南洋珍禽異獸的模型或標本周圍,都成為了最為陰森、令人不敢靠近的角落。
我無法說明恐懼的原因。甚至說不出到底在害怕什麼。就算長大成人了也一樣。每當我想說明我看見了什麼、我遇到的都是些什麼,卻只能想到幽浮(不明飛行物體)或外星人(地球外生命體)這類其實沒真正解釋到的稱呼。原來這是一個先備的預言,被預習的恐懼。到底是因為擁有如此本質才對這樣的讀物興味盎然,還是因為讀了這種書而走向一條像是被決定的道路?
三
再怎麼搜羅都沒辦法涵蓋所有的「奇異」。因為只要「正常」的標準增加一個,之外的東西就都成了「奇異」。人是處在自以為正常的位置才能將那一切當作有趣的事看待。若自己就是被登載在《寰宇蒐奇》上的照片中的主角。若自己就是當事者、成為那個怪誕的中心、被眾人注視的怪物,被蒐集、被恐懼、被當作獵奇的對象、被廉價地同情、被編為圖鑑的一部分。我沒想過自己會面臨這種更龐大的恐懼。
感受出自內部和來自外界的目光的照射,一再複習當別人露出不可思議之情時的正確反應。原來我版本的寰「予」蒐奇是,將自己的奇異暴露以後,尚必須持續將自我對象化這件事。我害怕被注視。被恣意想像地注視。樂在其中地被注視。將自己形塑為珍奇事物一般地被注視。我感到心虛。不是不誠實,而是無法一致。私底下可以弄彎湯匙,眾目睽睽之下卻做不到──這是我最大的惡夢。
四
被收錄在《寰宇蒐奇》中的日本人魚木乃伊,最近被發現是江戶時代的人工偽造物。對此衝擊性的消息,長年供養人魚的寺院住持說:「這個『人魚木乃伊』有著各種不同人們的意念寄宿其中。這些意念今後將持續存在,所以我也將繼續守護傳承這個『木乃伊』。」
他竟然沒有感到受騙,沒有感到世界崩毀。
原來可以這樣。森森繁茂而眾多,陰寒而使人戰慄。它們就只是存在著。因被賦予意念而存在,因意念的存在而存在。那是所有無以名狀事物的綜合體,是人類犯難與犯錯的投射。若離開蒐奇的意圖,剝開其恐怖與迷人的外殼,一切與我並無分別。恐懼與迷戀是斷絕,全盤接納是連通。對象化與指認是斷絕,存而不論是連通。
話雖如此,我還是感覺遭受背叛。一邊與自己的這種心境對抗同時,反覆著斷絕與連通,一邊完成了這本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