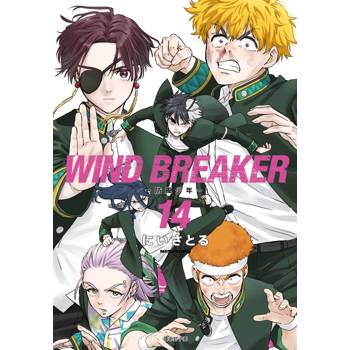台灣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與隨行紀錄雪羊在世界第七高峰的踏勘冒險紀實。
台灣登山運動在「八千米高峰」的歷史性突破。
無氧、無雪巴,全然未知的高峰雪坡與岩壁──
台灣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
與隨行紀錄雪羊在世界第七高峰的踏勘冒險紀實。
▍台灣登山運動在「八千米高峰」的歷史性突破。 ▍
▍這裡沒有任何人類定義的路線,沒有痕跡可循。
▍這是道拉吉里西北稜這面山壁開天闢地以來,
▍第二次有人類如此親近它。
時速50公里的風吹雪,近8,000公尺的稀薄氧氣,
隨時轟然襲擊的雪崩,險些一氧化碳中毒的驚心一瞬……
這是世界級的極限挑戰,貨真價實的俄羅斯輪盤,
每一步,都是自己的思考、個人的判斷。
2023年3月,雪羊擔任橘子關懷基金會「大夢計劃|前進十四峰」的隨行紀錄者,跟著台灣探險家、8,000米無氧攀登第一人呂忠翰及攀登好手張元植,一同前往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
兩位台灣登山家跳脫「傳統路線」,以及嚮導、雪巴隨行協助開路與背負行囊的「商業攀登」,是台灣人首度嘗試在8,000公尺高峰上自主攀登,建立自己的營地,一步步攀登、架繩、探勘,探索未曾被完整開發的新路線。
這是趟長達兩個月的冒險之旅。高峰冰河上的壯闊、恐懼與驚險,登不登頂的兩難抉擇,一切未知與已知的衝擊,當代登山文化與冒險價值的觀察反思,一一在雪羊的文字、影像中真誠再現。
道拉吉里西北稜的山壁上,從此增添一條由台灣人所開闢、世上再無其他人類走過看過的新路段。
//
我們花了三個小時,才把從基地營遠眺,看起來比半片指甲還小的黑色色塊,放大成高聳城牆下的一堵玄鐵巨門。視線左側是一面從天空垂下的帷幕,那是一道拒絕冰雪停留的石壁,峭絕得令人膽寒。
當我抬頭仰望,所有的岩石不斷往天空延伸,左側、右側與正前方的線條,最後全都匯聚到最靠近天空的那個點,在流動的白雲下閃閃發光。我知道那只是視野的極限,而非山體的盡頭。
黝黑的前進基地營石壁就在眼前,而道拉吉里也逐漸成為一堵高聳巨牆……
★ 各界推薦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劉柏園|橘子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專文作序
呂忠翰|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張元植|登山家
──極限推薦
三條魚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作者
伍元和|台灣山徑古道協會理事長
周 青|中華民國越野跑協會理事長
麥覺明|山岳紀錄片導演
崔祖錫|登山旅遊探險作家
陳彥博|極地超級馬拉松運動員
陳德政|作家
劉克襄|作家
謝旺霖|作家
──一致好評
(依姓氏筆劃序排列)
這本書出版的前夕,故事主角之一的元植在法國白朗峰山區攀登時墜落,突然離開了世界。我在前幾年就曾聽他津津有味地描述西北脊未登路線的可能性,眼裡閃耀著光芒,讀著眼前的書頁,我試著進入他們當時的靈魂裡,讓道拉吉里的風把我灌飽(或擊潰),或許這樣,才能驅散那無處不在、宛若一道漫長山谷般、不斷綿延、新生的哀傷。
但讀者們可不必如此,這本書飽滿的是樂觀的勇氣,就像「暴風雪裡滿天的星星」(滅火器大正語),帶著一本,上路吧!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當參與更多遠征,將發現台灣登山者與世界的差距難以置信。畢竟台灣缺乏冰雪環境訓練,丁點經驗累積都不易,冒險精神亦缺乏社會支持。至今台灣登山者在各國高峰的探索才剛萌芽罷了。
我支持跨出舒適圈探索的勇者們,引以為榮卻也深感擔憂,只因深知其中困難。無氧、自助背負裝備、設立高地營……這些條件在一般傳統路線就已經足夠辛苦且高風險了,而他們竟還嘗試新路線!我可以想像那種未知引燃探索的渴望,可能的困難撩起挑戰的熱血,而他們剛好有那份勇氣,這冒險故事因此展開。
無法言說,只能羨慕忌妒。下次帶上我,好嗎?
──三條魚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作者)
我們就像一隻渴望自由的鳥,在名為「人生」的束縛之中努力掙扎;登山者用雙腳畫出了自己心中的藍圖,在失敗與挫折中體會了自由(生命)的真諦。
──周青(中華民國越野跑協會理事長)
從青空下西北稜路線的攀登與探索,到傳統路線上,國際登山者焦躁不安的會議,再到第二營以上對無比壯美安娜普納山群的凝視……雪羊用他細膩且生動的文筆,記錄了2023年在道拉吉里那兩個月的精彩歷程與體驗。
在攻頂執著與冒險精神的選擇與辯證間,更將視界提升到生命層次。原來人生價值的探索不僅在那遙遠的、艱困的苦寒之地,也同樣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崔祖錫(登山旅遊探險作家)
作者簡介:
雪羊(黃鈺翔)
台大森林系學士,台大新聞所碩士畢。2015年開始經營「雪羊視界」Facebook粉絲專頁,至今(2024年)有超過15萬名追蹤者,是台灣最知名的山岳攝影師暨作家之一。從2013年首次登上玉山開始,登山超過十年,完登台灣百岳,更走過許多中級山與海外高峰;長期關注山林政策,致力山野教育,也常為山岳議題發聲。
期許自己成為一位稱職的山岳報導者,建立台灣人與自然的連結,壯大守護山林的行列。
2023年參與橘子關懷基金會「大夢計劃|前進十四峰」,前往位於尼泊爾的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擔任隨行紀錄者。
中央山脈最速挑戰紀錄片電影《赤心巔峰》編劇,著有《記憶砌成的石階》。
章節試閱
【第六章.節錄】
▍意料之外的鬧鐘
2023年5月21日,凌晨3:42
尼泊爾,道拉吉里峰第三營,海拔7,250公尺
[…]「羊羊!」聲音再度出現,那是元植的嗓音,我這才發現不是夢,從半夢半醒之中馬上坐起來喊了回去,看了看手錶,心情頓時警戒了起來:「快四點而已,天還沒亮,顯然是撤退了,上面發生什麼事了嗎?!」我思忖著,外頭除了風聲以外多了「嚓、嚓」的冰爪行走聲,還有鉤環在吊帶上的叮叮噹噹,這很明顯是撤退了,而且聽腳步似乎只有他一個人。
「滋──」一聲,我拉開內帳,把頭探出去。外面正飄著小雪,元植黃藍交錯的身影映入眼簾。「恭迎大大回鑾!趕快進來!」我用媽祖遶境結束,要回到自己廟宇時的用詞,打趣迎接歸來的元植。
「欸,不好意思吵醒你們了!呼,我喘一下!」
元植噗唰一聲跌進帳篷,靠在我的腳上,撥著身上的殘雪,第一句話竟然是不好意思,可見他的狀態其實還不錯,讓我又更疑惑他怎麼會回來。僅僅隔了不到十二小時,我和元植的角色就完全對調,我忽然能體會當時他們聽到我的聲音時,內心有多麼開心與放心。
「我的眼角膜好像被冰晶給刮傷了,左眼視力剩一半。」「一半?!天啊!那要不要叫直升機?」「不用!我剛剛靠著一隻右眼衝下來,我超屌的!」元植得意地說著,精神非常好,心情卻很悶。
原來入夜後的天氣真的愈來愈差,不只帳篷被吹得啪嗒作響,通往峰頂的路更是勁風飛雪,氣流刮起雪沙冰晶,不斷打在攀登者的身上、臉上,還有元植沒戴眼鏡的眼睛上。起初以為只是睫毛結冰看不到,殊不知想辦法把掛在睫毛上的冰霜解凍後依然看不太到,他就知道事情大條了,馬上掉頭撤退。
在7,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眼睛有可能因為風雪或缺氧的關係而暫時喪失視力,最經典的故事莫過於《凍》一書所描述,山野井夫婦從格仲康峰撤退時,山野井泰史後來近乎失明的可怕過程。
「啊這個會好嗎?」「會啦,只是暫時的,不用擔心。」元植一派輕鬆地說著,但話鋒一轉,開始各種粗口:「幹,我狀態真的超好欸,跟著阿果一路衝衝衝,都到7,700公尺了吧!但那個風真的太大了,上面風速至少五十(公里)以上,然後那個雪一直被刮起來……因為都有固定繩,阿果就繼續戰,我先回來了。」
「那其他人呢?」我問。「也都下來了。」我感到不可思議,今晚在山頂等待眾人的,竟是如此惡劣的天候。
吸氧的攀登者們在海拔7,500公尺左右全因風太大而撤退,只剩阿果一個無氧攀登者繼續對抗強風,獨自咬牙向上。整個道拉吉里山頂地帶只剩下阿果一人還在奮戰,這實在太魔幻、太強大了。
聽完元植的前線匯報,我不禁倒抽一口氣,更加佩服阿果過人的勇氣與體能,也由衷祈禱他平安、成功。
元植的歸來雖然帶著一絲絲遺憾,也讓帳篷更為擁擠,但更多的是溫暖與喜悅。此刻他喝完水,正安詳地在我身旁打盹,身體也很完整,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事了。
「欸元植,你的睡袋不暖欸,我和拉卡帕晚上一直從腳底被冷醒。」睡前,我和元植說我睡不好。「喔,那個正常啦!你這是缺氧、血液循環不良的冰冷,蓋再多東西也不會暖。」元植打了個呵欠,眼睛半瞇,見怪不怪地說。不過這一次,我就沒有再被冷醒,一路睡到日出,睡到帳篷被加熱得暖烘烘,直到帳外再次出現獨特的中文嗓音。
元植的視力一直到這天晚上才恢復。回台灣跟我們的野外急救教練蔡奕緯討論後,我們才比較確定這是急性青光眼的可能:有青光眼病史的元植,因為衝頂時壓破了一瓶藥水,所以只有使用平常的一半劑量。
「喔—!」「欸—!」「阿果!你回來了!」
帳外的呼喊,把淺淺睡著的我們喚醒,抖擻的嗓音顯示阿果的狀態很好。然而我看了一下手錶,心裡又是一沉—8:40,這不是撤退了嗎?!我頓時有點沮喪。
「元植,你的眼睛還好嗎?」
「還好,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壞。」
「嗯。」
回到第三營的阿果沒有馬上進帳篷,而是坐在外頭曬著溫暖的太陽,隔著薄薄的帳幕,和我們一來一往聊著。第三次遠征道拉吉里,山神依然不給他登頂,甚至一個人獨自在死亡禁區戰到最後一刻,這時阿果的心情,應該十分微妙吧?
「我在暴風雪裡待了兩個小時,幹,差點軟掉。」和冰雪鏖戰到將近天亮時,阿果已經接近山頂了,但一回頭才驚覺,原來所有人都沒來,只剩他孤身一人。「我衝到7,900,他們架繩結束那個地方,整個White out(遮天蔽日的雪霧讓全方位視野一片白,無法分辨方向),那個雪煙一直吹、一直吹。」
元植毫不意外地喊:「整個晚上都是那個樣子啊!」我在旁邊聽著,心想如果當時我跟著上去,是不是即將面對這輩子最嚴酷的天候考驗?風吹雪的經驗我有過不少,但時速50公里的風吹雪,再加上近8,000公尺的稀薄氧氣,還有分不清東西南北的White out,光想就令人頭皮發麻。
「然後我就衝上去,想說就拚一波了,看看早上會不會雲開、風變小──結果沒有!衝了一個小時,還是都是霧。」
那時,距離山頂只剩下200多公尺,除了不理想的天氣外,世界第七高峰已是唾手可得。對於阿果這樣有實力的老練登山家而言,拚一把衝上去的誘惑非常大,畢竟在那裡放棄,就代表未來還得回來爬第四次,才能完成完整的十四座8,000米,背後代價是一個半月的時間與好幾十萬的支出,非同小可。
「我就想說,幹,我是真的很想要衝上去啦,但因為White out,我就怕我回不來這樣。後來七點多之後雲才散掉,但風就很強、沒有再停了。」
阿果共在接近8,000公尺的暴風雪中等了三個小時,最終也接受了自己的判斷,與天氣和解、放棄了。畢竟硬拚上去雖然有機會成功,但代價很可能是在White out中迷失方向,或者是因為風速太強再次凍傷,失去身體的某個部位。阿果自從前一年在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因為超越自己的極限而凍傷後,就變得更加謹慎。
比起所謂「成功」,在道拉吉里傳統路這條每年人來人往的稜脈上,生命與身體,無疑是更重要的事。不過阿果終究是個有血有肉的人,他還是有點惋惜,如果當時吸氧的隊伍有跟著他一起拚,在前面輪流開路、破開堆積的鬆雪並確保方向,那他就很有機會帶著大家拚一波登頂。無氧又要一個人在鬆雪與強風中開路、判位,這個體能消耗實在太大,風險太高了。
「就很心碎而已,大家沒有上來。一個人一路幹上去,然後有些地方又是深雪,又要拉繩,唉。」他說完便打開前庭,坐了進來,接受我和元植的擁抱與喝采。
平安是福。在山的面前,我們都必須衡量「冒險」的重量,是否足以將不可逆的代價放上那名為「成功」的天秤──無論那是錢、時間、身體,還是生命。
▍偉大的冒險、冒險的平凡
2023年5月21日,晚上6:45
尼泊爾,道拉吉里基地營,海拔4,670公尺
自1950年6月3日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納被法國人首登以來,世上的登山家們前仆後繼地將十四座8,000米頂峰視作生命的終極意義、挑戰的最高殿堂。直到1964年,中國的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馬被登頂後,「山頂」本身的意義在高峰攀登的領域中,就不再代表著未知的朦朧美與值得被追求的創新榮耀,而是一個「有人去過、有固定路線可循」的傳統路線,一個可以「拜訪」而非「賭命冒險」的地方。
然而崇尚自由的登山家們,不屑已知、討厭框架,嚮往未知、渴望自由。唯有踏足那些尚未被人類開拓過的角落,才能撇除一切雜訊,以純粹的有機生命體與無機的山對話,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路,不被任何他人所拘束、限制、揭露、指揮,單純以肉體在山稜與山壁上,繪出一道道充滿生命力的美麗創作。唯有未知,才是真正的自由,才能有無限多的選擇。
在道拉吉里的冰河上,我看見悉數已知的世界猶如監獄的禁閉室,沒有任何未知事物、沒有任何變化,最後,被關進去的人,將會先從靈魂開始窒息,意識與自我慢慢融化,最終成為重複著固定動作的無機物。
在任何傳統路上,以生命為賭注力拚淺薄的「成功」,已非國際登山圈的主流價值,因為登山的典範早已轉移至岩壁的攀登與新路線的開拓,和我在冰河上感受到的一樣,終極價值正是「未知的追尋」。在基地營的日子裡,我親眼見證了何謂「登山家」,又何為「登山客」,我們是在這冰天雪地裡追逐一個超級集郵行動,又或是設法在雪巴人架好的繩子以外,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攀登價值,自由地在冰雪間揮灑自己的想法、開拓自己甚至台灣人的眼界?
在阿果身上,我看見了和我相同的天秤:在道拉吉里的傳統路上,如果不能走出新的價值,那麼一步都是多餘。一如阿果帶領的「沒有台灣人完成過無氧十四峰」,以及我的新嘗試「用最好的影像記錄高峰攀登」。然而在生命面前,這一切也顯得微不足道了:這早已有人完成的峰頂、幾百人重複過的路線,不值得我們賭上生死。無論時間與金錢的代價再大,一旦遭遇險阻,我們都會選擇下次再來。
大山無情,無論擁有再強的身體與能力,身為生物的我們,在山的面前依然是那麼渺小、那麼必須屈服。
阿果回來第三營後不到一小時,我們就打包完成,沿著緊繃且被磨出許多毛邊的白絞繩垂降下撤了。直到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手腳並用、背著重裝掙扎爬上的冰坡,竟然是陡到會腳底發癢、任何東西掉到地上都會一路滑到山下的程度。若不是有固定繩可以面向山頂半垂降下山,我面對的,將不只是內心的恐懼,更有一個沒踩好就直接墜落2,500公尺的巨大風險。我吞了吞口水,對於上來開路架繩的雪巴人感到更加敬佩。
九個半小時後,我們終於從海拔7,250公尺的第三營,回到相對溫暖舒適、有著滿滿回憶的道拉吉里基地營,海拔4,670公尺。雖然阿果、元植因為狀態絕佳,一路上都在討論要不要過兩天再上去拚一把,但對於已無氧氣瓶的我而言,人生第一次的8,000米攀登,到這裡就告一段落了。
沒登頂雖然很可惜,但我已十分滿足,不僅幸運地全身而退,還帶回無比豐盛的故事──那些等待的日子,與各國攀登者的互動,還有新舊路線的對比。在基地營等直升機下山時,阿果和我們分享了一段話,確認了我對冒險一詞的認知:「任何探索未知的行動,都可以定義為冒險。」這也正是我在道拉吉里每一天的寫照。
[…]那些以身體經歷的種種,與冰川、與雪巴、與道拉吉里、與阿果和元植為伍的日子,已用各種型態刻在我的靈魂之中,無論什麼時候拿出來,都不會褪色,都能找到令我成長的啟發。這是遠比「山頂」更珍貴的寶藏,這就是冒險所給予的自由;再平凡的冒險,哪怕像是第一次走路上學的孩子,都能獲得同等的自由。
冒險可以很偉大,像巴特克的滑降道拉吉里,像阿果和馬素的無氧攀登十四峰;也可以很平凡,走在傳統路上來趟突破自己的冒險,做沒做過的事,走沒走過的路。無論是否能為他人、為世界帶來新意,但對願意冒險的人而言,他自己的內心世界,肯定一次又一次因冒險而擴大,生命也被一個又一個的小夢引領著前進。
那是一個勇敢尋找自己的「未知」的過程,讓生命得以往前,讓意識得以延續。當一個人克服萬難去逼近夢想時,無論事大事小,在達成的那一刻,身體便會記住那個體感,暢快、感動、自信、快樂,我相信這是驅動生命不斷前行與成長的核心,為生命找到「新」與「變化」的過程。
道拉吉里西北稜踏勘計畫,是一個長達兩個月的冒險,一趟見證了自由與困頓的旅程。有無盡的冰雪之美、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會、來自雪的威脅、熱血的冒險挑戰,以及一日有四季的神奇、未知與已知的衝擊,全都濃縮在世界第七高峰那雪白的巨大山脊與冰河上。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是最強,且大多數人都與我一樣平凡,沒有頂尖登山家的技術與體能。但我們仍能看著強者的背影,讓他們成為我們的勇氣和靠山,陪著每一個人跨越那些看起來高聳可怕的障礙,進行那些想也沒想過的奇妙冒險。看到連湯瑪士這樣的越級打怪者都能賭上性命,借助雪巴之力與好運一次成功,而強如阿果這樣的登山家卻到了2024年第四次挑戰道拉吉里,依然被山神退貨,便能領悟「只看結果」的愚蠢無知,而懂得開始欣賞過程與方法。
有達成目標當然最好,但就算結果不盡如人意,努力的過程也並非毫無收穫,反而還更加珍貴。不斷為自己的生命尋找未知,無論是以什麼樣的形式,都會是精彩絕倫的冒險;再平凡的人,都會因為歷經內在的冒險、找到靈魂的新意而發光發熱。
在世界登山名著《餵鼠──一種老派登山家風範》中,英國登山家莫.安東尼(Mo Anthoine)說過,每個人都需要自己的史詩,以餵飽渴望冒險、在心中啃咬的那隻老鼠,也就是另一個自己。
無論是高峰,又或是大海,甚至是沒去過的國度,每個人都可以在世界的角落裡,透過探索未知找到自己的史詩。那將會是驅動靈魂不斷前行的火種,能在心中永遠燃燒,哪怕軀殼老朽,依然燦爛。道拉吉里毫無疑問是我的史詩,也是阿果、元植的史詩,是巴特克的,是歐列格的,更是湯瑪士的。雖然程度有別,但無論能不能成為人類的史詩,這段日子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意義非凡的旅程。
【第六章.節錄】
▍意料之外的鬧鐘
2023年5月21日,凌晨3:42
尼泊爾,道拉吉里峰第三營,海拔7,250公尺
[…]「羊羊!」聲音再度出現,那是元植的嗓音,我這才發現不是夢,從半夢半醒之中馬上坐起來喊了回去,看了看手錶,心情頓時警戒了起來:「快四點而已,天還沒亮,顯然是撤退了,上面發生什麼事了嗎?!」我思忖著,外頭除了風聲以外多了「嚓、嚓」的冰爪行走聲,還有鉤環在吊帶上的叮叮噹噹,這很明顯是撤退了,而且聽腳步似乎只有他一個人。
「滋──」一聲,我拉開內帳,把頭探出去。外面正飄著小雪,元植黃藍交錯的身影映入眼...
作者序
【推薦序】風雪、星子、道拉吉里——不要告別!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Dhaulagiri)的名字來自梵語,Dhaula意指「耀眼、潔白、美麗」,Giri則是「山」的通稱。它的海拔高度8,167公尺,隔著一道卡利甘達基峽谷(Kali Gandaki Gorge,部分流域直墜5,000米,有「世界最深峽谷」稱號)與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納(Annapurna,海拔8,091公尺,梵語中Anna是「食物」之義,而Purna則是「豐饒」)遙相對望。
世界超過8,000公尺的巨峰共有十四座,其中八座位於尼泊爾境內,而道拉吉里是最西邊的一座,沿著喜馬拉雅山脈往西北,再無更高的山峰,一直要到巴基斯坦境內的南迦帕爾巴特(Nanga Parbat,海拔8,126公尺,當地烏爾都語是「赤裸之山」之義),才戲劇性地為地表最大造山運動收束了一個結尾。
在八十年前的世界8,000米巨峰挑戰賽中,安娜普納是最先被人類足跡踏上的一座,南迦帕爾巴特是最先被歐洲人嘗試攀登的一座。話雖如此,兩座大山奪走人命的數字和成功登頂者的比值都相當高,相較之下,道拉吉里看似親切許多,但也絕不是一座容易的山。因為地理位置靠近印度邊境,沒有其他山峰的阻擋,英國測量隊早在1808年就發現它的山巔,咸認道拉吉里就是世界第一高峰,直到分別三十年與五十年後,大三角測量隊接次發現了干城章嘉與聖母峰為止。
道拉吉里的人類首登紀錄發生在1960年,一支由瑞士、奧地利和雪巴人組成的遠征軍,成功地由東北脊攀上峰頂。它是十四座裡倒數第二個才被攻克的巨峰,部分原因是探勘可行路線花去不少時間,它直面印度平原的南壁,既垂直又高拔,峰頂下有一道300米高的花崗岩環帶,是難關中的難關,至今仍無人能經此路線達陣,號稱為「喜馬拉雅最後障礙」。爾後的攀登者絕大多數都走初登者開發出來的東北脊,在天氣狀況好的情況下,成功登頂的機率非常高。
在這本雪羊所著的《道拉吉里的風》一書中,故事主角是台灣兩位登山家呂忠翰(人稱「阿果」)與張元植,再加上作者自己。而故事的骨幹,則是台灣隊伍與這座8,000米巨峰「交陪」的心路歷程,包含著大山如何施予攀登者無情、壯麗與殘酷的考驗,以及在基地營、高地營、攀登路上和不同國籍的登山者所發生的文化價值撞擊,特別是雪巴人在攀登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總會讓人產生人類學似的立體與深刻的反思。
為什麼要去攀登道拉吉里山呢?阿果是已經許下志願要成為無氧攀登十四座8,000米巨峰的攀登者,尚未完攀的道拉吉里,自是他的必要功課之一;元植在經歷2019年世界第二高峰K2的未竟之役後,決定選擇走跟阿果不一樣的道路,著重於冰雪岩混合、美感路線的技術攀登,此次之所以再度與阿果結成繩伴,是兩人決定不走傳統路,瞄準著尚無人成功走過的西北稜脊。他們覺得如果能攻破兩個難關的煙囪地形,上到雪原後,即使沒有成功登頂,那也看到了世界無人看過的風景,便值回票價。作者雪羊既想要成為兩位大哥的冒險行動紀錄者,也想嘗試走傳統東北脊路線,或可寫下生命中第一座八千大山的紀錄。
故事的結局與三個人的期待不一樣,所有的目標都沒有達到。經歷過多次撤退經驗的阿果和元植慨然地接納這樣的後果,身為作者的雪羊不免心中有很多小劇場,畢竟這是他的喜馬拉雅初體驗,然則,這也是高海拔紀錄吸引人的地方——在都市中的文明人,來到大自然的不毛之地,不論是知性或感性上,都會蛻上好幾層皮,而這一段切身而不免疼痛的歷程,是無法在生命的安全帶之內感受到的。
十九世紀末,最早來到喜馬拉雅山腳下,嘗試攀登南迦帕爾巴特峰的英國登山家阿爾伯特.馬默里(Albert F. Mummery)有言:「登山運動的要義不在於登上一座山巔,而是與困難奮戰,並克服困境。」《道拉吉里的風》一書所描寫的,正是各種困難交織下,三個台灣年輕人如何跟來自大自然與異文明,甚且自身內在心魔的搏戰,所留下的真摯紀錄。
這本書出版的前夕,故事主角之一的元植在法國白朗峰山區攀登時墜落,突然離開了世界。我在前幾年就曾聽他津津有味地描述西北脊未登路線的可能性,眼裡閃耀著光芒,讀著眼前的書頁,我試著進入他們當時的靈魂裡,讓道拉吉里的風把我灌飽(或擊潰),或許這樣,才能驅散那無處不在、宛若一道漫長山谷般、不斷綿延、新生的哀傷。
但讀者們可不必如此,這本書飽滿的是樂觀的勇氣,就像「暴風雪裡滿天的星星」(滅火器大正語),帶著一本,上路吧!
【推薦序】前進十四峰,高山上的毅力、冒險與專業
◎劉柏園(橘子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那是一個勇敢尋找自己的『未知』的過程,讓生命得以往前,讓意識得以延續。當一個人克服萬難去逼近夢想時,無論事大事小,在達成的那一刻,身體便會記住那個體感,暢快、感動、自信、快樂,我相信這是驅動生命不斷前行與成長的核心,為生命找到『新』與『變化』的過程。」
這段話出自書中的一個片段,《道拉吉里的風》充滿了冒險精神和對大自然的敬畏,讓人深刻感受到登山者的勇氣和專業。雪羊(黃鈺翔)以其出色的登山經驗和卓越的紀錄能力,將兩者完美結合,為這次道拉吉里峰的探險注入了非凡的能量和視野。雪羊的生動敘述和專業文字讓人彷彿身臨其境,感受到探險的真實與壯麗,彷彿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皓白的山景。
因為橘子關懷基金會參與支持阿果「前進十四峰」的計畫,才與雪羊有這個緣分;在書中,雪羊細膩地描繪了他與隊友阿果和元植在極端環境下的每一刻,透過他的文字,能感受到那刺骨的寒風、稀薄的空氣,真實體驗到攀登過程中的每一份艱辛與喜悅。這些細節真切地呈現了他們在高海拔地區面對的挑戰和困境,無論是應對失去氧氣瓶的突發意外,還是克服高山反應,都展現專業的態度和無比的毅力,雪羊也透過文字將這一切真實地呈現。
在探險中的合作與互助精神尤為值得讚賞,隊友之間深厚的友誼和無私的團隊精神,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為整個探險增添了無限的力量,體現了真正的團隊合作和無私精神。勇氣和決心是這次探險成功的關鍵,書中生動地記錄了他們的每一刻,令人由衷敬佩。
書中也記錄了在極端環境下應對突發狀況的經歷,從氧氣瓶的意外丟失到面對極端天氣的無常,這些不僅是對技術和體力的挑戰,更是對心理和意志的磨練與登山專業的體現。這些故事展示了對大自然力量的尊重與敬畏,提醒著我們在面對偉大山脈時的謙卑和慎重。
《道拉吉里的風》為每一位心懷夢想的冒險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認真面對並且迎接未知的挑戰,不僅激勵人心,也引領我們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推薦序】風雪、星子、道拉吉里——不要告別!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Dhaulagiri)的名字來自梵語,Dhaula意指「耀眼、潔白、美麗」,Giri則是「山」的通稱。它的海拔高度8,167公尺,隔著一道卡利甘達基峽谷(Kali Gandaki Gorge,部分流域直墜5,000米,有「世界最深峽谷」稱號)與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納(Annapurna,海拔8,091公尺,梵語中Anna是「食物」之義,而Purna則是「豐饒」)遙相對望。
世界超過8,000公尺的巨峰共有十四座,其中八座位於尼泊爾境內,而道拉吉里是最西邊的一座,沿著喜馬拉雅山脈往西北...
目錄
目錄
山岳好手聯合推薦
【推薦序】風雪、星子、道拉吉里——不要告別!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推薦序】前進十四峰,高山上的毅力、冒險與專業 ◎劉柏園(橘子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第一章 八千米的質問
第二章 冒險的前奏
第三章 西北稜,未知的美與自由
第四章 傳統路,已知的困頓與追逐
第五章 冰河上的人性,資本主義的極限
第六章 冒險的本質,屬於每一個人的故事
附錄──寫在2024霞慕尼Frendo Spur攀登事故之後
● 少了一個伴 ◎呂忠翰(阿果)
● 從林鐵到冰川,無可取代的山之背影 ◎雪羊
目錄
山岳好手聯合推薦
【推薦序】風雪、星子、道拉吉里——不要告別!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推薦序】前進十四峰,高山上的毅力、冒險與專業 ◎劉柏園(橘子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第一章 八千米的質問
第二章 冒險的前奏
第三章 西北稜,未知的美與自由
第四章 傳統路,已知的困頓與追逐
第五章 冰河上的人性,資本主義的極限
第六章 冒險的本質,屬於每一個人的故事
附錄──寫在2024霞慕尼Frendo Spur攀登事故之後
● 少了一個伴 ◎呂忠翰(阿果)
● 從林鐵到冰川,無可取代的山之背影 ◎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