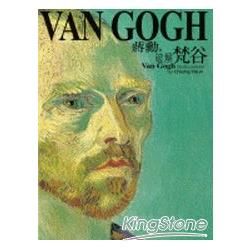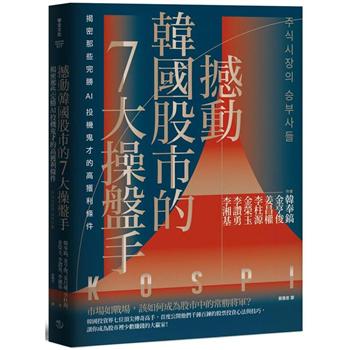梵谷.文生
一位背負新教使命的礦坑牧師
最終成為囚禁在被精神療養院裡的瘋子
一生從未賣出一幅作品
卻在後人被認定是19世紀最偉大的畫家
是信仰與救贖,他刻畫出勞動者最悲哀的存在
是渴望與絕望,他親手割下了自己的左耳
是孤獨與黑暗,他看見眾人所看不到的華麗星光
一八八八年底視梵谷為瘋子的人,和一九八七年以十億台幣高價買梵谷一張「向日葵」的人,都可能沒有讀懂他畫中的心事。
梵谷無法與現實妥協,他要一種絕對純粹的愛,近於信仰上的殉道。殉道者必須飽受折磨,飽受肉體與靈魂的燃燒之苦。
梵谷丟給我們許多問題,在他自殺離開人世後,人們用一百多年的時間試圖回答,仍然無法有完滿解答。
2007年五月,蔣勳帶著一疊稿紙,一站一站地重新再來到梵谷畫作的現場,年輕時儲存在他腦海裡、筆記本裡的故事,躍然而出成為這本書。這是一位美學家面對梵谷危險的美,面對真實生命的深度烙印。
作者簡介
蔣勳
福建長樂人。一九四七年生於古都西安,成長於寶島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一九七二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一九七六年返台。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並先後執教於台大、文化、輔仁大學及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系系主任。專攻中西藝術史研究,亦從事繪畫、創作,多次舉辦畫展,有散文、小說、藝術史、美學論述作品數十種。近年專事美學教育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