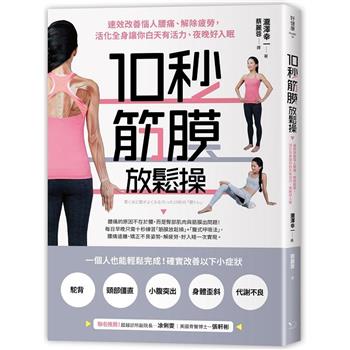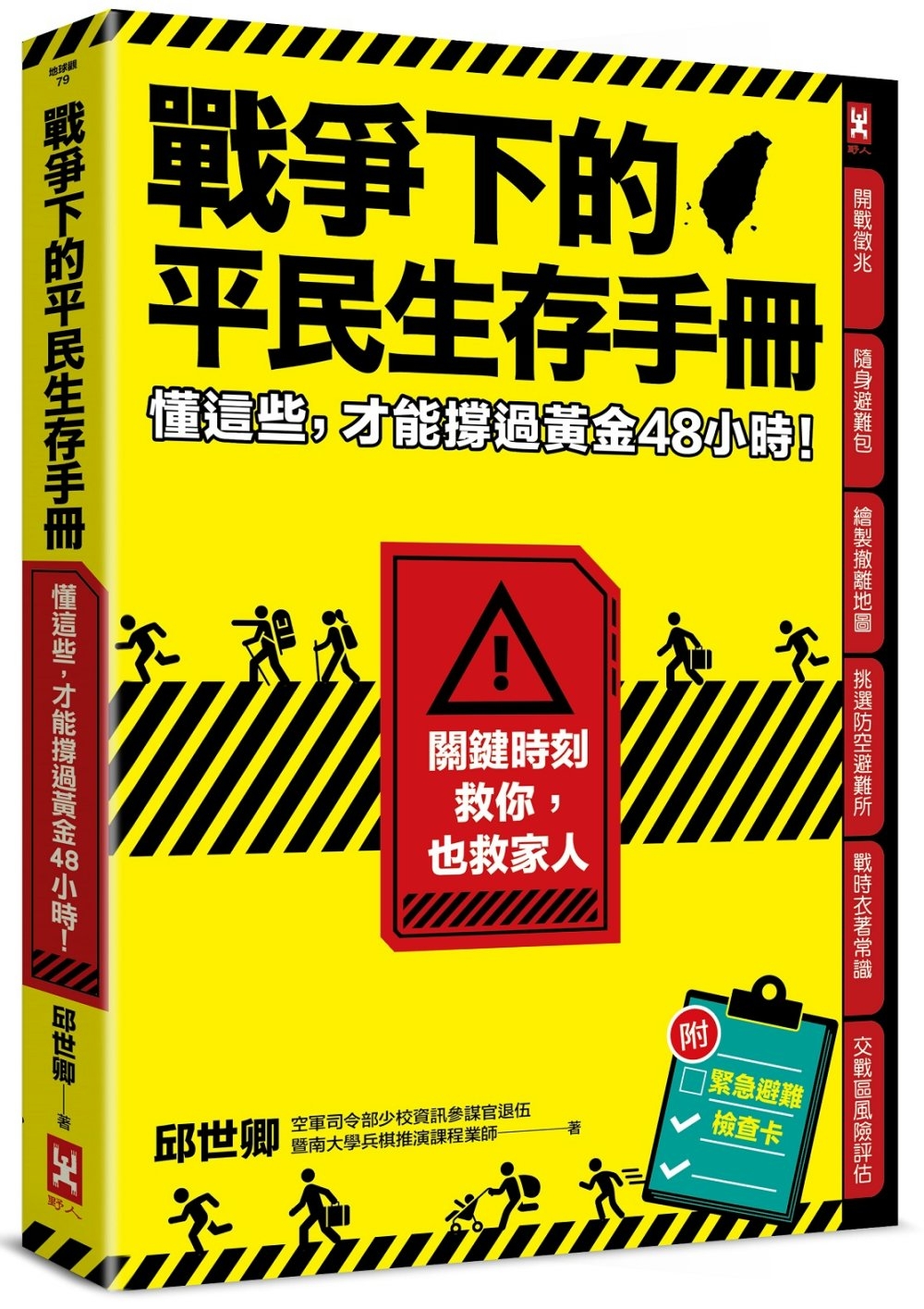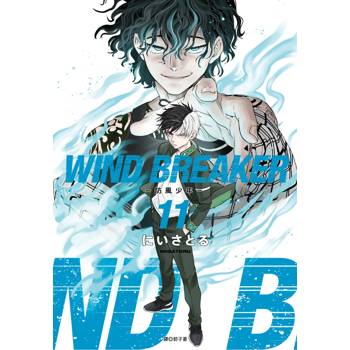序
幾米有一個繪本是《我的世界只有你》,其中有一個故事讓我非常印象深刻,裏頭描述有一個小鼓手,因為她的父母離婚,她對此非常的不諒解,因此她的鼓聲裡總是充滿著憤怒。直到有一天夜半醒來,她看見她的媽媽對著窗外默默地哭泣著。那一刻,她才了解到有許多的事情不僅僅只有她在傷痛,她的媽媽也不例外。她過去擁抱住她的媽媽,兩人相擁而泣。從那之後,她再也打不出憤怒的鼓聲了。
這個故事讓我很有感觸,事實上,我認為,許多我們對他人的不諒解,常常不是因為我們不具備體諒的能力,而是在於我們沒有理解他人困境的機會。
作為一個在醫學系任教的醫學人文教師,當我在講授醫學倫理的時候,我發覺目前大家所看見的醫病關係緊繃、對立,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很好的理解到對方的角色困境。對許多醫療人員而言,他們在繁重的醫療場域中常常無奈於、受傷於一些病人的惡言相向、甚至醫療糾紛。而對病人而言,他們則在病痛的折磨之餘,常常難受於為甚麼醫療人員不能夠對他們多一點同理心?
他們都錯了嗎?其實不然。就如同那個憤怒的小鼓手的媽媽一樣,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沒有把我們自己的困境很好地傳遞給對方知道,也因此對方無從了解我們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了解並且真實的去感受,「病人」角色是一種「非自願性」的選擇,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多一點體諒。這世界上有很多種角色都是我們自願選擇的,但卻沒有人願意主動並且樂意地成為病人這個角色,我們都是不得不地成為一個病人,是疾病找上了我們,使我們成為一個病人。也因此,在這種萬般不願、心有不甘的情況下,要求一個病人能夠抱持理性、平和地與醫療人員溝通,有時實在是一種過高的期待,特別是在一種病痛的折磨下、對疾病的未知恐懼中,病人常常是失了平常的從容的。而病人家屬更是在這種無知的焦慮中,放大了他們的恐懼,因為身邊這個飽受病痛折磨的人,是他們最愛的人,對於最愛的人正遭逢的折磨,有時甚至比 自己受折磨痛苦更甚。
我很喜歡日本茶道中的「一期一會」這個詞,它意指人世間的相遇只有那麼一次。其實這用在病人和疾病身上也很貼切。對很多醫師而言,病人身上的症狀可能已經看過幾百個案例,見怪不怪。但對於那個踏入你診間的病人而言,這些疾病與病人本身都是那「一期一會」。所以當他們問出那些讓你嗤之以鼻的問題、表達出一種你覺得大驚小怪的擔憂時,請試著體諒病人並非與此疾病相熟,他們也只是這麼的一次相遇。特別是當我們對一些事情無法了解、毫無經驗時,無知的恐懼更加會吞沒我們的理性。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一直認為病人與病人家屬也必須學著去理解並體諒醫療人員背後的辛苦與困境。其實病人對醫療人員的怒目相向也不在少見,特別是我們這幾十年來特別強調「病人的權利」、「醫療是種服務業」的過度解讀的情況下,有時病人或者是家屬會忽略掉一種對人的基本尊重。
正如同我們希望醫療人員能夠理解病人的「一期一會」,我們也希望病人及其家屬能夠理解,醫療人員不僅要處理你的「一期一會」,他們同時還得處理許多病人的「一期一會」。但醫療人員的時間、精力是固定的,我們在過度要求他們的醫療態度時,是否也曾關懷過他們是否也已經在體力耗盡的邊緣?當他們面臨這些臨床醫療場域中與疾病分秒必爭搶救病人的生命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可以多一點對人的基本同理心?去想想他們究竟已經多久沒有坐下來休息一下、喝一口水了?
每個早晨,我們還在睡夢中時,許多醫療人員已經在醫院開始他們緊湊的醫療工作;當我們在餐廳享用一頓豐富的晚餐,愉快的打卡上傳照片時,他們可能還在門診工作中一個接一個病人的進行診療;而深夜當我們安詳地進入夢鄉時,他們可能還在手術台上奮戰,努力搶救病人的生命。而這一些難道不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尊重與體諒嗎?
任何一種「關係」,不論是朋友關係、親子關係、夫妻關係等,都必須建基在互相尊重與體諒上,這一段關係才有可能走的健康、走得長遠。醫病關係也不例外。過於強調病人的權利,而忽略病人的義務以及損害醫療人員的權利,都不是一種健全的狀態;反之亦然。
唯有雙方都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學著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與體諒,這種關係才有可能良好的維繫下去,而所謂的信任才有可能 慢慢地滋生。
鼓聲可以是悠揚的,讓我們停止憤怒的鼓聲,試著理解每個人背後所經受的痛苦,學著體諒在每個情緒下的行為,當我們都能夠放下自身的成見,相信醫病關係能夠越來越好。
編著者 謹識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醫學倫理教育:由理論到實踐(第三版)的圖書 |
 |
醫學倫理教育:由理論到實踐(第三版) 作者:黃苓嵐 出版社:新文京 出版日期:2019-08-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14頁 / 17 x 23 x 1.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三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8 |
醫藥 |
$ 318 |
中文書 |
$ 318 |
醫學總論 |
$ 318 |
高等教育 |
$ 318 |
健康醫療 |
$ 335 |
醫療衛生學群 |
$ 335 |
醫療保健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醫學倫理教育:由理論到實踐(第三版)
「醫學倫理」是在探究醫學情境中所會涉及到的「關係」,包含了醫療人員與病人間的關係、醫療人員彼此間的關係、醫療人員與相關機構的關係、醫學與社會的關係等。醫學倫理教育希望達成兩個目的:一是教導我們認知什麼是符應於醫學倫理的行為,另一個則是幫助我們願意去落實這些倫理行為。
本書透過對醫學倫理的相關基本原則以及判斷進行說明,並進而找出可以幫助這些原則實踐的方式。在這本書中,作者由道德情感教育以及生命教育這兩個方面來切入醫學倫理教育之中,透過這兩種模式,引導讀者由理論進入到實踐,確實的落實醫學倫理的價值。
第三版更新案例、補充新知,並新增倫理的價值、醫學教育的核心等單元,及各種目前臨床可能遇到的倫理問題。
本書各章問題與討論均須讀者研讀該章內容後,自行思考或討論作答,不提供解答。需要標準解答的自學讀者,選購時請留意,出版公司與銷售單位均無法提供解答給讀者。
作者簡介:
黃苓嵐
學歷:
輔仁大學 哲學研究所 博士
現任: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倫理學、醫學人文、兒童哲學、生死學
作者序
序
幾米有一個繪本是《我的世界只有你》,其中有一個故事讓我非常印象深刻,裏頭描述有一個小鼓手,因為她的父母離婚,她對此非常的不諒解,因此她的鼓聲裡總是充滿著憤怒。直到有一天夜半醒來,她看見她的媽媽對著窗外默默地哭泣著。那一刻,她才了解到有許多的事情不僅僅只有她在傷痛,她的媽媽也不例外。她過去擁抱住她的媽媽,兩人相擁而泣。從那之後,她再也打不出憤怒的鼓聲了。
這個故事讓我很有感觸,事實上,我認為,許多我們對他人的不諒解,常常不是因為我們不具備體諒的能力,而是在於我們沒有理解他人困境的機會。
...
幾米有一個繪本是《我的世界只有你》,其中有一個故事讓我非常印象深刻,裏頭描述有一個小鼓手,因為她的父母離婚,她對此非常的不諒解,因此她的鼓聲裡總是充滿著憤怒。直到有一天夜半醒來,她看見她的媽媽對著窗外默默地哭泣著。那一刻,她才了解到有許多的事情不僅僅只有她在傷痛,她的媽媽也不例外。她過去擁抱住她的媽媽,兩人相擁而泣。從那之後,她再也打不出憤怒的鼓聲了。
這個故事讓我很有感觸,事實上,我認為,許多我們對他人的不諒解,常常不是因為我們不具備體諒的能力,而是在於我們沒有理解他人困境的機會。
...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Chapter 1 醫學與倫理
第一節 倫理與醫學倫理
第二節 醫學倫理教育的目的
第三節 各種倫理學說在醫學倫理上的應用
第四節 醫學倫理教育的困難
Chapter 2 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一)
第一節 不傷害原則
第二節 自主原則
Chapter 3 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二)
第一節 效益原則
第二節 正義原則
第三節 知情同意原則
第四節 行善原則
第五節 誠信原則
Chapter 4 醫學倫理中的道德判斷方式
第一節 道德判斷的重要性
第二節 道德判斷的方式
第三節 道德判斷的實際應用
Chapter 5 醫學倫理的道德情感教育
第一節 當前的醫學倫...
第一節 倫理與醫學倫理
第二節 醫學倫理教育的目的
第三節 各種倫理學說在醫學倫理上的應用
第四節 醫學倫理教育的困難
Chapter 2 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一)
第一節 不傷害原則
第二節 自主原則
Chapter 3 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二)
第一節 效益原則
第二節 正義原則
第三節 知情同意原則
第四節 行善原則
第五節 誠信原則
Chapter 4 醫學倫理中的道德判斷方式
第一節 道德判斷的重要性
第二節 道德判斷的方式
第三節 道德判斷的實際應用
Chapter 5 醫學倫理的道德情感教育
第一節 當前的醫學倫...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