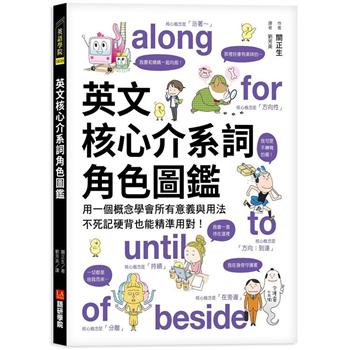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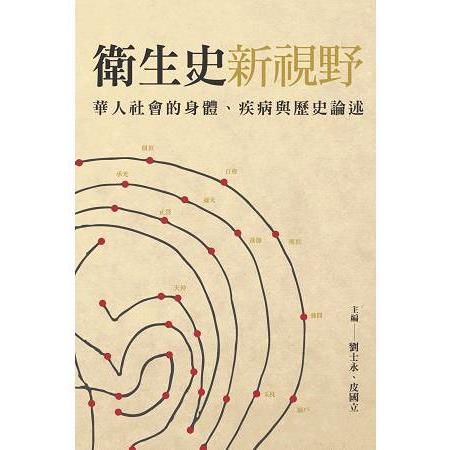 |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 作者:劉士永、皮國立 出版社: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25 |
二手中文書 |
$ 383 |
健康醫療 |
$ 405 |
中國歷史 |
$ 405 |
中國歷史 |
$ 405 |
中國歷史 |
$ 405 |
醫療保健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
內容簡介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是一本集合多數年輕學者的研究成果所編輯而成的學術專著。近三年來,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與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共同組織了「醫學史與醫學人文研究與教學」(2013)、「生命醫療史與醫籍文獻」(2014)等兩場學術會議,成就了本書的基礎;此外,本書還邀請學者提供較具有主題性的文章,一併經由審查通過後始收入,使本書的整體內容具有「生命醫療的文本與書寫」、「疾病與醫治的歷史」和「醫療衛生與政治」等三大向度。這些專書的共同作者包括了歷史學者、文學家和中醫師,他們試著從不同的切入視角來書寫一篇篇與近代「衛生」、「身體」和「疾病」有關的故事,大體展現了臺灣生命醫療史研究的若干傳承與創新之論述。
作者介紹
主編簡介
劉士永
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博士,現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研究興趣為近代臺灣史、日本殖民醫學史、20世紀東亞公共衛生史,與東亞環境史等。著有專書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 and Policy in Japan-Ruled Taiwan、《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之接納與開展》,以及相關領域論文40餘篇。當前研究重點為二戰時期中國軍事醫護體系發展,與冷戰時期東亞地區美援醫療之關係。
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歷史組專任助理教授,兼任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出版過《醫通中西——唐宗海與近代中醫危機》、《臺灣日日新——當中藥碰上西藥》、《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等學術專書。
劉士永
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博士,現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研究興趣為近代臺灣史、日本殖民醫學史、20世紀東亞公共衛生史,與東亞環境史等。著有專書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 and Policy in Japan-Ruled Taiwan、《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之接納與開展》,以及相關領域論文40餘篇。當前研究重點為二戰時期中國軍事醫護體系發展,與冷戰時期東亞地區美援醫療之關係。
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歷史組專任助理教授,兼任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出版過《醫通中西——唐宗海與近代中醫危機》、《臺灣日日新——當中藥碰上西藥》、《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等學術專書。
目錄
導言 i
壹、生命醫療的文本與書寫 001
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劉士永 003
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吾妻鏡》及其讀者╱張仲民 045
責任與擔當:二十世紀中國的醫學史研究╱甄橙 073
醫療與救國想像──論蔣渭水〈臨床講義〉的醫療隱喻與主體再現╱陳康芬 095
貳、疾病與醫治的歷史 115
近代中國的大流感: 1919-1920 年疫情之研究╱皮國立 117
鼠疫前香港醫療狀況:以《1895 年醫務委員會報告書》為中心╱羅婉嫻 143
西醫東漸對民初中醫學術的影響──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趙中豪 169
參、醫療衛生與政治 191
遷徙與籌組:抗戰時期軍醫教育體系的建立╱楊善堯 193
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以廈門關為例╱李欣璇 217
編後記 249
壹、生命醫療的文本與書寫 001
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劉士永 003
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吾妻鏡》及其讀者╱張仲民 045
責任與擔當:二十世紀中國的醫學史研究╱甄橙 073
醫療與救國想像──論蔣渭水〈臨床講義〉的醫療隱喻與主體再現╱陳康芬 095
貳、疾病與醫治的歷史 115
近代中國的大流感: 1919-1920 年疫情之研究╱皮國立 117
鼠疫前香港醫療狀況:以《1895 年醫務委員會報告書》為中心╱羅婉嫻 143
西醫東漸對民初中醫學術的影響──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趙中豪 169
參、醫療衛生與政治 191
遷徙與籌組:抗戰時期軍醫教育體系的建立╱楊善堯 193
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以廈門關為例╱李欣璇 217
編後記 249
序
導讀
醫學史研究向來有「內史」與「外史」的分類說法,前者經常用來指涉醫學的知識或技術演變,而後者則泰半討論的是影響或承受醫學活動之社會及文化條件。相映之下,醫學「內史」儼然成為醫者專擅之場域,而醫療「外史」則似乎是人文社會學者揚聲的所在。然而,若借用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或後來被稱為結構史(structural history)學派的觀點而言,這般內史、外史的分野恐未能反映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反而更像是醫家與人文社會學者互相區隔的便宜行事,從而可能造成各自陳述裡「見樹不見林」的隱憂。
1929 年從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初試啼聲之年鑑學派支持者,呼籲歷史研究應當突破傳統歷史學家本身的,或是與其他學科間自立門戶、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他們的主張以今日時髦的語彙來說,就是跨界(cross-boundaries)與跨學科(multi-disciplines)研究。為了倡導史家去研究人類活動的總體像而非殊像,歷史分析就必須除了傳統史學擅長之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範疇外,也應包括影響人類活動之自然或環境條件,也就是自然科學專長的領域,並透過比較的手法凸顯社會結構的作用。他們所提倡之歷史比較研究,就是比較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來加深、擴大和驗證對歷史的認識之方法。這種比較與對照,既可以是單一社會經驗內的縱向(時間)對比,也可以是不同社群間之橫向(空間)對照。1980 年代之後,美國史學界更由此衍義比較研究對結構史學派的重要性,認為是否應用比較方法於歷史研究中,有助於研究者檢視其是否具備探索的精神和開放的態度。
立基於這樣的觀點,這本《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或許會被歸類為醫學「外史」,但從表現華人社會對身體、疾病乃至於醫藥的歷史經驗來說,本書尚可視為運用結構史學觀點的醫學史研究,而無須在意其是否該被歸類為「內史」抑或「外史」。尤其是醫學或醫療領域涵蓋面甚廣,更不若量子物理或基因研究等硬科學(hard science)般遠離人們的日用生活。從象牙塔最深處的知識與研究,以迄病榻旁的熬煮湯藥及灶腳邊的養生餐食,專家或素人都無可避免地參與到醫學知識的脈絡與實作中,因此專長研究人與其相關事務的史家,當然有觀察與分析醫學史的立足點。此外,從問醫求診到養身保健,個人與社會都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為醫學知識及醫療行為所影響,這些影響既是全面的(overwhelming),但也經常是片斷與不連續的(fragmental and disconnected),此等情況尤令研究者須由多元面向,切入醫療這個複雜的現象。
本書的論著主體,多選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與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合辦之青年學者醫學史相關會議論文。這些論文的作者對醫療在華人社會裡的關懷角度不一,切入分析的手法也不盡相同,但熱中參透醫療行為與華人社會之糾結則無分軒輊。本書九篇論文雖各自展現其議題與論證,但內在仍有理路相通氣息。舉例而言,〈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以廈門關為例〉一文,論證晚清海關檢疫制度作為新興洋務在傳統中國開展的歷史意義。是文曾點出華人社會對於洋務等於西化或現代化的期待甚或可能的爭議,儘管兩者已相距近百年,在〈遷徙與籌組:抗戰時期軍醫教育體系的建立〉的討論中仍依稀可見。這般視西醫為現代醫學或拯救民族的醫學之類的想法,即便是跨海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亦然,這亦可由〈醫療與救國想像─論蔣渭水〈臨床講義〉的醫療隱喻與主體再現〉的字裡行間仔細玩味得知。而〈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吾妻鏡》及其讀者〉的作者,則從民初社會對於性病的恐懼及性學之欲拒還迎中,發掘出《吾妻鏡》雜誌在建構性道德論上的時代與社會意涵。若將這四篇論文對比覘之,即能看出〈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與〈遷徙與籌組〉二文,呈現的是自上而下的醫療現代性期待,而〈醫療與救國想像〉及〈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則更趨近於社會對新醫學的想像與運用,或許更隱喻了社會菁英欲由下而上改造國家、民族的期待。如此推進新醫學或衛生體制的上下期待交錯與交鋒,於今之華人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
一如政治期待與民族想像無法自外於華人對醫療與醫學的期待,疾病的經驗更是難以醫者或俗民為區分基準。儘管患病經驗不盡然有上下之別,但卻有關照全體與個人體驗的落差。對於患者個人的抒懷或自身體驗,過去多半是文學家擅長的領域,前述〈醫療與救國想像〉一文的筆法即相當貼近此等文學性的論述。然對於習慣關注總體經驗之史家,或是強調總體史(total history)的結構史學派,以社會總體為單位處理疾病流行與醫學知識傳播方屬常態。無怪乎,皮國立以〈近代中國的大流感:1919-1920 年疫情之研究〉探討西班牙流感總體性地威脅下,政府、民間,與醫界對應之道與困境,相對地是羅婉嫻之〈鼠疫前香港醫療狀況﹕以《1895 年醫務委員會調查報告書》為中心〉,雖同樣從政府立場討論 1895 年香港鼠疫之蔓延,但也凸顯了香港當時作為一個國際港、殖民城市,以及對於中國疫情環伺的憂慮。前述兩篇以國家對照社會(state vs. society)為基調的論文,在〈西醫東漸對民初中醫學術的影響─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中卻以不同的角度開展對於「全體」的理解。除了表面上的政府與社會,歷史中的醫界也自有其對全體社會之關照和對政府之想像。儘管作者僅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然其欲呈現的是該時代裡醫家與大時代的關聯及肆應。對照閱讀上述三篇論文的價值,不僅是回溯醫學與疾病的經驗而已,亦是對各個政府與社會所處歷史時空條件的投射,亦即透過史學研究才能達到之「同情的理解」。而孰令兩者能適切揉合?或許唯有醫學史背景者方以致之。
全書尚有兩篇論文〈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與〈責任與擔當:二十世紀中國的醫學史研究〉,顯然較為偏向史學史式的分析,並得以此作為全書各篇論文的基礎,以協助讀者瞭解當前華人醫學史研究之淵源,並兼及呈現醫學史學者的根本關懷及價值。雖說海峽兩岸之華人醫學史發展,均可追溯自民國初年對於西學之渴求,但大陸在 1949 年後的醫史學發展與臺灣於 1990 年代後再現之研究熱潮,卻不盡然系出同源。由兩篇論文之比較閱讀不難發覺,大陸醫學史研究與臺灣醫學史學者的興趣或有交疊,資料上也頗多參照,但兩者分析之手法或教育之理想等則相當不同。類似的差異也體現於各自醫學史傳統之延續;大陸醫學史的傳統起於民初而賡續迄今,其所在意者是如何配比時代價值與意義,以便和現代醫學科學與時俱進。臺灣方面則尋求如何從醫家業餘興趣及史家旁系間,走出自己的領域與研究特質,成為醫史學者無可逭逃之承擔。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編輯伊始,即擬以青年學者為主體而編纂其代表作品。鼓勵新血後進持續投入醫學史領域,當然是編輯出版本書的目的之一。然尤有甚者,相較於政治史,或稍微晚近點的社會經濟史,醫學史實在不能稱之為有傳統的史學領域。儘管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嘉言,無法應和今日醫學史發展的階段需求,但《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修為砥礪,卻暗喻了編輯們為本書取「新」字的深切期許。後者的「新」有自身持續進步、棄舊揚新的底蘊;也同樣是對新生世代引領研究新氣象與新視野的期待,盼望化世代差異而成就研究上之新意與發展之蛻變。識者或將發現本書之主題容有斷續,各論文間的立場與觀點也不免互異。惟就青年史家之養成與歷史之真實面言之,此等現象儘管無非是年輕史家必經之青澀階段,但卻又何嘗不是華人醫學史多元且豐富之面貌所致?回應導言之初所簡述的結構史學派觀點,也許保留這些論文主題與觀點的歧出,亦是一種反映歷史真實的手法。至於對某些華人醫學史論題之系統性專論,編輯們期待日後能在本書的作者群中誕生相應的專書寫作,如此亦不枉費大家戮力同心於本書之精力與時日。
劉士永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聘研究員
醫學史研究向來有「內史」與「外史」的分類說法,前者經常用來指涉醫學的知識或技術演變,而後者則泰半討論的是影響或承受醫學活動之社會及文化條件。相映之下,醫學「內史」儼然成為醫者專擅之場域,而醫療「外史」則似乎是人文社會學者揚聲的所在。然而,若借用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或後來被稱為結構史(structural history)學派的觀點而言,這般內史、外史的分野恐未能反映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反而更像是醫家與人文社會學者互相區隔的便宜行事,從而可能造成各自陳述裡「見樹不見林」的隱憂。
1929 年從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初試啼聲之年鑑學派支持者,呼籲歷史研究應當突破傳統歷史學家本身的,或是與其他學科間自立門戶、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他們的主張以今日時髦的語彙來說,就是跨界(cross-boundaries)與跨學科(multi-disciplines)研究。為了倡導史家去研究人類活動的總體像而非殊像,歷史分析就必須除了傳統史學擅長之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範疇外,也應包括影響人類活動之自然或環境條件,也就是自然科學專長的領域,並透過比較的手法凸顯社會結構的作用。他們所提倡之歷史比較研究,就是比較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來加深、擴大和驗證對歷史的認識之方法。這種比較與對照,既可以是單一社會經驗內的縱向(時間)對比,也可以是不同社群間之橫向(空間)對照。1980 年代之後,美國史學界更由此衍義比較研究對結構史學派的重要性,認為是否應用比較方法於歷史研究中,有助於研究者檢視其是否具備探索的精神和開放的態度。
立基於這樣的觀點,這本《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或許會被歸類為醫學「外史」,但從表現華人社會對身體、疾病乃至於醫藥的歷史經驗來說,本書尚可視為運用結構史學觀點的醫學史研究,而無須在意其是否該被歸類為「內史」抑或「外史」。尤其是醫學或醫療領域涵蓋面甚廣,更不若量子物理或基因研究等硬科學(hard science)般遠離人們的日用生活。從象牙塔最深處的知識與研究,以迄病榻旁的熬煮湯藥及灶腳邊的養生餐食,專家或素人都無可避免地參與到醫學知識的脈絡與實作中,因此專長研究人與其相關事務的史家,當然有觀察與分析醫學史的立足點。此外,從問醫求診到養身保健,個人與社會都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為醫學知識及醫療行為所影響,這些影響既是全面的(overwhelming),但也經常是片斷與不連續的(fragmental and disconnected),此等情況尤令研究者須由多元面向,切入醫療這個複雜的現象。
本書的論著主體,多選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與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合辦之青年學者醫學史相關會議論文。這些論文的作者對醫療在華人社會裡的關懷角度不一,切入分析的手法也不盡相同,但熱中參透醫療行為與華人社會之糾結則無分軒輊。本書九篇論文雖各自展現其議題與論證,但內在仍有理路相通氣息。舉例而言,〈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以廈門關為例〉一文,論證晚清海關檢疫制度作為新興洋務在傳統中國開展的歷史意義。是文曾點出華人社會對於洋務等於西化或現代化的期待甚或可能的爭議,儘管兩者已相距近百年,在〈遷徙與籌組:抗戰時期軍醫教育體系的建立〉的討論中仍依稀可見。這般視西醫為現代醫學或拯救民族的醫學之類的想法,即便是跨海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亦然,這亦可由〈醫療與救國想像─論蔣渭水〈臨床講義〉的醫療隱喻與主體再現〉的字裡行間仔細玩味得知。而〈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吾妻鏡》及其讀者〉的作者,則從民初社會對於性病的恐懼及性學之欲拒還迎中,發掘出《吾妻鏡》雜誌在建構性道德論上的時代與社會意涵。若將這四篇論文對比覘之,即能看出〈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與〈遷徙與籌組〉二文,呈現的是自上而下的醫療現代性期待,而〈醫療與救國想像〉及〈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則更趨近於社會對新醫學的想像與運用,或許更隱喻了社會菁英欲由下而上改造國家、民族的期待。如此推進新醫學或衛生體制的上下期待交錯與交鋒,於今之華人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
一如政治期待與民族想像無法自外於華人對醫療與醫學的期待,疾病的經驗更是難以醫者或俗民為區分基準。儘管患病經驗不盡然有上下之別,但卻有關照全體與個人體驗的落差。對於患者個人的抒懷或自身體驗,過去多半是文學家擅長的領域,前述〈醫療與救國想像〉一文的筆法即相當貼近此等文學性的論述。然對於習慣關注總體經驗之史家,或是強調總體史(total history)的結構史學派,以社會總體為單位處理疾病流行與醫學知識傳播方屬常態。無怪乎,皮國立以〈近代中國的大流感:1919-1920 年疫情之研究〉探討西班牙流感總體性地威脅下,政府、民間,與醫界對應之道與困境,相對地是羅婉嫻之〈鼠疫前香港醫療狀況﹕以《1895 年醫務委員會調查報告書》為中心〉,雖同樣從政府立場討論 1895 年香港鼠疫之蔓延,但也凸顯了香港當時作為一個國際港、殖民城市,以及對於中國疫情環伺的憂慮。前述兩篇以國家對照社會(state vs. society)為基調的論文,在〈西醫東漸對民初中醫學術的影響─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中卻以不同的角度開展對於「全體」的理解。除了表面上的政府與社會,歷史中的醫界也自有其對全體社會之關照和對政府之想像。儘管作者僅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然其欲呈現的是該時代裡醫家與大時代的關聯及肆應。對照閱讀上述三篇論文的價值,不僅是回溯醫學與疾病的經驗而已,亦是對各個政府與社會所處歷史時空條件的投射,亦即透過史學研究才能達到之「同情的理解」。而孰令兩者能適切揉合?或許唯有醫學史背景者方以致之。
全書尚有兩篇論文〈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與〈責任與擔當:二十世紀中國的醫學史研究〉,顯然較為偏向史學史式的分析,並得以此作為全書各篇論文的基礎,以協助讀者瞭解當前華人醫學史研究之淵源,並兼及呈現醫學史學者的根本關懷及價值。雖說海峽兩岸之華人醫學史發展,均可追溯自民國初年對於西學之渴求,但大陸在 1949 年後的醫史學發展與臺灣於 1990 年代後再現之研究熱潮,卻不盡然系出同源。由兩篇論文之比較閱讀不難發覺,大陸醫學史研究與臺灣醫學史學者的興趣或有交疊,資料上也頗多參照,但兩者分析之手法或教育之理想等則相當不同。類似的差異也體現於各自醫學史傳統之延續;大陸醫學史的傳統起於民初而賡續迄今,其所在意者是如何配比時代價值與意義,以便和現代醫學科學與時俱進。臺灣方面則尋求如何從醫家業餘興趣及史家旁系間,走出自己的領域與研究特質,成為醫史學者無可逭逃之承擔。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編輯伊始,即擬以青年學者為主體而編纂其代表作品。鼓勵新血後進持續投入醫學史領域,當然是編輯出版本書的目的之一。然尤有甚者,相較於政治史,或稍微晚近點的社會經濟史,醫學史實在不能稱之為有傳統的史學領域。儘管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嘉言,無法應和今日醫學史發展的階段需求,但《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修為砥礪,卻暗喻了編輯們為本書取「新」字的深切期許。後者的「新」有自身持續進步、棄舊揚新的底蘊;也同樣是對新生世代引領研究新氣象與新視野的期待,盼望化世代差異而成就研究上之新意與發展之蛻變。識者或將發現本書之主題容有斷續,各論文間的立場與觀點也不免互異。惟就青年史家之養成與歷史之真實面言之,此等現象儘管無非是年輕史家必經之青澀階段,但卻又何嘗不是華人醫學史多元且豐富之面貌所致?回應導言之初所簡述的結構史學派觀點,也許保留這些論文主題與觀點的歧出,亦是一種反映歷史真實的手法。至於對某些華人醫學史論題之系統性專論,編輯們期待日後能在本書的作者群中誕生相應的專書寫作,如此亦不枉費大家戮力同心於本書之精力與時日。
劉士永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