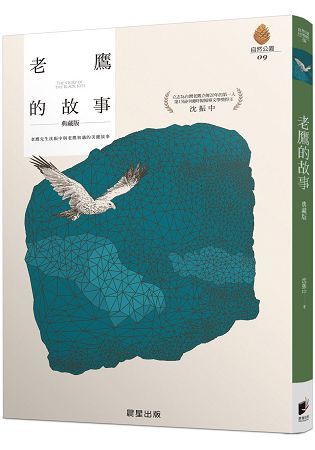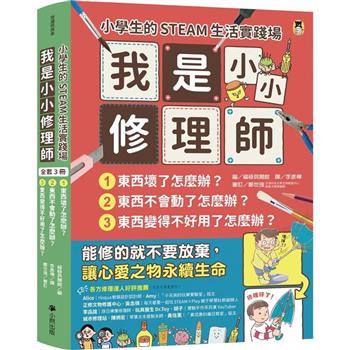圖書名稱:老鷹的故事【典藏版】
《老鷹想飛》記錄老鷹先生沈振中追鷹20年的故事,
三年來飛越全台,感動台灣2000萬人!
看過《老鷹想飛》,
絕不能錯過《老鷹的故事》!
立志為台灣老鷹立傳20年的第一人
第15屆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得主
老鷹先生沈振中
與老鷹初遇的美麗故事
老鷹先生沈振中是台灣首位全天候投入老鷹觀察的記錄者,他為老鷹寫日記,春天繁殖季時,奔忙於巢位之間,仔細記錄誰向誰求愛?如何求愛?在哪築巢?何時築巢?完全忽視花費了的多少心力、時間與體力。如此全心全力的記錄,成就了本書。
本書共分為三個篇章,第一篇〈老鷹的守護者〉是位於基隆老鷹族群的故事。完整記錄老鷹們的「生活日記」,包括基本習性:抓枝、晚點名,及求偶、築巢、育雛的經過。
第二和第三篇章,則記錄老鷹先生除了老鷹記錄之外的自然觀察及自然體驗,如廚房角落的蜘蛛觀察,以及獨自步行、露營的方式,從台北至屏東近四百公里的自然體驗日記。
本書特色
1.《老鷹想飛》紀錄片主人翁沈振中先生,第一本完整記錄老鷹故事的書籍,也是《老鷹想飛》紀錄片的起點。
2.看過《老鷹想飛》,感動於老鷹先生沈振中對台灣老鷹的癡迷,就不能錯過《老鷹的故事》。
作者簡介
沈振中
四十三年生,基隆人。輔大生物系畢,曾任康寧護校、德育護專生物教師,於八十一年遇見老鷹,八十二年辭去教職,全心投入台灣老鷹觀察記錄工作,立志為老鷹作傳二十年。曾任基隆鳥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野鳥協會常務理事長、基隆鳥會常務監事,著有《老鷹的故事》、《鷹兒要回家》、《尋找失落的老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