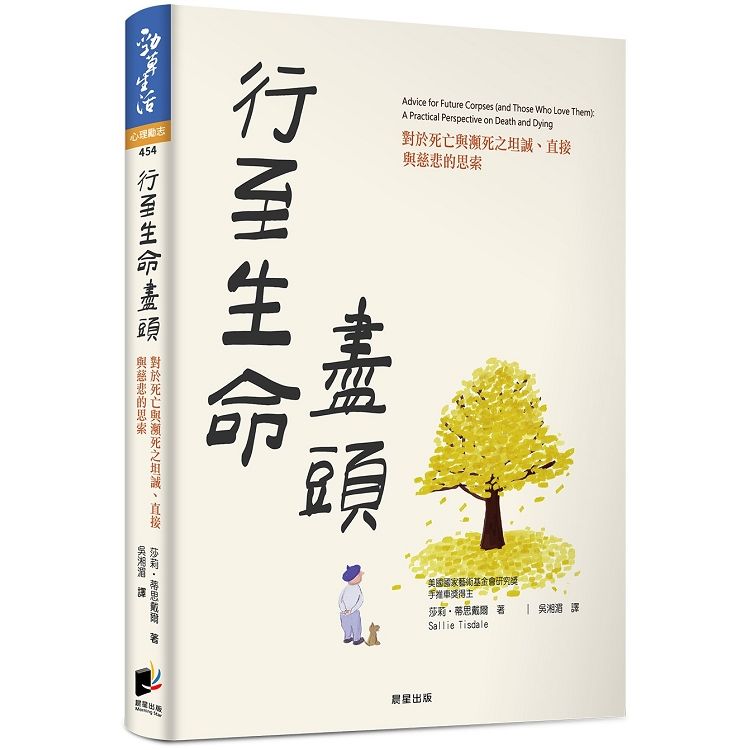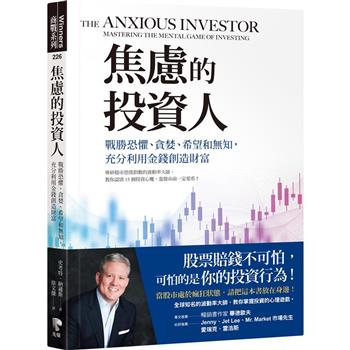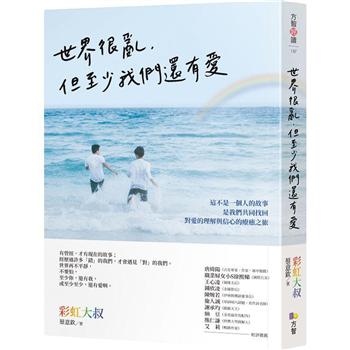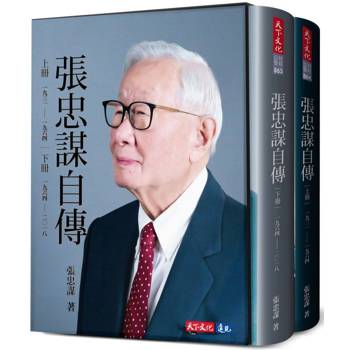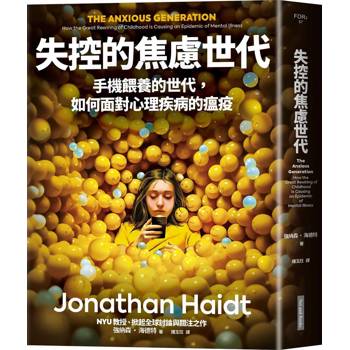生命的盡頭有什麼?
我們究竟在害怕什麼?
當一個人在死亡當下及過世之後,情況會是怎麼樣呢?
這是寫給每個人在面對人生終途時的實用建議,我們都該學習如何向生命說再見......
累積自作者從事護理工作及十幾年安寧照護的經驗,她以坦誠、慈悲的方式引導我們去思索那無可避免的生命盡頭:
●善終:「善終」是什麼意思?善終的方式只有一種嗎?我要怎麼做才能讓自己或摯愛的人擁有「善終」呢?
●溝通: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對垂死之人、至親、醫生等,什麼該問、何時問。
●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幾週、幾天、幾個小時:哪些是你在形體上、精神上所可能預期的,包括那個獨特的時刻所意味的侷限、自由、痛苦、和喜悅等。
●遺體:死亡後,遺體會產生什麼變化?我死後可以有哪些選擇、要如何選擇、如何確定我的願望能被遵循?
●悲傷:「悲傷是一個必需不斷被重複述說的故事,一次又一次......」
這是一本關於死亡、其實也是關於如何活著的書,將讓你思考你真的很不想去思考的一些事......
本書特色
1.這不只是一本面對死亡時的操作手冊或心靈聖經,作者詳細地匯編全世界的殯葬傳統以及在工作和生命裡所曾目睹的與死亡相關的軼事。在死亡和垂死的議題上提供了許多感情豐富、引人深思且實際的觀點。
2.作者以她鎮靜、睿智、又幽默的筆,帶領讀者穿越死亡的峰谷,也帶領讀者思考生死之事。
3.大眾普遍存在著面對衰老和死亡的恐懼,這本書會帶給我們面對死亡的有力答案,協助我們消除潛藏的不安感。
4.書中提供了死亡計畫書、預設醫療指示等文件,讓我們在讀完本書後,可以練習從計劃書中學習如何隨時為死亡這件事做好準備。
作者簡介:
莎莉.蒂思戴爾 (Sallie Tisdale)
已出版之作品包括《冒犯》、《挑逗我》、《往西邁進》、《女禪師的智慧》等。她曾獲得手推車獎、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研究獎、詹姆斯‧迪‧費朗恩文學獎等,並曾獲選成為舍恩費爾特傑出訪問作者系列之一。她的作品經常出現在《哈潑雜誌》、《紐約客》、《三毛錢文學評論》、《安堤阿克文學評論》以及《Conjunction》、《Tricycle》等佛教雜誌裡。除了屢獲殊榮的寫作生涯,蒂思戴爾多年來一直從事護理工作,其中包括十年的安寧緩和醫療,她住在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歡迎拜訪她的網站:SallieTisdale.com
譯者簡介:
吳湘湄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英美文學碩士、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博士
譯有文學類與勵志類書籍十數種:《心靈雞湯之悲傷話題》、《相信自己很棒》、《愛因斯坦怎麼思考》、《馬克吐溫的人生建言》(皆為晨星出版)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莎莉.蒂思戴爾優雅低調的新書《行至生命盡頭》乍看是一本操作手冊,實際上卻是一本深刻的沉思錄。它乍看也是一本有關如何死亡,而事實上是有關如何活著的書。」
——大衛.薛爾德,暢銷書《真相渴求》作者
★「蒂思戴爾寫作的所有中心思維都與照料他人有關,而事實證明,這永遠是一個複雜又動人的主題。」
——蘿拉.馬爾許,《紐約客》
★「莎莉.蒂思戴爾是一個真正的典範。身為作家,她的思考像哲學家,觀察力像新聞工作者,而行文書寫像吟唱詩人。」
——梅格罕.東姆,《不可言說》一書作者
★「蒂思戴爾的長處在於透過歷史、民俗、敏銳的分析及個人軼聞等的整合幫助讀者看見事情的重點。」
——《出版者週刊》
★「閱讀莎莉.蒂思戴爾的《行至生命盡頭》時,不過幾行字我就著魔了。不管她描繪的是體重驟減的霸道、綠頭蒼蠅令人驚駭的生命、或在腫瘤科工作時的經驗(她是一名盡忠職守的護士,也是一位才氣橫溢的作家),從頭到尾我全都沉迷其中。我願意追隨她到她筆下所描述的任何地方去:一個交替的圖像——跟隨她進入潛艇掌握駕駛桿,然後潛至最深深深處,進入她奇特的感性、她語言的魔力、以及她對我們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的熱愛。」
——凱倫.卡波,《茱莉亞.釵爾德傳:享受生命的課程》一書作者
★「莎莉.蒂思戴爾將一個可能有點世俗或過度操作的主題,神奇地轉化成令人難忘的書寫。」
——《舊金山紀事報》
名人推薦:★「莎莉.蒂思戴爾優雅低調的新書《行至生命盡頭》乍看是一本操作手冊,實際上卻是一本深刻的沉思錄。它乍看也是一本有關如何死亡,而事實上是有關如何活著的書。」
——大衛.薛爾德,暢銷書《真相渴求》作者
★「蒂思戴爾寫作的所有中心思維都與照料他人有關,而事實證明,這永遠是一個複雜又動人的主題。」
——蘿拉.馬爾許,《紐約客》
★「莎莉.蒂思戴爾是一個真正的典範。身為作家,她的思考像哲學家,觀察力像新聞工作者,而行文書寫像吟唱詩人。」
——梅格罕.東姆,《不可言說》一書作者
★「蒂思戴爾的長處...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危險的情境
現在:想像一下瀕死。隨自己的意願想像。你可以是在自己的臥室裡,在一座孤寂的山丘上,或在一家美麗的旅館中,怎麼樣都行。在哪一個季節?在一天裡的哪個時刻?也許你想要躺在夏日清香的草地上、看著太陽從海平線升起。想像一下。也許你想蜷縮在一張柔軟的床上,聽著莫札特或碧昂絲。你想要獨自一人嗎?有沒有你特別想要握著的手?你有聞到烤麵包的飄香味——或香奈兒十九號隱約的香氣嗎?請閉上雙眼,感受草坪,絲質床單,愛人的手,傾聽那持續的音符,跳一點舞,聞著麵包的香氣。想像這一切。
我沒死過,所以這整本書就是一個笨蛋的忠告。出生與死亡是人類唯一無法練習的行為。我們喜歡神祕的謀殺案,也熱愛電玩遊戲,但死亡,彷彿某種理論,在我們的面前森森逼近。在維多利亞時期,人們不容許孩童碰觸任何與性愛或生產有關的事,但他們可以坐在親友臨終的病榻上、目睹死亡並幫忙處理屍體。但現在,孩子可能會看著自己手足的誕生,卻從未看過一具屍體。其實多數大人都沒看過,很多人在自己走到生命盡頭之前,都未曾看過一個瀕死之人。
我七歲時,有一天,媽媽坐在餐桌旁哭了一整個下午,雖然那時已經快要聖誕節了。父親告訴我,外公過世了,我不大理解那是什麼意思。我喜歡外公,他很愛大笑,常常在吃飯時故意將整副假牙拿下來,嚇得我們這些小孩哇哇大叫。媽媽拿出皮箱,開始整理行李,父親說,她要去參加葬禮。我不懂什麼是葬禮,但是,假如媽媽是要自己一個人出門,那一定是很特別的事。「我也想去,可以嗎?」我問。「不行。」父親很嚴厲地說,他們不容許讓小孩子參加葬禮。沒有人跟我解釋原因,而我從此也未再見到外公。
長大後,我曾試圖要盡自己所能地看清死亡,那並不是我刻意的選擇,而是我的生命自然走上的道路。也許,多年前我外公神祕消失的影響與此有關。幾條不同的道路互相交錯,形成了現在的我,而從編織品(非碎布條)的角度來檢視我的生命,我看到了那些不同道路裡的相同處、那個共通的焦點。身為一個作家,我必需願意且毫不畏懼地探索自己和這個世界;身為一名護士兼臨終教育者,我也必需願意踏入他人的個別世界,走進他們的祕密裡去擁抱另一個人的痛苦。我是佛教徒,也是一位佛教導師,我經常帶領學員進行從佛教觀點為死亡做準備的討論會。而那樣的練習,對我如何創造自身的世界而言,需要一種無情的自我檢視和深刻的探索。在我面對人生無可避免的諸多變化時,那不同的道路所整合起來的力量賦予了我某種程度的鎮靜。它們為彼此提供養分,教我學會容忍各種歧異、各類不安以及親密關係——有時那是所有事情中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在想到死亡的種種狀況時,那些學習非常有幫助,而死亡在深化這些學習上也成為一種助力。在一個臨終者的床邊,我知道該怎麼做;當我們準備死亡或要失去我們所愛的某一個人時,我也知道該進行哪些處理。我最重要的經驗也是大部分的人都曾有的,那就是:所愛的人的死亡,我懂得悲傷。
靠著這些不同的技巧,我可以應對一個新的狀況,就好像一名電工初次進入一棟屋子時就能查覺它的管線那般。但是,即使死亡對我而言不陌生,我並不想讓人聽起來彷彿瀕死與死亡是很尋常的事。那些事情所教會我的,就是瀕死與死亡永遠都是極其特別的事。
當代佛學家片桐大忍禪師在死前寫了一本很了不起的書叫做《回歸寂靜》。他寫道:「生命是一種危險的情境。」生命,正是因其脆弱,才顯得如此珍貴。大師在書裡直言不諱自己生命正在逐漸消逝的事實。「瓷碗看起來那麼美麗,因為它遲早都會被打碎⋯⋯瓷碗的生命永遠存在於一個危險的情境中。」這就是我們的掙扎:那危險的美,那無可規避的傷口。我們忘了——我們多麼容易遺忘——愛與失去是親密的伙伴;忘了我們喜愛真花遠勝過塑膠花;忘了喜愛秋天短暫明亮的色彩和那籠罩在山坡上剎那即逝的曙光。而打開我們心房的,正是那脆弱和短暫。
小孩子不可以參加葬禮。我們藉由枝微末節及最細微的文字或表徵來學習。我在牧場和伐木場的地區裡長大,我父親是一名消防隊員。有人會死在磨坊裡、死於大火;有人會死在河流裡、深山裡或自己的牧場裡⋯⋯等意外經常發生。我小的時候,我們家在森林裡有一棟原始小木屋,每當夏日我們都會在那裡消磨幾個星期,我學會釣魚給自己做早餐。我喜歡檢查我在這裡或那裡發現的死掉的小動物。我從小就對屍體、活物等的知識充滿好奇,而那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我對掠奪和腐朽的探索。我養各種各類的寵物:我在山裡抓到的蜥蜴和蛇、我郵購而來的變色龍和螳螂、還有一次別人送我的一隻小鱷魚。我需要餵養我的寵物,而牠們大部分都喜歡活食,所以我就餵牠們蟋蟀、黃粉蟲、蚱蜢等。我喜歡蚱蜢,有時也會把它們當寵物飼養,但我仍然很開心地將牠們餵給螳螂吃。變色龍總是死掉,螳螂總是死掉,牠們的壽命都很短。那隻小鱷魚很快地也死了,我根本不知道牠需要什麼樣的食物。我試著用香油替牠做防腐,但沒有成功,我所做的大概只夠在「展示與敘述」的課堂裡做一次令觀眾難忘的演練罷了。有一次我的一隻烏龜死掉了,我跟弟弟把牠埋在媽媽的玫瑰花床的土裡,想要看看是否可以作出一個空的烏龜殼來,因為能有一個烏龜殼是蠻酷的事。但是幾個星期後,當我們把牠挖出來時,牠卻幾乎屍骨無存。那個看起來很硬、很堅實的龜殼結果竟只是另外一種血肉,而牠的腐化在我心裡留下了一股奇特又不安的感受,原來泥土比我想像的還要殘酷。外公死了,我們的狗死了。當我十四歲參加一位同學的葬禮時,我看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具人類屍體;那位同學是接下來幾年裡我幾個死掉的同儕中的第一個。有人告訴我,小孩子不可以參加葬禮,但那卻跟我暴露在死亡的面前不相干。
我在大學二年級時修了「解剖學與生理學」這門課。那是一整學年的課程,也是醫學預科生的必修課程。在實驗室裡,我們利用四具大體做練習,而那些大體都已經被大四的學生以不同的方式解剖過了。大體的臉部總是蓋起來的。我們的教授是威爾敦博士,他是一位身材高大、頭頂微禿、個性嚴謹的老師,擁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而他是不容許我們開任何玩笑的。我們在實驗室裡的時光總是安靜又嚴肅,我們會捧著各自的練習單,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在那些大體上查看各種線條、翻開不同標籤、檢查細緻的組織,學習所有人體的精密和複雜。我當時十七歲,對生物學很著迷,我也發現解剖學是一門偉大的奇觀。每一具大體裡的每一項細節多少都是相似的,相似到你幾乎可以精確地將最細微的結構畫下來。然而,那些大體中的每一具也是獨特的,而那一具具複雜的機械於不久前還在運作,或一直在運作——而那便是我所學到的課題之一。
我在「解剖學與生理學」這門課的實驗室裡是個麻煩精,後來並將麻煩帶進威爾敦教授的研究室裡。我用各種問題轟炸他,為了讓我閉嘴,他便交代了許多額外的作業給我。第二個學期時,他容許我做大體解剖,那表示我要在下課後進入上鎖的大體實驗室裡。那房間總是很陰涼且安靜,充滿甲醛的味道和屍體淡淡的皮革味。下面的窗戶都貼著紙以隔離外界窺探的眼睛,而房間裡灑滿了傍晚逐漸消散的陽光。威爾敦教授指定一具最新的屍體給我,上面的解剖才剛開始,而且全部集中在左手。他要我把肌腱和韌帶展露出來。日復一日,我拿著工具,一個人坐在放大體的桌旁,按照一本厚書裡的圖示,小心翼翼地將手剖開,我做得很好。我逐漸地瞭解那隻手和所有的手,直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但同時,我也瞭解到其他的事情。有一天,就在我快要完成肌腱的解剖時,我發現只要輕輕地拉那些肌腱,我便可以一根一根地扯動手指。在那個房間裡,我從未感到不自在,但那一天,我抬頭看著那整具除了臉部以外其他部分完全赤裸的屍體,我忽然間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對許多人而言,解剖是一種遠超過心智經驗的心理經驗。對我來說,兩者都是。比起背擴肌附著處的所有細節,我更清楚地記得跟死者在一起、碰觸並剖開一具屍體和檢查屍體的各種問題時的感受。跟大體一起工作,讓何謂死亡變得更明確清晰。一個主體變成了一件物體,一個活人變成了一具屍體。而,很神奇地,反過來看:這具屍體,這具結實、動也不動的物體是—曾經是—一個活人,一個有體溫、會呼吸的活人。一具屍體不是一件尋常的物體—絕不是一件尋常的物體。這件特別的物體,曾經是醒著的。
心裡一震,我忽然明白我正在切開的是一隻活生生的手,就像我自己的手:它曾經很柔軟,而且會動;它曾經握著筆、推過土、給孩子洗過澡、撫摸過某人的髮;它就像我自己這雙珍貴的手,而這雙手直到那一刻都還只不過是我身上的一部分而已,一種活生生的感受。我明白:這個人就跟我一樣。我當時就知道那具屍體就像我的身體,我能夠標記它的每個部位。但忽然之間,我明白那個人跟我一樣,就像有一天我也會跟那個人一樣。
我們對生命的必死性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社會性協議: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會選擇不去注意它。我在1957年誕生於美國,是最龐大的嬰兒潮中的一員。我們一直都是最幸運的一個世代,同時也是最虛幻的世代之一。我們費盡心力不想要變得跟我們的年紀一樣老、不想要看起來老或覺得自己老,而且,最重要的,不想要被別人發現老了。人們對理想的永保青春的不朽充滿崇拜,但這並不新鮮:古希臘人對不朽就十分癡迷,其實,所有的人類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但是我的世代似乎既比較免於衰老的事實,也比較不願屈服於它。我們從早到晚地忙碌、將心力專注於身體、我們的身體、我的身體上,卻不曾真正深刻地看待身體及其所隱含的一切意義。我們假裝我們所完全認知的事實,從某種角度來看,並不是真的。但那些討厭的各種意外不可能真正地被規避:最細微的靜脈屈張、腦頂禿掉的一小塊、老人斑、肌肉鬆弛等——用愛默生的話來說就是:「大自然的各種暗示與警告……是這麼地羞辱人。」我有時覺得迷惘: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似乎都淪陷在一個充滿各種減肥祕方、療法、形象塑造、尋求商標化的正念以解決一切麻煩、經常服用針對每一種情緒的藥物等的商業市場裡,彷彿⋯⋯怎麼?難道我們以為將這些都做了就能發生逆天奇蹟嗎?
我覺得很幸運能夠很早就與死者有所接觸,雖然我是因為自己早年的原因才去尋找他們。在大體實驗室學習後幾年,我因為在一家大型療養院當助手,安息的屍體再次變成了活生生的肉體。我家族中多數人都很長壽,幾乎每一個都頭好壯壯地活到九十幾歲。也許是因為我在成長的過程中見識過太多的曾祖父母、祖父母以及老邁的伯叔嬸等,因此我學會了不懼怕老人。他們老態龍鍾又鬆弛的肉體、滿頭銀絲、下垂的乳房、灰白的下顎等,都是我所熟悉的。他們就只是他們該有的樣子:跟我不一樣,非常不一樣,但沒有不好。沒有錯,也無遮掩,只是不同。
我觀察現在的護士助手,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做到的,那工作既辛苦,工時又長,而且報酬比你以為的一個文明社會所應該給付給這麼重要的工作的少很多。當時我很喜歡那個工作:我有一件制服,人生第一次領薪水;我也正在談戀愛,全身充滿無盡的力量。我在那個工作裡所學到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與該專業有關的文化、專門術語及信仰體系。一開始,我學的是護理脆弱的人所需的特別技巧,也就是照顧虛弱者的例行公事。幫一個睡在床上的人鋪床、幫一個無法自理的人洗澡、幫一個無法行動的人放進移出他的輪椅等,這些都是有正確方式的。在那個工作裡,我第一次目睹死亡並幫忙清洗死者的遺體,同時學習到清洗遺體也是有正確的步驟的。然而,在那幾年裡,我不記得有任何時刻曾單純清晰地明白這個老人或那個瘦小皺巴巴的老婦也曾經跟我一樣青春瀟灑過。當時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也會跟他們一樣,就像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跟我的姑祖母露易絲一樣。當時的我皮膚光滑、充滿活力,而且熱愛那份工作,除此,我並未想到其他事了。
當我決定要當個作家時,我知道我得找個固定工作,一個跟寫作無關的工作以維持生計。護理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工作時間有彈性,薪水不錯,而且可以兼職。但讓我驚訝的並不是那個工作及其訓練比我所預想的要艱難許多:那是任何行業的入門者都必需學習的功課。我不曾預料的驚奇是,以如此具體的方式照顧他人的身心,其最終竟都無可避免地滲進我自己的人生裡。我當時太年輕,不知道我所從事的工作跟那些遺體一樣,會影響我看待自己的生命和身體的方式。我當時太年輕,不明白自己有多年輕。
三十幾年後的現在,我一周幾天在一個安寧療護機構工作,照顧患有嚴重慢性疾病的病人。我看到活得不錯的堅毅老人和比我年輕卻脆弱的人。那些患者中,每年約有五分之一會死亡。我負責的患者遍布整個城市,有的住在公寓裡、在拖車裡、在失智中心、在生活輔助住宅區、在成人寄養家庭等各種國家機構裡。像我照顧的那種患者,全世界到處都有,怎麼可能沒有呢?我忘了生命的這一部分是如此深藏不露,因為當我去工作時,那就是我所處的地方:在老人失智中心,真的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在一個小小的屋子裡,五個非常年長的婦人由幾個較年輕的婦人照顧著;在某棟生活輔助大樓裡,每一戶公寓都是一個長壽老人的小宇宙。
但是,曾經有許多年,我忘了我就像那個手有如一朵玫瑰花般被我剖開的人。假如我們夠幸運,我們便能從中學得一點點。我忘了我也會變老,並且會失去那曾經似乎完全屬於我的力量,那曾經容許我忙碌和豐收、養育三名子女、在晚間寫書且隔天仍能早起出門工作的力量。在年輕的歲月裡,當我想到死亡的時候,我並不是很以為然。當然,病人有時候會死亡。我不認識的人死掉了—新聞報導裡的人、醫院裡的人、街上的人等。我年紀較老邁的親戚也開始死亡,一個接一個,但是他們畢竟真的很老了。
當我二十幾歲剛完成護理學校的課程時,我便開始學習曹洞宗禪學。這本書不是一本有關佛教徒如何邁向死亡的書,但我的生命因受到佛教的影響而深刻,因此我會時常借用它的語彙並回歸它的指引。佛教徒所學的第一個故事——根的故事——就是歷史上的佛陀悉達多的故事。他是一個深受寵愛的王子,成長過程中受盡小心翼翼的呵護,從未看過任何痛苦的景象。有一天,他很煩躁不安,刻意躲開護衛的追隨後,他看到了前所未見的幾件事:一個病人、一個老人和一具屍體。他的隨從告訴他,那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過程,每一個人都一樣。對年輕的王子來說,那是什麼樣的震驚!每一個人都無法避免嗎?我呢?然後他遇見了一位苦行者,一個為了追尋知識而遠離塵世的宗教實踐者。王子那時便知道自己生命的任務就是要去瞭解變化之必然性的意義。(在這個故事的另一些版本裡,那些可怕的景象是上天安排的,目的就是為了刺激他去尋找人生的啟迪。)
佛教的修習要求一個人要勇敢地去面對生命中所有粗硬的事實:我們一直在變化,我們永遠都會有一些不滿足,我們拼命地想要掌握住自己所擁有的,我們都是受著苦、早晚會死的平凡人。我們會改變,而每一件事情、我們所愛的每一個人也都會改變。以下是一則古老的佛教冥想,道理很簡單:我本來就會變老;我本來就會生病;我本來就會死掉。我所珍視的一切和我愛的每一個人本來就會改變,要與他們永遠不分離,根本是不可能的。過去幾千年來,佛陀的故事在無數人們的心中引起深刻的共鳴,因為那也是我們自己的故事。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早晚都會有這樣的一種顯現:病、老、死。也許那個病人痊癒了,也許那個老者只是一個陌生人,也許那具屍體被人謹慎處理後躺在教堂裡的一副昂貴的棺材裡,但是,事實就是事實。在某一刻,你會想著:我呢?我也是嗎?然後你或是不想再面對那個念頭,或是開始要尋找一個解釋,而無論哪種方式,該出現的自會有它來臨的時候。
我們生命中經常出現的念頭之一便是:會有明天。明天,也許我會把髒衣服都洗了;明天,我再來計劃我的退休生活;明天,我要開始過暑假。然而,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危險情境的話,那麼我們根本沒有明天、沒有明年,只有當下。誠然,我們總是會做計劃,除了播下種子等待開花結果,我們也沒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洗衣服或退休或明年的暑假。弔詭的是,我們一邊做著明年的暑假計畫、一邊又明白誰也不能保證我們會有明年的夏天。這種無常正是我們生命中痛苦和喜悅的關鍵。能接受萬事萬物的本相是多麼根本的事!「我們為什麼要用特別的方式對待自己呢?」鈴木俊隆問。「當你瞭解所謂的生與死就是萬事萬物——植物、動物、樹木等——的生與死時,它就不再是個問題了。對一切事物的問題,都不再是個問題。」一張桌子之所以是一張桌子,是因為它的形狀及我們使用它的方式,因為旁邊還有一張椅子,也因為我們稱它為桌子。我們可以
將一張桌子拆卸開來,到某個程度後它就不再是一張桌子了。即便所有的部分都還在,那張桌子已經不見了,因為只要無法全部拼湊起來,它就無法成為一張桌子。而我就像這張桌子,你也像這張桌子,萬事萬物都像這張桌子。這樣的認知可以替我們創造一個我們能存活於其中的巨大空間,一種生命的自由。對所有人的那個問題,都不再是個問題。我們都會腐壞,就如同其他一切—多美麗,多甜蜜,多艱難!
千古以來人們一直在盡己所能地想要知道死亡的本質。有關於死亡的現代文學一定不會讓我們忽略了在一般對談中極少被提及的西塞羅:「做理性闡述便是為死亡做好準備。」那一股衝動就是稍微倚靠歷史、再添加脈絡、然後創造出一幅較大的圖像來。但是,我們真的需要給這個對談添加分量嗎?偶爾,我也會這麼做—仰賴另一個人的文字。也許我只是在提醒自己:我們所有的問題其實早就都已經被問過了。在我所帶領的討論會裡,同樣的問題每一次都會被提出來:痛苦、尊嚴、恐懼等很老掉牙的問題。我們要如何為一個如此神祕、如此不可捉摸的事情做準備呢?我們要如何替未知做決定?當我們都還不確定我們是否相信其存在時,我們又如何為那不可避免的事做準備?
當我們談到死亡時,總彷彿它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也許在某個夏日的夜晚,當空氣很清新而我們健康的孩子都乖乖地坐在我們腳邊牙牙學語時,我們一邊喝兩杯、一邊隨意地談著、想像著我們希望自己是怎麼死的。我們談到死亡、什麼時候死,似乎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可以如此隨意地思忖著。
看看你周圍的空間,現在就看。無論你身在何處:辦公室、地鐵站裡、自家的客廳。請看看四周、仔細地看著你所能看見的每一件事物。你將在一分鐘內死掉。就這樣,沒有時間去尋找那甜蜜的夏日草坪或你最喜歡的愛黛兒的歌。沒有手可以握,沒有時間打電話或寫紙條。你在此時此地所看見的——這個季節、這些人、這一天、這樣的光線、這個空間——就是你的所有。
我的朋友卡洛一輩子很少生病,她甚至沒有感冒過。她是奧勒岡州某地區的刑事律師。當她競選州郡法官一職時,她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到處敲門、向選民們介紹自己。就在她當選揚希爾郡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法官的前夕,她的左腳覺得麻木。她以為是神經挫傷,因為走太多路或一直穿著不合腳的鞋。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說:「我得了癌症。」沒有開場白,只有流不完的淚水。無論怎麼看,我們的身體都是一個非常精密複雜的自體調節系統。但我們的體內也有無法估量的變數,而且,當它們發生時,絕大多數都是靜悄悄的:呢喃的動脈瘤、隱形的栓子、正在死亡的細胞、細胞分裂等。卡洛前一個夏天做的定期乳房X光攝影告訴她沒事,但現在她得了轉移性乳癌。她左腳的痠麻是因為腹部腫瘤壓迫脊椎所造成的。
得了絕症的人會把對死亡的認知視為一種界線來討論。生命被劃分為他知道——真的知道——自己即將死亡的時間之前和之後。當我們穿越理論與事實之間的邊界時,那一日就會到來。剛開始,人們通常會頗務實地面對。保羅‧卡拉尼堤被診斷出患了肺癌時,他是一位神經外科醫生,和太太露西一起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兩人坦率地談著後事。「我告訴她要再婚,跟她說我不願意她孤獨一人。我跟她說我們要馬上重新處理房子的貸款事宜。」這種暫時性的接受、這種面對死亡的意願,是很普遍的;也許那是一種保護作用,一種來自能夠緩和那類震驚的腦內啡的作用。卡洛後來告訴我,她以為她也許再也不能走出醫院了。當時她很鎮靜,躺在她的私人病房裡,轉頭看著窗外朝西那邊她最愛的沿海山巒,太陽光灑在她的病床上,而她也容許自己成為一個忽然得病的病人:不是一名律師、不是一名法官或妻子、或愛狗人士,只是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我們談著她的切片檢查、她的選擇、她的幾隻愛犬以及牠們將來何去何從。
如同腦內啡,這樣的接受很快就會消褪。卡洛接受了手術,恢復了,宣誓就職法官,並且熱情地投入工作。她對化療的反應良好,之後又活了幾年。她做盡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盼望能不死,但那整個期間她一直都在面對死亡。她知道,我也知道。每一天都是浩劫之後。
這是一本有關如何為你自己的死亡以及與你親近之人的死亡做準備的書。我要談的是這兩種經驗,因此有時候我會把你當作探視者或瀕死者所愛之人在談這件事;有時候我也會把你當作瀕死者在談這件事(我總是在跟自己談論。)在西方,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年邁時因慢性病而死亡,而那些疾病絕大多數都是在幾個月或幾年之內造成我們的衰頹、使我們逐步邁向死亡的因素。我在這本書裡所要說的,便是針對這個事實,也就是:你和我都可能因為生病一段時間後死亡,而在我們自己的死亡發生之前,我們都會先看到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以這樣的方式去世。但是,我曾經看過很快就斷氣的人,我也看過有人在一剎那間就往生了。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思索死亡、尤其是自己的死亡(我?真的?)——如果我們能夠熟悉死亡這個事實——那麼,幾分鐘就夠了。我們從幾千個燦爛的時刻裡知道,時間是如何變快、又是如何變慢的。假如我們能準備好直截了當地面對,那麼或許五秒鐘就夠了。我們一輩子都在創造自己的未來,透過創造自己的習性,我們從經驗學習並檢視自己的弱點和長處。我們如何過自己的每一天,就會創造出我們在死亡時的那一刻是怎樣的人。在一個瀕死的人的床邊,你會見證到這個;在一具屍體安息或掙扎的樣子裡、在一個人臉部的線條裡、在一個微笑或怒容、憂慮或平和的模糊的影子裡,你都會見證到這個。隨著每一天的消逝,我們都在創造我們自己將會有的那種死亡。
第一章 危險的情境
現在:想像一下瀕死。隨自己的意願想像。你可以是在自己的臥室裡,在一座孤寂的山丘上,或在一家美麗的旅館中,怎麼樣都行。在哪一個季節?在一天裡的哪個時刻?也許你想要躺在夏日清香的草地上、看著太陽從海平線升起。想像一下。也許你想蜷縮在一張柔軟的床上,聽著莫札特或碧昂絲。你想要獨自一人嗎?有沒有你特別想要握著的手?你有聞到烤麵包的飄香味——或香奈兒十九號隱約的香氣嗎?請閉上雙眼,感受草坪,絲質床單,愛人的手,傾聽那持續的音符,跳一點舞,聞著麵包的香氣。想像這一切。
我沒死過,所以這整...
目錄
1.危險的情境
2.抗拒
3.善終
4.溝通
5.最後幾個月
6.要在何處過世?
7.最後幾週
8.最後幾日
9.那一刻
10.遺體
11.哀慟
12.喜悅
附錄
1.死亡計畫書
2.預設醫療指示
3.器官與組織捐贈
4.協助死亡
銘謝
1.危險的情境
2.抗拒
3.善終
4.溝通
5.最後幾個月
6.要在何處過世?
7.最後幾週
8.最後幾日
9.那一刻
10.遺體
11.哀慟
12.喜悅
附錄
1.死亡計畫書
2.預設醫療指示
3.器官與組織捐贈
4.協助死亡
銘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