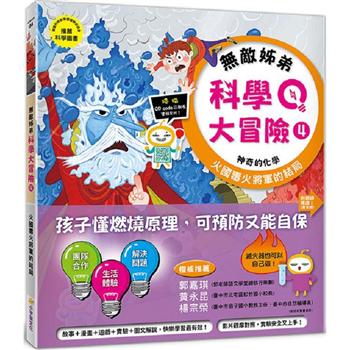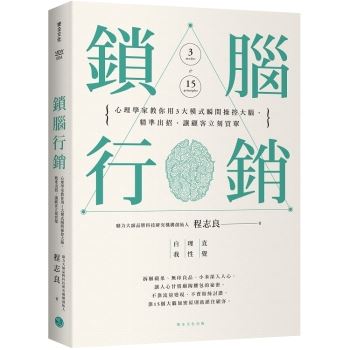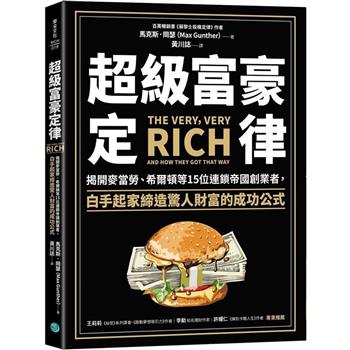在深巷的角落,富士山圖案的珠簾伴著風鈴聲聲搖曳。
這只是一間有著淡淡醇味,讓你放鬆身心的小店。
或許有一天,你也會在這裡發生屬於你的故事。
這只是一間有著淡淡醇味,讓你放鬆身心的小店。
或許有一天,你也會在這裡發生屬於你的故事。
我希望這是一間有著淡淡溫馨的店,
讓每個踏進來的人
都可以覓得生活中的一絲放鬆。
街角的小小角落,坐落著一間靜謐的居酒屋,
悠揚的老歌在空間裡漂浮,撩動著每夜每人的思緒。
來來去去的顧客帶來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或是甜美,或是壓抑,
但是在這裡,他們能夠用自己最愜意的方式抒發自己。
凱面對著感情,在忍受精神病痛的折磨之餘,又該如何追尋自己的幸福?
Slyvia在不經意間陷入漩渦,又該如何面對被她拉扯下來的另一位?
蕭將心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最後又該如何做出最重要的決定?
放下酒盞,在品嘗過一晚的人生暢意與苦澀之後,歡迎您再度光臨。
我的夢想是開一間給人感覺舒悅的店面,這個店面不一定要大、但我希望它能夠給人溫暖,而且,是要無限大的溫暖,好讓所有惱人的字眼都從這裡消失,生活上的壓力不要走入這裡。
這是個妄想。我知道這是妄想卻依舊願意努力嘗試。重新裝潢了離東區市街不遠的小巷子底,一間不起眼店面,我的能力也許無法將這店面撐住太久,但每過一天就是寫下一頁歷史;不僅是我自己的紀錄,也記錄了來店的各種人士面容,有些是我的舊友、有的僅是第一次見面,我或許無法從中吸取太多世事變遷,也至少,充實了我處於空虛的寂寞心靈。
是的,我開了間居酒屋,一間與這塊地方格格不入的居酒屋。
許多故事也就從這裡開始。
本書特色
純愛小說作者幕後黑手的另類愛情之作,與青澀的校園戀愛不同,伴著醇酒芬芳與老歌音響,在深夜的居酒屋裡看見來來去去的一對對有緣人,不論他們是否能夠牽手直到永遠,都是一段人生的記憶。


 2015/11/19
2015/11/19 2015/11/17
2015/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