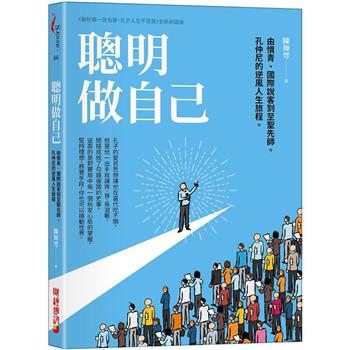詩人阿米最新創作,以最純粹直接的詩的語言,描寫真實人生的挫敗與成長、義無反顧的愛情,一語擊中心靈的最深處。
「交錯衝撞又不能解決的事象,阿米不分辨也不分析,直接進入。讓我們到達一個無解的迷宮,讓我們去體會萬物被創造之始的森嚴,因為阿米詩句之間從來不是軟弱妥協的。那兒有股強韌的生的呼喚,無形地,鼓動我們。那些道理,因為謎一般的事象,需要不斷重整。她說上帝也有張開眼睛的第一刻,那深刻的瞬間又跌入無間地獄,如海一般的錯愛。她說我們最後的死,像一個甜甜圈,炸得金黃、灑滿糖霜。(〈紀念日〉)」--翁文嫻
本書特色
「阿米的眼神沉靜,能將驚濤駭浪化成某些本質,而生出她的領悟。」--翁文嫻〈阿米轉動世界〉專序推薦
專家推薦
翁文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昨日痛苦變成麥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華文現代詩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現代詩 |
$ 252 |
華文現代詩 |
$ 252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280 |
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昨日痛苦變成麥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阿米
1980年次,台灣女詩人和畫家。
自2009年起,作品大量刊登於《衛生紙+》。
2011年第一本詩集《要歌要舞要學狼》入選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同年舉辦她的第一個畫展。
2012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慾望之閣》。
2012年與黑眼睛跨劇團合作,擔任音樂劇作詞人。
2013年出版與潘家欣往來的詩歌書信詩集《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
2013年出版中英圖畫詩集《日落時候想唱歌》,收錄2009至2013年間的畫作。
2013年策展「公寓秀-請按電鈴」,邀請12位年輕與壯年詩人在公寓內展出私物件,包括畫作,手稿,日記,襪子,t-shirt......並連續舉辦「衛生紙沙龍」包括戲劇表演與講座。
2014年舉辦第二次油畫個展「澆花」。
2014年與碧娜‧鮑許學生賴翠霜合作,親自改編《慾望之閣》第一章內容,由賴翠霜編成兩支各20分鐘長度的現代舞碼〈屋簷下〉、〈獨角戲〉。
2015年出版成人童話圖文詩集《我的內心長滿了魚》。
目前與金曲獎得主李哲藝合作音樂專輯,擔任作詞人。
阿米
1980年次,台灣女詩人和畫家。
自2009年起,作品大量刊登於《衛生紙+》。
2011年第一本詩集《要歌要舞要學狼》入選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同年舉辦她的第一個畫展。
2012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慾望之閣》。
2012年與黑眼睛跨劇團合作,擔任音樂劇作詞人。
2013年出版與潘家欣往來的詩歌書信詩集《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
2013年出版中英圖畫詩集《日落時候想唱歌》,收錄2009至2013年間的畫作。
2013年策展「公寓秀-請按電鈴」,邀請12位年輕與壯年詩人在公寓內展出私物件,包括畫作,手稿,日記,襪子,t-shirt......並連續舉辦「衛生紙沙龍」包括戲劇表演與講座。
2014年舉辦第二次油畫個展「澆花」。
2014年與碧娜‧鮑許學生賴翠霜合作,親自改編《慾望之閣》第一章內容,由賴翠霜編成兩支各20分鐘長度的現代舞碼〈屋簷下〉、〈獨角戲〉。
2015年出版成人童話圖文詩集《我的內心長滿了魚》。
目前與金曲獎得主李哲藝合作音樂專輯,擔任作詞人。
目錄
阿米轉動世界/翁文嫻
【第一章 妹妹的床頭歌】
海產
媽媽—和吾友蔚昀
回到正常的世界
年夜菜
雞蛋糕
活小孩
父親是寫實的
全家福
丈夫
慈父
剎那
秋日發票
記姪女第一次住院
棉花糖
我妹妹
妹妹的床頭歌
五樓
失去/我有
為什麼甜美總是帶著哀傷
兒時記憶
【第二章 沉默麵包店】
病與藥
失眠
驗傷
遠足
小羊之歌
沉默麵包店
杜鵑-致精神病患
不寫
夏天
雨後
吃麵的臉
黑色可愛-寫給草間彌生
擺渡
聖誕節過後
【第三章 女囚徒】
在旅行中遺失一只鞋子
螺絲-致詩人范家駿
即興音樂
默丑畢費
疑問集-Fb「要歌要舞要學狼」社團接力詩
一邊厭世一邊活
日常
煙火
為女囚讀詩
逐漸傍晚的歌聲-聽Elena Frolova
阿茲海默
紀念日
我是:羊一般幸福雨一般憂傷
消失
一天
相信
【第四章 不寫作的春天】
我沒有臉
致普拉斯
純潔
花痴
愛經
我恨安琪拉
你忙音樂盒
戀人指南
繼續去遠方
只有哭一下下
小確幸
聽說
抑鬱或者愛
晚餐
早安
終將
未來
年
冬天
我和先生的故事
愛人風景
純情派
沒有永遠的
【第五章 小島夫人】
小島夫人
【第六章 重要書】
當代樹人
寫給兒童
文林路
請停下來聽我說
一個三分鐘的故事
寫給查理周刊的
一首詩
紀念林冠華
【第七章 這麼美 這麼短】
月光
沒有我的一張畫
日子
女朋友
摺紙鶴
反光
飛魚
龍
櫻花
寫作練習
生活
情詩與哀歌
【第一章 妹妹的床頭歌】
海產
媽媽—和吾友蔚昀
回到正常的世界
年夜菜
雞蛋糕
活小孩
父親是寫實的
全家福
丈夫
慈父
剎那
秋日發票
記姪女第一次住院
棉花糖
我妹妹
妹妹的床頭歌
五樓
失去/我有
為什麼甜美總是帶著哀傷
兒時記憶
【第二章 沉默麵包店】
病與藥
失眠
驗傷
遠足
小羊之歌
沉默麵包店
杜鵑-致精神病患
不寫
夏天
雨後
吃麵的臉
黑色可愛-寫給草間彌生
擺渡
聖誕節過後
【第三章 女囚徒】
在旅行中遺失一只鞋子
螺絲-致詩人范家駿
即興音樂
默丑畢費
疑問集-Fb「要歌要舞要學狼」社團接力詩
一邊厭世一邊活
日常
煙火
為女囚讀詩
逐漸傍晚的歌聲-聽Elena Frolova
阿茲海默
紀念日
我是:羊一般幸福雨一般憂傷
消失
一天
相信
【第四章 不寫作的春天】
我沒有臉
致普拉斯
純潔
花痴
愛經
我恨安琪拉
你忙音樂盒
戀人指南
繼續去遠方
只有哭一下下
小確幸
聽說
抑鬱或者愛
晚餐
早安
終將
未來
年
冬天
我和先生的故事
愛人風景
純情派
沒有永遠的
【第五章 小島夫人】
小島夫人
【第六章 重要書】
當代樹人
寫給兒童
文林路
請停下來聽我說
一個三分鐘的故事
寫給查理周刊的
一首詩
紀念林冠華
【第七章 這麼美 這麼短】
月光
沒有我的一張畫
日子
女朋友
摺紙鶴
反光
飛魚
龍
櫻花
寫作練習
生活
情詩與哀歌
序
推薦序
【阿米轉動世界】
2011年台文館金典獎,在當年新出三十幾本詩集內要選出三本,記得曾極力推薦阿米,作為第二名。理由是:「我讀阿米的作品,有讀到比較痛的東西,表面上的童真,只寫表象、可愛的事物,可是裡面藏著很多社會的指涉,很多恐怖的事……」
又過了四年,台灣社會是愈來愈恐怖,那些傷殘殺戮總是從「家」開始。阿米的第五本詩集〈妹妹的床頭歌〉系列,就寫出她的家;〈女囚徒〉、〈沉默麵包店〉系列,到處都是社會上畸零的人。報紙上版面評論,其實已很少能回應這些崩壞的生存實況,社會裡的抑鬱直接反映在詩。阿米第一本詩集《要歌要舞要學狼》,是「吹鼓吹詩人叢書」的選詩,主編蘇紹連稱,她「詩中觸及人類生命中的醜陋、缺陷、病痛、惡行、悲傷、野蠻、憂患等,都能淡淡地流露著詩意的美感」,「不管寫什麼,總有一股優雅的氣質。」我很喜歡蘇主編用「優雅」二字去涵蓋她筆下的爛泥人生。
阿米邀我寫序,詩集反覆讀了十次以上。只要心一靜下,詩句就一直吸著我,重複唸也不厭煩好像第一次讀。這經驗倒是奇怪的,不斷讀這些惡事,頹敗的社會性漸漸淡去,我們不會為了同情,或為了抗議為了任何的關心可以反覆生出新鮮感。阿米詩句應該是些別的,我覺得她已超過了上面一般人對這類事件的反應,或許是過了許久,捱受太多,於是她來到另外的一片泥層。
在「另外」的境地上,以前肉身感覺疼痛的事,換了一個時間維度,另個距離的空間,人可以再正常的滋長愛意,如此,讀者被慢慢吸進阿米的世界。
例如寫那位「日復一日打媽媽」的父親:
父親很狡滑
我來不及替母親復仇,
他便老了,要人把屎把尿
初看,以為詩人的父親已經老成這樣,你還要報仇嗎?多讀幾首,父親可有各種年齡面相。例如另一個爸爸,他只終日與電視情婦寶多見面:「寶多渾圓多肉/爸爸打著節拍/寶多滿屋子跑」。這樣的老人充滿精力,可惜孤獨得只與一台電視做情婦,真是滑稽。阿米詩沒有虛擬遙遠意象,人物行為是我們日常的,只是她可以不知不覺地,推著「轉經輪」似的,轉動她的世界。
新聞或友朋左右發生的事,可以成為阿米親身經歷的事,她感同身受,若果她有原諒,我們就一同被她原諒。〈慈父〉詩內,見到一名長期受家暴的女兒,看見父親老去的畫面,終於說出:「父親沒有變/他一直都是/慈祥的」。需要過好多年、有好多智慧,才能說出父親一直都是慈祥的,但不等於忘記:「只是/他伸手/打了母親」。
阿米的眼神沉靜,能將驚濤駭浪化成某些本質,而生出她的領悟。詩最後一段:「我是一隻僵掉的小蟲/需要取暖」。人的理解力並不能消滅悲哀的記憶。時光是什麼?在阿米詩內,親人的糾纏暴戾有若更深深轉入的愛,沒有這些刻骨的創傷就沒有愛。像螺絲,旋轉入這疼痛的人生,木板的痛苦與喜悅,又是那麼真實。(〈螺絲〉)
阿米的句子非常乾淨,她令我們心無旁騖,不沾惹不必要的事物,對於真正重要的,毫不避諱、毫無疑問,褪盡俗氣與成見地表達,常有意外的神來之筆,安撫我們體內的雜亂之氣。不是說她詩有多幸福的情節,剛相反,她寫的是人生的挫敗,例如寫一個家庭破碎了:「大型家具一件一件搬出來/床組、櫃子、桌椅/再來是柔軟的家飾品/窗簾、桌巾、棉被」……全部搬光了,忽然看到這景象:
屋子空曠起來
陽光之下的灰塵
是突然顯眼的愛情
愛情從未出現過這種寫法吧?但愈想又愈有理由。人在一切皆無中,重新品味那些被光照亮的塵埃,每粒微塵曠大,是已逝的、飛動流竄的情。
於是,阿米帶我們去一個五味雜陳的世界,人在那兒,有如草間彌生的圓點畫:我們五彩繽紛、面容毀壞,我們不斷地想死、創作、活到七老八十(〈黑色可愛〉)。也猶如她寫的,一名吃麵的男人:沒有人知道他,吃麵的臉,看起來疲倦,使人想摸(〈吃麵的臉〉)。
交錯衝撞又不能解決的事象,阿米不分辨也不分析,直接進入。讓我們到達一個無解的迷宮,讓我們去體會萬物被創造之始的森嚴,因為阿米詩句之間從來不是軟弱妥協的。那兒有股強韌的生的呼喚,無形地,鼓動我們。那些道理,因為謎一般的事象,需要不斷重整。她說上帝也有張開眼睛的第一刻,那深刻的瞬間又跌入無間地獄,如海一般的錯愛。她說我們最後的死,像一個甜甜圈,炸得金黃、灑滿糖霜。(〈紀念日〉)
諸如此類,阿米不知用什麼來源的力,重新轉動了她的世界。我甚至愛上了她的歪理,例如〈驗傷〉這一首:「你掐住我的脖子/不是故意的呀/一定是因為太愛了吧 我很痛/發出嘶嘶的聲音」(〈驗傷〉)
愛情有多少種形容?我喜歡阿米能寫出那種嘶嘶的聲音,在愛裡受傷的聲音。本詩集《昨日痛苦變成麥》,有完整的一組愛情詩:「不寫作的春天」。阿米重新為愛去畫圖,是非常遼闊有氣勢的一張藍圖。你們看這愛的宣言:
多年來我一直在睡覺
你一次驚動了
全部的我
「全部的我」,有約翰、瑪莉、莎兒......「那些人格的鬥爭,我一概否認」,這種愛就很來勁了。今天廿一世紀的台灣女子,如何認識?要看阿米塑造的像──這位女子是經過大風浪的:她產生一種人格的特質。是愛,驚醒了身上各種事物,因為愛,引出各個真實的門,去觸摸去打開,它們彼此相撞,但愛是無方位無認定,也是無辜的。只有一股源源不絕,要熔化融匯萬種恆河沙數的力。奇怪的阿米甚至將《金剛經》的句子轉成〈愛經〉。
我是一切虛空中為你倒吊的精靈,我是無法離欲的妒婦
這名充滿愛欲的女子創造出她男人的情婦〈我恨安琪拉〉;創造出想吞噬她甜蜜順境的霉運〈我和先生的故事〉。她愛得很不安寧,有一百種不可能愛的畫面,總見到「那個可惡的女人,和你的孩子,像甜甜圈一樣站在一起」,啊但同一首詩的結局我們又看見:「我這樣一個野孩子/只有你的懷抱/讓我明白/靜止不動/的一種乳白色」(〈愛人風景〉)。
阿米用痛苦經歷開展出《金剛經》的真義:愛與欲沒有定義、愛與痛同等深沉、愛可以產生一百種不平靜的理由,但我們會被阿米在九種苦難之後第十個小小的話語角落,感動而哭。她這首〈沒有永遠的〉,說:
不必說再見
因為沒有永遠
沒有永遠的親人
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悲喜
沒有永遠的存款
沒有永遠的學歷
沒有永遠的體重
沒有永遠的熱吻
即使如此
還是小跑步靠近你
用盡所有的力氣讓你明白:我是一個愛你的小孩
歷盡劫難之後的詩人,阿米意識到在愛的滋潤下,可以碰觸到,如沙特說的:人類深不可測的自由,那兒有廣大宇宙的動能。
【阿米轉動世界】
2011年台文館金典獎,在當年新出三十幾本詩集內要選出三本,記得曾極力推薦阿米,作為第二名。理由是:「我讀阿米的作品,有讀到比較痛的東西,表面上的童真,只寫表象、可愛的事物,可是裡面藏著很多社會的指涉,很多恐怖的事……」
又過了四年,台灣社會是愈來愈恐怖,那些傷殘殺戮總是從「家」開始。阿米的第五本詩集〈妹妹的床頭歌〉系列,就寫出她的家;〈女囚徒〉、〈沉默麵包店〉系列,到處都是社會上畸零的人。報紙上版面評論,其實已很少能回應這些崩壞的生存實況,社會裡的抑鬱直接反映在詩。阿米第一本詩集《要歌要舞要學狼》,是「吹鼓吹詩人叢書」的選詩,主編蘇紹連稱,她「詩中觸及人類生命中的醜陋、缺陷、病痛、惡行、悲傷、野蠻、憂患等,都能淡淡地流露著詩意的美感」,「不管寫什麼,總有一股優雅的氣質。」我很喜歡蘇主編用「優雅」二字去涵蓋她筆下的爛泥人生。
阿米邀我寫序,詩集反覆讀了十次以上。只要心一靜下,詩句就一直吸著我,重複唸也不厭煩好像第一次讀。這經驗倒是奇怪的,不斷讀這些惡事,頹敗的社會性漸漸淡去,我們不會為了同情,或為了抗議為了任何的關心可以反覆生出新鮮感。阿米詩句應該是些別的,我覺得她已超過了上面一般人對這類事件的反應,或許是過了許久,捱受太多,於是她來到另外的一片泥層。
在「另外」的境地上,以前肉身感覺疼痛的事,換了一個時間維度,另個距離的空間,人可以再正常的滋長愛意,如此,讀者被慢慢吸進阿米的世界。
例如寫那位「日復一日打媽媽」的父親:
父親很狡滑
我來不及替母親復仇,
他便老了,要人把屎把尿
初看,以為詩人的父親已經老成這樣,你還要報仇嗎?多讀幾首,父親可有各種年齡面相。例如另一個爸爸,他只終日與電視情婦寶多見面:「寶多渾圓多肉/爸爸打著節拍/寶多滿屋子跑」。這樣的老人充滿精力,可惜孤獨得只與一台電視做情婦,真是滑稽。阿米詩沒有虛擬遙遠意象,人物行為是我們日常的,只是她可以不知不覺地,推著「轉經輪」似的,轉動她的世界。
新聞或友朋左右發生的事,可以成為阿米親身經歷的事,她感同身受,若果她有原諒,我們就一同被她原諒。〈慈父〉詩內,見到一名長期受家暴的女兒,看見父親老去的畫面,終於說出:「父親沒有變/他一直都是/慈祥的」。需要過好多年、有好多智慧,才能說出父親一直都是慈祥的,但不等於忘記:「只是/他伸手/打了母親」。
阿米的眼神沉靜,能將驚濤駭浪化成某些本質,而生出她的領悟。詩最後一段:「我是一隻僵掉的小蟲/需要取暖」。人的理解力並不能消滅悲哀的記憶。時光是什麼?在阿米詩內,親人的糾纏暴戾有若更深深轉入的愛,沒有這些刻骨的創傷就沒有愛。像螺絲,旋轉入這疼痛的人生,木板的痛苦與喜悅,又是那麼真實。(〈螺絲〉)
阿米的句子非常乾淨,她令我們心無旁騖,不沾惹不必要的事物,對於真正重要的,毫不避諱、毫無疑問,褪盡俗氣與成見地表達,常有意外的神來之筆,安撫我們體內的雜亂之氣。不是說她詩有多幸福的情節,剛相反,她寫的是人生的挫敗,例如寫一個家庭破碎了:「大型家具一件一件搬出來/床組、櫃子、桌椅/再來是柔軟的家飾品/窗簾、桌巾、棉被」……全部搬光了,忽然看到這景象:
屋子空曠起來
陽光之下的灰塵
是突然顯眼的愛情
愛情從未出現過這種寫法吧?但愈想又愈有理由。人在一切皆無中,重新品味那些被光照亮的塵埃,每粒微塵曠大,是已逝的、飛動流竄的情。
於是,阿米帶我們去一個五味雜陳的世界,人在那兒,有如草間彌生的圓點畫:我們五彩繽紛、面容毀壞,我們不斷地想死、創作、活到七老八十(〈黑色可愛〉)。也猶如她寫的,一名吃麵的男人:沒有人知道他,吃麵的臉,看起來疲倦,使人想摸(〈吃麵的臉〉)。
交錯衝撞又不能解決的事象,阿米不分辨也不分析,直接進入。讓我們到達一個無解的迷宮,讓我們去體會萬物被創造之始的森嚴,因為阿米詩句之間從來不是軟弱妥協的。那兒有股強韌的生的呼喚,無形地,鼓動我們。那些道理,因為謎一般的事象,需要不斷重整。她說上帝也有張開眼睛的第一刻,那深刻的瞬間又跌入無間地獄,如海一般的錯愛。她說我們最後的死,像一個甜甜圈,炸得金黃、灑滿糖霜。(〈紀念日〉)
諸如此類,阿米不知用什麼來源的力,重新轉動了她的世界。我甚至愛上了她的歪理,例如〈驗傷〉這一首:「你掐住我的脖子/不是故意的呀/一定是因為太愛了吧 我很痛/發出嘶嘶的聲音」(〈驗傷〉)
愛情有多少種形容?我喜歡阿米能寫出那種嘶嘶的聲音,在愛裡受傷的聲音。本詩集《昨日痛苦變成麥》,有完整的一組愛情詩:「不寫作的春天」。阿米重新為愛去畫圖,是非常遼闊有氣勢的一張藍圖。你們看這愛的宣言:
多年來我一直在睡覺
你一次驚動了
全部的我
「全部的我」,有約翰、瑪莉、莎兒......「那些人格的鬥爭,我一概否認」,這種愛就很來勁了。今天廿一世紀的台灣女子,如何認識?要看阿米塑造的像──這位女子是經過大風浪的:她產生一種人格的特質。是愛,驚醒了身上各種事物,因為愛,引出各個真實的門,去觸摸去打開,它們彼此相撞,但愛是無方位無認定,也是無辜的。只有一股源源不絕,要熔化融匯萬種恆河沙數的力。奇怪的阿米甚至將《金剛經》的句子轉成〈愛經〉。
我是一切虛空中為你倒吊的精靈,我是無法離欲的妒婦
這名充滿愛欲的女子創造出她男人的情婦〈我恨安琪拉〉;創造出想吞噬她甜蜜順境的霉運〈我和先生的故事〉。她愛得很不安寧,有一百種不可能愛的畫面,總見到「那個可惡的女人,和你的孩子,像甜甜圈一樣站在一起」,啊但同一首詩的結局我們又看見:「我這樣一個野孩子/只有你的懷抱/讓我明白/靜止不動/的一種乳白色」(〈愛人風景〉)。
阿米用痛苦經歷開展出《金剛經》的真義:愛與欲沒有定義、愛與痛同等深沉、愛可以產生一百種不平靜的理由,但我們會被阿米在九種苦難之後第十個小小的話語角落,感動而哭。她這首〈沒有永遠的〉,說:
不必說再見
因為沒有永遠
沒有永遠的親人
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悲喜
沒有永遠的存款
沒有永遠的學歷
沒有永遠的體重
沒有永遠的熱吻
即使如此
還是小跑步靠近你
用盡所有的力氣讓你明白:我是一個愛你的小孩
歷盡劫難之後的詩人,阿米意識到在愛的滋潤下,可以碰觸到,如沙特說的:人類深不可測的自由,那兒有廣大宇宙的動能。
翁文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