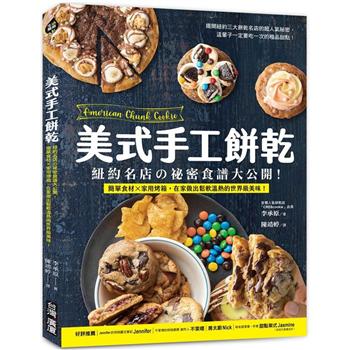溫婉還是豪放?端莊還是浪蕩?
★國際知名學者孫康宜、李奭學、張宏生聯合推薦
★融合中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探討中國古典詩詞的專論,格局宏闊,立論別開生面!
從詩經、楚辭、樂府古詩、艷歌宮體,直到閨怨詩和花間詞,以男性為中心的詩詞創作隱藏了多少釋放情慾的性符碼?古代才女們又是如何突破傳統,拓展出新的女性視野?
一部探討中國文學中的婦女及婦女文學的文學批評力作,結合古典文學傳統批評與現代西方批評理論,特別是以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梳理文本中的女性和女性作者問題,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風騷精神」與「豔情趣味」這兩大源流對立與融合之趨勢作為探討主軸,獨到分析了政治與愛情、文人與女性、詩歌與音樂的複雜關係,融合引人入勝的詩詞鑒賞與多所創新的理論探討為一爐。
作者簡介:
康正果,退休教師。已出版的作品有《風騷與艷情》、《重審風月鑒》、《交織的邊緣》、《鹿夢》、《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肉像與紙韻》、《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平庸的惡──一位海外華人筆下的中國剪影》、《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等著。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一部在中美均有深遠影響的文學批評力作,精彩而精闢地探討了文學中的婦女和婦女文學之間的複雜關係,通過追溯各類言情表愛之作中相關的表述問題,對涉及到比興的詩歌理論作了極富新意的檢討。該書以全新的範疇揭示了古代詩人及其在表述性與性別上含蓄微妙的層面,其富有啟示的詮釋對行家和普通讀者均有啟迪作用。全書融詩作鑒賞、本事鈎沉和理論爭辯為一體,特具可讀性,實為垂範古典文學研究的一部佳作。」——耶魯大學首任Malcolm G. Chace'56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 孫康宜
「本書不僅審視中國歷代的女詩人,也處理史上涉及女性形象的各種詩體的寓義的遞嬗。作者以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為論證基礎,也由創作和讀者反應的聯動開啟新意,乃有其思想與批評視境的詮釋佳構,一般文學史難以企及。」——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 李奭學
「作者以扎實的文獻功力,敏銳的問題意識,靈動的思想火花,溝通傳統與現代,將舊領域賦予新視野,將老問題融入新思考。」——南京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講座教授 張宏生
名人推薦:「一部在中美均有深遠影響的文學批評力作,精彩而精闢地探討了文學中的婦女和婦女文學之間的複雜關係,通過追溯各類言情表愛之作中相關的表述問題,對涉及到比興的詩歌理論作了極富新意的檢討。該書以全新的範疇揭示了古代詩人及其在表述性與性別上含蓄微妙的層面,其富有啟示的詮釋對行家和普通讀者均有啟迪作用。全書融詩作鑒賞、本事鈎沉和理論爭辯為一體,特具可讀性,實為垂範古典文學研究的一部佳作。」——耶魯大學首任Malcolm G. Chace'56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 孫康宜
「本書不僅審視中國歷代的女詩人,也處理史上涉及女...
章節試閱
【李商隱:風騷還是豔情】
李商隱歷來以詩風的綺麗香豔著稱,詩壇上早有所謂李、杜(牧)或溫(庭筠)、李之稱,足見他的詩歌給後世留下的主要印象。但相比之下,他的豔詩不但比與他並稱的兩個詩人數量多、質量高,而且情況也複雜得多。杜牧和溫庭筠都是有名的風流浪子,李商隱卻未留下類似的軼事,相反,他的傳記主要記載了他在朋黨交際上陷入的困境。這樣的遭遇在古代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經過歷代的解釋傳播,似乎他一生都在黨爭的漩渦中掙扎,都在用詩文陳情,爭取理解,而最終成為官僚政治的犧牲品。這是李商隱的研究者和李詩的各家注本素來強調的一點。詩人的這種命運不但通過後人對其作品的解釋被「重點擴散」,而且反過來也構成了一種批評準則,即把屬於歷史性問題的「事」和「志」視為李商隱寫詩的心理因素。再加上李商隱的豔詩寫得大都隱諱、朦朧,更有不少詩冠以「無題」的標題,其中更有「美人芳草」的意味,因而說詩者多傾向於把他的豔詩解釋成別有寄託的作品。這樣一來,李商隱的生平經歷就成為解釋李詩所不能不考慮的背景。這種過分拘於事實,片面根據寫作動機來解釋李詩的批評途徑最易陷入「新批評」派所謂的「意圖謬誤」(the intentional fallacy)。
另一種傾向則把某些豔詩當「謎語詩」破譯,或捕風捉影,力圖從中挖掘詩人埋藏的個人豔史,甚至非要把某些詩解釋為刺女道士之作。所有這一切都對讀者系統地理解李詩造成混亂。因此在分析李商隱詩作中最有代表性的「無題詩」之前,必須從三個方面澄清一些長期以來的模糊影響之說。
首先是李商隱與女道士交往的問題。在唐代,詩人與道士詩文往來,或在詩中記述尋仙訪道的遊歷,本是很普遍的現象。李商隱集中現存幾篇贈道士(包括女道士)的詩,也有不少詠道觀和道士生活的詩,這在唐代詩人中並非特殊事例。此外,李商隱早年曾學道玉陽,道觀中的生活自然在他的記憶中留有較深的印象,這也可能是他喜歡把詩中的女性寫成仙女或女冠的一個原因。更為主要的是,李商隱素以「獺祭魚」著稱,在唐代詩人中,恐怕還沒有一個詩人像他那樣把使事用典的範圍擴張到了道教的典籍之中。生僻的道教術語被他用作詩中的詞藻,道教傳說中的人物也多被他引入詩篇,致使他的某些詩作具有濃厚的道教色彩。與其說李商隱銳意反映女道士的道觀生活,不如說他的詩作獨創了道教題材的詩意。如「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銀河吹笙〉);「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碧城〉),這些詩不過借用有關道教的意象以製造一種幽渺清冷的意境,抒寫個人寂寞的心情而已。詩中的人物和景物既非寫實,亦非影射,說詩人同情女道士沒有愛情的生活,或說詩人諷刺女道士淫亂,恐怕純屬解釋者自己的偏執之談。聖女祠只是個小小的道觀,遠在略陽的山崖之上,詩人路經此地,偶爾形諸吟詠,沒有確切的理由能夠說明他為什麼要一再寫詩諷刺這裡的女道士。至於李商隱與女道士宋華陽相戀的說法,顯然缺乏根據,至少就〈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一詩來看,絲毫看不出任何男女相悅之情的流露。嚴格地說,有關道士或道教的詩篇在李商隱的詩作中並無多大的價值,也不屬於豔詩的範疇。因此不必在此花費過多的筆墨辨析此類問題。
為什麼後世文人多好在女道士的問題上大作文章呢?需要首先指出的是,文學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未必就是現實生活中婦女的真實寫照,有時候反倒是作品中的婦女形象把現實生活中的婦女假定為不同的類型。確切地說,文學作品並沒有反映婦女的真實處境,它傳達和宣揚的乃是男性中心文化對婦女的分類和評價。唐代的女冠是否風流,或女道觀裡是否淫亂的問題並不是文學研究的中心議題,也不能僅根據魚玄機這樣風流的女冠詩人,或駱賓王的〈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等詩篇,就可以對女冠或女道觀採取一概而論的態度。需要我們考慮的是,為什麼古代的文學作品常把淫亂的角色派在出家人的身上?這首先反映了世俗的儒家文化對佛道的醜化,例如,在宋元以後的小說戲曲中,寺廟的醜聞又從道士轉移到了僧尼身上。在重視婚配的中國社會中,人們自古以來都傾向於把獨身的男女視為不正經的人物,至今人們仍按這種古怪的邏輯議論男女關係。因此關鍵問題並不在於歷史上的女冠是否淫蕩,而在於人們以什麼態度看待她們,以及如何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她們的處境。顯而易見,古代作家很少從揭示寺院生活固有的缺陷出發寫僧道的生活,他們更喜歡通過暴露禁欲生活中的病態事例來展覽色情,嘲弄破戒犯規的「檻外人」,此類題材在「三言」、「二拍」之類的小說中非常之多。由此可見,除倡妓以外,像女冠這樣沒有與男子建立倫理關係的女人,也是男性中心文學作為色情對象描寫的人物。既然她們不屬於某一個男人所有,她們當然就是淫蕩的和有機可乘的了。連阿Q那孱頭不是也欺侮小尼姑麼?
所以,文學研究的任務實不必陷入實證地考據一個詩人是否與女道士有風流韻事,或唐代女冠到底淫亂到什麼程度,而最好致力於解釋為什麼詩人喜歡在他的詩作中吟詠女冠。此外,我們還應看到,後人的解釋有時也參與了所讀解文本的創作,通過勾沉索隱,附會本事,把文學文本中本無的意義強加於其上,如關於李商隱在詩中詠他與女道士戀愛或諷刺女道士淫亂的解釋,實際上已起到了塑造女道士風流形象的作用。
詠女冠的容貌本是詩歌中的一個專題,唐代教坊曲子中就有一個曲牌名〈女冠子〉,從後來的〈女冠子〉詞可以看出,該詞最初即專詠女冠的妖冶。這種趣味也散見於唐人贈女冠的詩中,如李洞〈贈龐練師〉(《才調集》卷三)就以輕佻的口吻描寫了龐練師的美色:「兩臉酒醺紅杏妒,半胸酥嫩白雲饒。」類似的描寫還可以從其他詩中找到。這都說明,唐人慣於在詩中把女冠描繪成一種風流美貌的女性。唐代女冠主要來源於四種女性:自願學道的公主和貴族女子,被釋放的宮人,被遺棄的姬妾和走投無路的妓女。無論是就她們的經歷而言,還是就她們的容色而言,她們都容易被作為風流妖豔的女性去描寫。正如南朝豔詩中常常把採桑女子寫成妖豔的女性,詩歌中的女冠也是一種美人形象,如此而已,並無多少深意。上述的一切正好為喜歡附會本事或發掘「刺淫」之作的解釋者提供了參考資料,而現代學者又從浪漫愛情觀出發翻新舊說,以致形成了一種硬是把李商隱及其作品和女道士拉扯到一起的定向思維。在著手分析李商隱的豔詩之前,最好還是先跳出此類枝節問題的糾纏。
其次是李商隱與歌妓的關係。李商隱詠歌妓的詩多為妓席應酬之作,這些詩多出於即興應景,既無寄託可言,也與愛情無關。唐代官僚普遍蓄養家妓,幕府中也有大量的官妓,她們在酒宴上為賓主佐酒,以歌舞助興,身分與平康諸妓根本不同。也許由於她們屬於主人或主管機構所有,只在席間表演或服務,不可能與在座的客人隨意建立超出界線的關係,因而在很多詠妓席的詩中,詩人普遍傾向於把歌妓描寫成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如吳融〈浙東筵上有寄〉:「襄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當語不傳。見了又休真似夢,坐來雖近遠於天。」這種「意密體疏」的情景構成了李商隱詠妓詩的基調。如「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和令狐八綯戲題二首〉),「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等詩句,都一再陳述男方徒自多情,女方難以接近,並以此與同座的友人互相戲謔。這些詩多為遊戲筆墨,它旨在以情色幽默活躍筵席上的氣氛,實在沒有多少真正的詩意。但也有個別詩篇,由於把讚美歌妓的色藝與對其人的表白較為自然地聯繫在一起,便顯得頗有情致。如〈贈歌妓〉兩首:
水精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
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裡唱陽關。
白日相思可奈何,嚴城清夜斷經過。
只知解道春來瘦,不道春來獨自多。
第一首詩讚美歌妓的色藝。首句以兩個精美的意象起興,首先形成一種晶瑩、玲瓏的美感。次句誇她有傾城傾國的美色。三、四句讚歎她的歌喉。「紅綻櫻桃」乃詩中形容歌唇的套語,「白雪」即所謂「陽春白雪」,代指美妙的歌曲,但「紅」與「白」的色彩對比,「綻」與「含」的動態描寫,兩者巧妙地配合在一起,又構成了一幅純美的畫面。
第二首詩語含戲謔。歌妓在筵席上服務的項目之一便是供客人調笑,詩人寫詩戲謔歌妓不惟無傷大雅,歌妓本人也會把詩人的自作多情當作可以欣然接受的殷勤。在觥籌交錯的宴會上,文人慣於寫詩湊興,玩這種風雅的遊戲,其中並不存在現代學者熱衷賞析的愛情。該詩的首句說詩人白日不便相訪,次句說夜間城內宵禁,所以他始終無緣與她接近。三、四句則向她表白,說他入春以來之所以消瘦是因為一直過著孤獨的生活,言外之意即他為思念她而憔悴。從這兩首詩可以略見李商隱妓席詩的一斑。
既然這些泛泛寫豔情的遊戲之作並沒有透露出李商隱與歌妓戀愛的消息,又有什麼根據去主觀猜測,憑空附會,給某些背景不明的詩編造本事呢?相反,有兩個事例倒可以說明,李商隱對待歌妓,即使不是持輕視的態度,至少也在感情上與她們有一定的距離。
其一為熱衷談論「愛情詩」的今人常常提到的柳枝其人其事。據〈柳枝〉五首的序文所述,十七歲的柳枝是一個漂亮活潑的洛陽「里娘」,她家與李商隱的堂弟讓山家相鄰。有一天讓山在柳枝面前朗讀了李商隱的新作〈燕台〉四首,引起柳枝的好奇心。當柳枝得知該詩的作者是讓山的堂兄時,柳枝當即拉斷衣上的長帶作為信物,託讓山向商隱乞詩。次日讓山偕商隱與柳枝相見,並約定三日後去水邊歡度節日。但因他故,商隱未能赴會即匆匆奔赴長安。後來他從讓山口中得知,柳枝為一有權勢者所佔有。商隱甚為感傷,賦〈柳枝〉五首,並寫了一篇小序記述這段因緣。
就詩而論,〈柳枝〉五首並非上乘之作,詩人既惋惜他與柳枝無緣結合,又竭力排遣感情的糾葛,自我寬解。五首詩中的第一首即云:「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詩人以蜂和蝶的本非同類比喻他與柳枝出身不同,言外之意是,他為士人,柳枝乃一「里娘」,他們雖彼此有情,卻非合適的配偶,因而他主動放棄了柳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士大夫擇妻的恒定標準,李商隱雖生於末代,畢竟是個沒落的王孫,他自然不會與商人的女兒締結婚姻。從這五首詩和序文可以看出,在社會上通行的婚配標準與詩人的個人感情發生衝突的情況下,他雖未像元稹那樣宣揚「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的薄情論調,但最終還是犧牲了自己的感情,做出了現實的選擇。不過,兩位詩人對自己的選擇又明顯地表示了不同的態度,元稹在詩中為自己求婚高門而辯護,〈柳枝〉五首則抒發了詩人的遺憾之情。
其二為李商隱入梓州幕府後的一件小事。李商隱與其妻王氏情愛甚篤,喪妻之後,他長期陷入悼亡悲情。在梓幕任職期間,長官柳仲郢見他生活孤獨,打算賜給他歌妓一名。商隱上書柳仲郢,坦率陳情,婉言回絕了柳的賞賜。他說:「某悼傷以來,光陰未幾。……檢庾信荀娘之啟,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飄泊……至於南國妖姬,叢台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上河東公啟〉)由此可見,李商隱在喪妻後對男女之情已心灰意冷,同時也說明他平日與歌妓殊少親密的往來。
在此特意列舉以上兩個事例並非為了證明李商隱行為正派,潔身自好,文學研究並無鑑定作家行為的額外任務。我的意圖在於,通過這兩件事例客觀地顯示李商隱的性格和心境,以及他的創作傾向,從而說明他大概沒有必要炮製「謎語詩」,去埋藏後世的好事者喜歡考證的豔史。
【李商隱:風騷還是豔情】
李商隱歷來以詩風的綺麗香豔著稱,詩壇上早有所謂李、杜(牧)或溫(庭筠)、李之稱,足見他的詩歌給後世留下的主要印象。但相比之下,他的豔詩不但比與他並稱的兩個詩人數量多、質量高,而且情況也複雜得多。杜牧和溫庭筠都是有名的風流浪子,李商隱卻未留下類似的軼事,相反,他的傳記主要記載了他在朋黨交際上陷入的困境。這樣的遭遇在古代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經過歷代的解釋傳播,似乎他一生都在黨爭的漩渦中掙扎,都在用詩文陳情,爭取理解,而最終成為官僚政治的犧牲品。這是李商隱的研究者和李詩的各家注...
作者序
【重印本自序:一本書的故事】康正果
談到這部舊作,我不由得回想起曾因此而經歷的憂患,以及後來所觸發的一系列善緣。在它出版二十七年之後,如今又蒙秀威資訊重印發行,趁寫這篇序言之機,我要給新一代讀者講些我與此書的故事。
我沒受過多少學院的正規教育,在中文系本科才讀到二年級上半學期,就因焚毀系總支強迫我上繳的私人日記而被開除學籍。從此,我墮入社會底層,從工廠轉到勞教農場,最後到農村落戶,做了好多年農民。直至多年後獲得平反,我才有機會考回原來那個大學攻讀古典文學碩士學位。當時親友多建議我另選一個學校讀書,我卻偏要顯示「前度劉郎今又來」的得意,硬是回到我曾跌倒的地方再站起來做人。
那時中國大陸正值二十世紀七○年代末的轉折年代,而中文系的教學和研究仍沿襲五○年代以降的教條,整個氛圍令人甚感沉悶。我的指導教師文筆趨時,比較風派,詩詞鑑賞的小文章寫得活潑通俗,在古典文學界已有相當的影響。但就做研究生所需要的扎實培訓而言,像他那類習慣做古典文學普及工作的教授就難免有所欠缺,實在說不上有多少值得師法之處。因此對我來說,考到學院裡讀這個學位,不過是把平日業餘的自學鑽研提升到正規專攻的程度,比起課堂上灌輸的那些知識,還是在圖書館和宿舍內自己研讀收益更多。好在我那位導師更關心他自己發表文章和參加學術會議的事情,極少給我們上課,我也樂得安享我的「被放羊」狀況,索性就古今中外隨心所欲地貪讀泛覽下去,與老教授日益脫節。
光陰似箭,轉眼就到了準備撰寫學位論文的時候。同學中有人選白居易,論述其關心民生疾苦;還有人研究邊塞詩,要展示盛唐的文治武功……我沒興趣去敷衍此類穩妥的老舊話題,暗地裡獨出心裁,在宮體、香奩和詞為豔科的脈絡中打起我論文的腹稿。有一天在校園的柳蔭道上與導師相遇,導師問起我的選題情況,我對他說:「我想研究豔情詩。」導師皺了下眉頭,頗為禁忌地迴避了我提出的論題,他嚴肅地要求我選擇內容健康的愛情詩,在論文中認真討論其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我沒有在「內容健康的愛情詩」範圍內做文章,而是選定韓偓的《香奩集》寫出了我的碩士論文。我的導師與答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對我如此放肆的做法滿懷學術義憤,他們說我那篇論文「所反映的思想傾向是不健康的」,指責我「亂講豔情詩的特徵。對作品的分析,全是對豔情詩的欣賞,有的宣揚色情……有的宣揚人性論……宣揚所謂『意淫』……肯定色情詩」等等。最後,他們對我作出結論:「鑑於上述情況,答辯委員會不接受其論文答辯。」這一決定的後果是很嚴重的,那幾個選題穩妥的同學都順利畢業,分配了工作,唯獨我留級在校,被指令隨下一屆學生重新答辯。
我被迫另選一合適的論題撰寫論文交差,好歹算是過了關,總算拿到了畢業文憑。但因檔案內已塞入了很差的評語,沒有哪個大學的中文系再願意要我。後來,西安交大社科系急需在新辦的雙學位班上推出「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新課程,我自告奮勇,保證能立即開出這個冷僻而無人應承的講座,這才獲得了交大的錄用。我的古典文學專業從此無用武之地,我也不打算在那方面再做出什麼成績。
一九八六年夏的一天,我在本地召開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結識了來自鄭州大學的李小江教授。她當時正主編「婦女研究」叢書,交談中自稱很賞識我的知識結構,當即約我為她的叢書寫一本「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史」的專著。我們隨後在多次通信中反覆討論,最終按我的提議,斷然捨棄了通常的文學史那種按作者和編年順序分期編排的歷時性敘述模式,決定通過風騷精神與豔情趣味這兩大源流對立與融合的演化軌跡,來統攝由女性作者書寫的和有關女性的所有詩詞作品及其相關的評論,並對政治與情愛、文人與女性、詩歌與音樂的關係予以充分的討論。李小江是一位辦事精幹,很有魄力的年輕學者,她當時正在銳意建立她所開創的新學科―婦女研究。若不是碰上她這樣不拘一格大膽組稿的主編,像我這般思路和行文均明顯出格的作者,稿子落在不論哪個編輯手中,都會被拒之門外。書稿在她的催促激勵下寫得快也出得快,一九八七年暑期定下選題,次年五月即交出定稿,幾個月後便發行上市。對我來說,這本書的出版,在實現我出書夢想的興奮之餘,總算出了口論文被斃的惡氣。
那時候我所在的交大社科系正在給教師評定高級職稱,由於「文革」造成的延誤,很多將近退休年齡的教師仍是講師職位。因此,評審工作基本上按論資排輩的老規矩進行,不少沒有任何學術成果的老講師也都給予照顧,提升了職稱,而像我這樣還算年輕的講師,便一再被往後挪移。我不甘後進,跑到教師科找科長理論,並出示我新出的著作,力陳我所具備的條件。那科長接過我的書,讀著「風騷與豔情」這個書名,疑慮地問我是不是本言情小說;並提醒我說,評定職稱要有學術論著,小說詩歌之類的文字可不算數。我只有耐心解釋,說這是本研究古典詩詞與女性的專著,的確屬於學術著作。交大當時還只是個工科大學,那科長顯然在死守針對工科教師學術成果的評定標準,他驢頭不對馬嘴地問我:「這本書應用的理論有什麼實際的經濟價值?」面對科長的問題,我實在有口難辯,只好拿上我那無經濟價值可言的書揚長而去。
就在這場不愉快的行政樓「上訪」之後不久,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國耶魯大學的來信。寄信者是該校東亞系的系主任孫康宜教授,她說她最近剛讀過我的《風騷與豔情》,對書中涉及的諸多問題很感興趣;還說她將在秋季學期開設一門討論課,要集中討論明清兩朝的婦女詩詞,很想拿我這本書給選課的學生做參考資料。給我寫信的目的,就是想讓我幫她聯繫出版社,為她的學生訂購這本新書。我立刻幫她聯繫了出版社,此後便與她有了通信往來。接著,應她盛情邀請,去美國參加了在耶魯舉辦的「明清婦女與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我提交的會議論文頗獲與會者好評。會後我照常返回交大,繼續教我的大學語文。大概是我的會議論文和那本書給耶魯東亞系諸教授留有較好的印象,一九九四年春,該系急需一中文教師,系主任命秘書給我發來傳真,問我是否有意赴耶魯講授中文。我當時在交大幹得並不愉快,有機會換個更好的地方,何樂不為?我立即回電應聘,果斷辭去了交大的教職。就在那年夏天,我帶上妻子兒女,舉家移居耶魯所在的康州紐黑文市。
在美國大學當中文教師,差不多就像中國大陸大學外語系聘來的外教,人家重用的只是你這個說母語的教師固有的語言資源,至於你出了什麼中文著作,都不在特別考慮之列。做這種口力勞動的工作,能把學生教得會說普通話、會寫漢字就算盡職,若有餘力編些中文教材,自然會更受嘉許,但並不存在必須在哪一級刊物上發了多少學術論文才能評高級職稱的問題。即使平日應邀參加研討會,也只限於中文教學的內容。我因此再不必為評職稱而苦心從事追求學術成果的寫作,更不必死守著古典文學專業來規劃我做學問的內容。讓我感到特別輕鬆的是,我曾經遭遇的種種非學術和反學術的困擾在此都一筆勾銷,從此可游離出學院學術的藩籬,隨興之所至,在異國的語言地圖上開拓母語寫作的天地。
耶魯校園的建築古色古香,走進圖書館正廳,恍如置身時間隧道,一下回到十八世紀。我家的住宅遠在城郊,一出門即有「悠然見南山」的圖畫視野。我儘管疏遠了那種從文本到文本的古典學問,卻活出了「古典的現世」,一股子與古為鄰的情味。從某種程度上說,古典已內化為我的情意思緒和胸臆氣度。退休以來,我偶爾會寫幾首舊體詩詞,算是在風騷與豔情走向融合的流變中添上幾筆綺麗的餘波。茲錄近作一首,作為這篇序言的結尾:
〈秋興〉
木已成舟恰稱身,飄洋過海好移民。
百年跌宕獨行客,半世浮沉局外人。
自省因緣權得失,追懷際遇辨疏親。
天涼最喜深秋景,又上東岩做片雲。
二○一五年八月
【重印本自序:一本書的故事】康正果
談到這部舊作,我不由得回想起曾因此而經歷的憂患,以及後來所觸發的一系列善緣。在它出版二十七年之後,如今又蒙秀威資訊重印發行,趁寫這篇序言之機,我要給新一代讀者講些我與此書的故事。
我沒受過多少學院的正規教育,在中文系本科才讀到二年級上半學期,就因焚毀系總支強迫我上繳的私人日記而被開除學籍。從此,我墮入社會底層,從工廠轉到勞教農場,最後到農村落戶,做了好多年農民。直至多年後獲得平反,我才有機會考回原來那個大學攻讀古典文學碩士學位。當時親友多建議我另選一個學校讀書...
目錄
重印本自序:一本書的故事/康正果
導言 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質疑和構想
第一章 「三百篇」:風情與風教
一、詩與樂
二、關於「興」
三、戀歌與婚歌
四、思婦和棄婦
五、解釋的演變與接受
第二章 屈宋騷賦:美人和香草
一、媚神的香草和娛神的戀情
二、「美人香草」的意象
三、舞女和神女
第三章 樂府古詩:風騷型
一、采桑與織素
二、擬作與託名
三、夫婦情與君臣情
第四章 南朝新聲:豔情型
一、豔歌和豔情
二、豔詩和婦女題材的豔化
三、宮體詩和豔情詩的擴張
第五章 唐詩:走向女性的現實
一、從閨中到民間
二、從宮怨到諷喻
三、從託喻到感事
第六章 唐詩:風流感傷的情調
一、敘冶遊和憶舊夢
二、李商隱:風騷還是豔情
三、香奩詩
第七章 唐宋詞:新的融合與分化
一、詞為豔科
二、豔詞的「雅」和「俗」
三、人與花:走向亦豔亦雅之境
第八章 婦女詩詞:才女的才情和詩名
一、淪落的才女
二、閨中的才女
三、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
四、尾聲,或者新的序曲
重印本自序:一本書的故事/康正果
導言 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質疑和構想
第一章 「三百篇」:風情與風教
一、詩與樂
二、關於「興」
三、戀歌與婚歌
四、思婦和棄婦
五、解釋的演變與接受
第二章 屈宋騷賦:美人和香草
一、媚神的香草和娛神的戀情
二、「美人香草」的意象
三、舞女和神女
第三章 樂府古詩:風騷型
一、采桑與織素
二、擬作與託名
三、夫婦情與君臣情
第四章 南朝新聲:豔情型
一、豔歌和豔情
二、豔詩和婦女題材的豔化
三、宮體詩和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