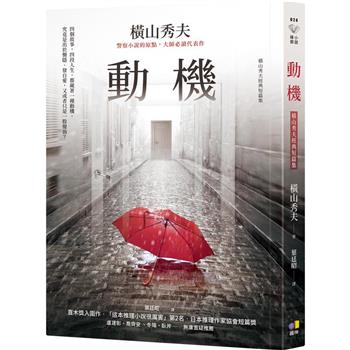春天釀的酒;甘醇、甜美,
在齒舌之間生津、漫漾、放縱、醉人!
事業、愛情、健康
甚麼樣的年紀應該追求甚麼?
你,做對了嗎?
在齒舌之間生津、漫漾、放縱、醉人!
事業、愛情、健康
甚麼樣的年紀應該追求甚麼?
你,做對了嗎?
本書收錄〈綠苗〉、〈遲暮〉、〈雷堡風雲〉、〈春釀〉四篇中短篇小說。作者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點滴甘苦,將平凡人生中剎那的感動與喜悅轉化為溫醇暖人的文字,傳達出愛情、親情、友情與同袍間相互扶持的珍貴情誼,在心中深處醞釀後留下的甜美滋味,值得我們一再細細回味。
本書特色
年過八旬的老兵作家,以軍人的樸實生命彩繪出燦爛歷程,對人生充滿積極樂觀的精神,透過文字創造出充滿生命力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