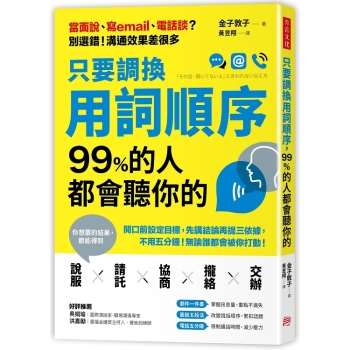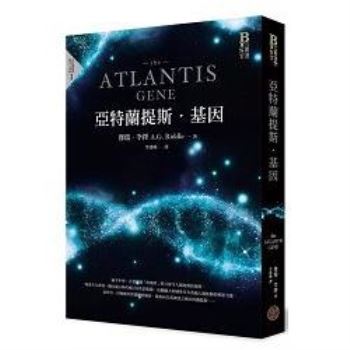「我發現這個世界上的詩的花園多的很,每個詩園裡都有許多美麗的花朵。他們不只來自一個花園,他們原來生長在各種不同的土壤裡,開放在各種不同的角落裡。他們不一定都是頂偉大的或頂好的;只是因為當我走過他們身旁時,投合過我當時的偏好,曾經引起過我注目,曾經感動過我一次或多次,我就顧不了別的,居然把他們譯出來了,把他們採摘回來了。」──周策縱《風媒集‧自序》
周策縱先生為著名漢學家,兼擅古典與現代詩詞,是現代難得的通儒。周氏自一九三七年起便偶有翻譯外國詩人作品,部分譯作亦曾公開發表,然從未集結成冊。本書按照周氏遺稿,重新整理編排。書稿現存翻譯詩作數量約一百二十餘首,長篇短調皆有;所涉獵的詩人,旁及歐美各國,更有部分乃當時新進冒起作家,是喜讀外國文學與欣賞詩集的讀者們不可錯過的收藏。
本書特色
§國際知名漢學家周策縱未曾完整曝光過之著作,收錄外國翻譯詩達百餘首。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風媒集:周策縱翻譯詩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94 |
外國詩 |
$ 332 |
詩 |
$ 370 |
中文書 |
$ 370 |
世界詩集 |
$ 378 |
華文現代詩 |
$ 378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420 |
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風媒集:周策縱翻譯詩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譯著者簡介
周策縱
周策縱(1916-2007),湖南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為知名漢學家和歷史學家,以《五四運動史》一書聞名中外。同時也是白馬社詩人。
編者簡介
心笛
心笛(浦麗琳),江蘇常熟人。紐約白馬社元老。曾任職美國南加州大學數十年。著有《貝殼》、《摺夢》、《提筐人》與《我是蒲公英白球裡的傘》等詩集,《海外拾遺:浦薛鳳家族收藏師友書簡》。合編《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海外新詩鈔》等。
王潤華
周策縱學生,現任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副院長兼中文系教授,曾任新加坡作家協會會長、台灣元智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兼中國語文學系主任。
瘂弦
著名現代詩人,曾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期刊部總編輯。榮獲第二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
黎漢傑
曾任《聲韻詩刊》總編輯。著有《詩經譯註》及個人詩集《漁父》、編有《2011香港新詩選》、《2012香港新詩選》、《2013香港新詩選》。
周策縱
周策縱(1916-2007),湖南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為知名漢學家和歷史學家,以《五四運動史》一書聞名中外。同時也是白馬社詩人。
編者簡介
心笛
心笛(浦麗琳),江蘇常熟人。紐約白馬社元老。曾任職美國南加州大學數十年。著有《貝殼》、《摺夢》、《提筐人》與《我是蒲公英白球裡的傘》等詩集,《海外拾遺:浦薛鳳家族收藏師友書簡》。合編《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海外新詩鈔》等。
王潤華
周策縱學生,現任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副院長兼中文系教授,曾任新加坡作家協會會長、台灣元智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兼中國語文學系主任。
瘂弦
著名現代詩人,曾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期刊部總編輯。榮獲第二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
黎漢傑
曾任《聲韻詩刊》總編輯。著有《詩經譯註》及個人詩集《漁父》、編有《2011香港新詩選》、《2012香港新詩選》、《2013香港新詩選》。
目錄
前言
風媒集自序
編輯凡例
A‧E‧休士曼(A. E. Housman)
山花
I Hoed and Trenched and Weeded
他們說我底詩悲哀
They Say My Verse Is Sad
西方
The West
我二十一歲的時候
When I Was One-and-Twenty
訣絕
We’ll To The Woods No More
最可愛的樹
Loveliest of Trees
舊地
Give Me a Land of Boughs in Leaf
C‧德‧路易士(C. Day Lewis)
衝突
The Conflict
E‧E‧卡明司(E. E. Cummings)
「甜蜜的春天是你的」
Sweet Spring
有些地方我從來沒遊過
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G‧M‧哈卜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圓滿癖
The Habit of Perfection
K‧S‧阿林(Kenneth Slade Alling)
獨自在公園的凳子上
On The Park Bench
S‧T‧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忽必烈漢
Xanadu—Kubla Khan
青年和老年
Youth And Age
時間,真實和想象的─一個寓言
Time, Real And Imaginary
W‧H‧台維斯(W. H. Davies, 1870 - 1940)
月亮
The Moon
野心
Ambition
散學了
School’s Out
最好的朋友
The Best Friend
給一個女朋友
閒暇
Leisure
榜樣
The Example
W‧H‧敖敦(W. H. Auden)
可是我不能
But I Can’t
法律就像愛情
Law, Say the Gardeners, Is the Sun
停了一切的鐘錶
Song: Stop All The Clocks
卡爾‧山德堡(Carl Sandburg)
小草
Grass
白朗寧(Robert Browing)
終身的愛
Love in a Life
白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白朗寧夫人底情詩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白墨安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我解除了這蠱惑了我許久的符咒
I Broke the Spell That Held Me Long
色爾薇亞‧卜萊芝(Sylvia Plath)
比喻
Metaphors
艾莉諾‧魏勒(Elinor Wylie)
什麼地方,啊,什麼地方?
Where, O, Where?
天鵝絨的鞋子
Velvet Shoes
艾德格‧坡(Edgar Allan Poe)
海市
The City in the Sea
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豪氣
Heroism
亨利‧朗法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潮漲又潮平
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
克蕾司丁娜‧羅色蒂(Christina Rossetti)
我死後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附錄:歌
狄朗‧湯瑪司(Dylan Thomas)
不要輕輕走進那訣別的良夜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貝多斯(Thomas Lovell Beddoes)
要是有夢賣
If There Were Dreams To Sell
拉伏勒斯(Richard Lovelace)
赴戰─給露卡司塔
To Lucasta, on Going to the Wars
肯尼斯‧費欒(Kenneth Fearing)
美國狂想曲(其四)
American Rhapsody
阿蘭勒西(William Edgar O’Shaughnessy)
我另外造了個花園
Song
哈代(Thomas Hardy)
他所殺死的人
The Man He Killed
散步
The Walk
哈得(Bret Harte)
那個左道旁門的唐人─「老實人」哲穆司的坦白話
The Heathen Chinee
哈爾特‧克倫(Hart Crane)
夢爾維爾墓畔作
At Melvilie’s Tomb
威廉‧阿林漢(Allingham)
憶
A Memory
拜倫(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大海
The Sea
弔羅馬
Rome
她躝跚漫步
She Walks In Beauty
別湯穆斯‧莫爾
To Thomas Moor
哀希臘
The Isles of Greece
留別雅典女郎
“Maid of Athens, Ere We Part”
附蘇曼殊譯〈留別雅典女郎〉
柯立芝(Hartley Coleridge)
短歌
Song
約翰‧馬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
我想到天空就失了眠
I Could Not Sleep For Thinking Of The Sky
和她做了朋友
Being Her Friend
奉神曲
A Consecration
澤國之夜
Night On The Downland
哲木斯‧司梯芬斯(James Stephens)
風
The Wind
祕密
The Secret
晏珠‧馬維爾(Andrew Marvell)
花園
The Garden
給他撒嬌的情人
To His Coy Mistress
桑塔雅納(Georgr Santayana)
你有什麼財富?
What Riches Have You That You Deem Me Poor
泰布(John Banister Tabb)
演化
Evolution
莎蕾‧狄詩德(Sara Teasdale)
一瞥
The Look
忘了吧
Let It Be Forgotten
戀歌
Song
莫憂(Harvey P. Moyer)
我爸爸是個社會主義的信徒
My Papa Is A Socialist
惠特曼(What Withman)
大闊斧歌
Song of the Broad-Axe
斯賓德(Stephen Spender)
我不斷的想念
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普希庚(Alexander Pushkin)
你拋棄了這異國
“Abandoning an Alien Country”
湯木斯‧俄爾夫(Thomas Wolfe)
深夜有聲音向我說
Something Has Spoken To Me In The Night
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我們是七
We Are Seven
給一隻蝴蝶
To A Butterfly
霓虹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露茜‧孤蕾
Lucy Gray; or, Solitude
愛德孟‧華樓(Edmund Waller)
詠羅帶
On a Girdle
愛德納‧密勒(Edna St. Vincent Millay)
別憐恤我
Pity Me Not
我吻過了什麼嘴脣
What Lips My Lips Have Kissed
念黃海漁夫,鮑琴
For Pao-Chin, A Boatman On The Yellow Sea
愛德溫‧馬克漢謨(Edwin Markham)
你底眼淚
Your Tears
倚鋤人─ 馬格觀賞米勒(Jean F. Millet)
著作世界馳名的油畫「倚鋤人」後
The Man with a Hoe
愛彌麗‧狄更生(Emily Dickinson)
小陽春
Indian Summer
因為我不能等待死神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我為美而死
I Died for Beauty
愛彌麗‧蔔朗特(Emily Bronte)
最後的詩行
Last Lines
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
我底書所去的地方
Where My Books Go
他願有天上的錦繡
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玫瑰樹
The Rose Tree
政治
Politics
靜姑娘
Maid Quiet
瑪德林‧艾欒(Madeleine Aaron)
量衣蟲(尺蠖─愛爾蘭的就送信)
Measuring Worm (Old Irish Superstition)
福勞斯特(Robert Frost)
火與冰
Fire And Ice
沒有給選擇的路
The Road Not Taken
修牆
Mending Wall
雪夜小駐林邊外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請進
Come In
歐納司‧道生(Ernest Dowson)
我已不是賽娜拉管轄下的我了
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
幽居
魯巴克(Phyllis M. Lubbock)
「我摘了一枝櫻草」
I Picked a Primrose
鮑德朗(Francis William Bourdillon)
黑夜有一千隻眼睛
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
濟慈(John Keats)
大地的詩
The Poetry of Earth Is Never Dead
明亮的星呀
〔附〕袁水拍譯: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
希臘古瓶歌
Ode on a Grecian URN
繆蕾爾‧魯克色(Muriel Rukeyser)
歌
Song
懷阿特(Sir Thomas Wyatt)
給一位女郎的最後通牒
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
死
Death
你底名字
Well I Remember How You Smiled
為什麼
Why
無名氏(Anonymous)
義務
Duty
戀歌(約1600年作)
Madrigal (c.1600 A.D)
後記
風媒集自序
編輯凡例
A‧E‧休士曼(A. E. Housman)
山花
I Hoed and Trenched and Weeded
他們說我底詩悲哀
They Say My Verse Is Sad
西方
The West
我二十一歲的時候
When I Was One-and-Twenty
訣絕
We’ll To The Woods No More
最可愛的樹
Loveliest of Trees
舊地
Give Me a Land of Boughs in Leaf
C‧德‧路易士(C. Day Lewis)
衝突
The Conflict
E‧E‧卡明司(E. E. Cummings)
「甜蜜的春天是你的」
Sweet Spring
有些地方我從來沒遊過
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G‧M‧哈卜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圓滿癖
The Habit of Perfection
K‧S‧阿林(Kenneth Slade Alling)
獨自在公園的凳子上
On The Park Bench
S‧T‧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忽必烈漢
Xanadu—Kubla Khan
青年和老年
Youth And Age
時間,真實和想象的─一個寓言
Time, Real And Imaginary
W‧H‧台維斯(W. H. Davies, 1870 - 1940)
月亮
The Moon
野心
Ambition
散學了
School’s Out
最好的朋友
The Best Friend
給一個女朋友
閒暇
Leisure
榜樣
The Example
W‧H‧敖敦(W. H. Auden)
可是我不能
But I Can’t
法律就像愛情
Law, Say the Gardeners, Is the Sun
停了一切的鐘錶
Song: Stop All The Clocks
卡爾‧山德堡(Carl Sandburg)
小草
Grass
白朗寧(Robert Browing)
終身的愛
Love in a Life
白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白朗寧夫人底情詩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白墨安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我解除了這蠱惑了我許久的符咒
I Broke the Spell That Held Me Long
色爾薇亞‧卜萊芝(Sylvia Plath)
比喻
Metaphors
艾莉諾‧魏勒(Elinor Wylie)
什麼地方,啊,什麼地方?
Where, O, Where?
天鵝絨的鞋子
Velvet Shoes
艾德格‧坡(Edgar Allan Poe)
海市
The City in the Sea
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豪氣
Heroism
亨利‧朗法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潮漲又潮平
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
克蕾司丁娜‧羅色蒂(Christina Rossetti)
我死後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附錄:歌
狄朗‧湯瑪司(Dylan Thomas)
不要輕輕走進那訣別的良夜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貝多斯(Thomas Lovell Beddoes)
要是有夢賣
If There Were Dreams To Sell
拉伏勒斯(Richard Lovelace)
赴戰─給露卡司塔
To Lucasta, on Going to the Wars
肯尼斯‧費欒(Kenneth Fearing)
美國狂想曲(其四)
American Rhapsody
阿蘭勒西(William Edgar O’Shaughnessy)
我另外造了個花園
Song
哈代(Thomas Hardy)
他所殺死的人
The Man He Killed
散步
The Walk
哈得(Bret Harte)
那個左道旁門的唐人─「老實人」哲穆司的坦白話
The Heathen Chinee
哈爾特‧克倫(Hart Crane)
夢爾維爾墓畔作
At Melvilie’s Tomb
威廉‧阿林漢(Allingham)
憶
A Memory
拜倫(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大海
The Sea
弔羅馬
Rome
她躝跚漫步
She Walks In Beauty
別湯穆斯‧莫爾
To Thomas Moor
哀希臘
The Isles of Greece
留別雅典女郎
“Maid of Athens, Ere We Part”
附蘇曼殊譯〈留別雅典女郎〉
柯立芝(Hartley Coleridge)
短歌
Song
約翰‧馬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
我想到天空就失了眠
I Could Not Sleep For Thinking Of The Sky
和她做了朋友
Being Her Friend
奉神曲
A Consecration
澤國之夜
Night On The Downland
哲木斯‧司梯芬斯(James Stephens)
風
The Wind
祕密
The Secret
晏珠‧馬維爾(Andrew Marvell)
花園
The Garden
給他撒嬌的情人
To His Coy Mistress
桑塔雅納(Georgr Santayana)
你有什麼財富?
What Riches Have You That You Deem Me Poor
泰布(John Banister Tabb)
演化
Evolution
莎蕾‧狄詩德(Sara Teasdale)
一瞥
The Look
忘了吧
Let It Be Forgotten
戀歌
Song
莫憂(Harvey P. Moyer)
我爸爸是個社會主義的信徒
My Papa Is A Socialist
惠特曼(What Withman)
大闊斧歌
Song of the Broad-Axe
斯賓德(Stephen Spender)
我不斷的想念
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普希庚(Alexander Pushkin)
你拋棄了這異國
“Abandoning an Alien Country”
湯木斯‧俄爾夫(Thomas Wolfe)
深夜有聲音向我說
Something Has Spoken To Me In The Night
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我們是七
We Are Seven
給一隻蝴蝶
To A Butterfly
霓虹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露茜‧孤蕾
Lucy Gray; or, Solitude
愛德孟‧華樓(Edmund Waller)
詠羅帶
On a Girdle
愛德納‧密勒(Edna St. Vincent Millay)
別憐恤我
Pity Me Not
我吻過了什麼嘴脣
What Lips My Lips Have Kissed
念黃海漁夫,鮑琴
For Pao-Chin, A Boatman On The Yellow Sea
愛德溫‧馬克漢謨(Edwin Markham)
你底眼淚
Your Tears
倚鋤人─ 馬格觀賞米勒(Jean F. Millet)
著作世界馳名的油畫「倚鋤人」後
The Man with a Hoe
愛彌麗‧狄更生(Emily Dickinson)
小陽春
Indian Summer
因為我不能等待死神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我為美而死
I Died for Beauty
愛彌麗‧蔔朗特(Emily Bronte)
最後的詩行
Last Lines
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
我底書所去的地方
Where My Books Go
他願有天上的錦繡
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玫瑰樹
The Rose Tree
政治
Politics
靜姑娘
Maid Quiet
瑪德林‧艾欒(Madeleine Aaron)
量衣蟲(尺蠖─愛爾蘭的就送信)
Measuring Worm (Old Irish Superstition)
福勞斯特(Robert Frost)
火與冰
Fire And Ice
沒有給選擇的路
The Road Not Taken
修牆
Mending Wall
雪夜小駐林邊外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請進
Come In
歐納司‧道生(Ernest Dowson)
我已不是賽娜拉管轄下的我了
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
幽居
魯巴克(Phyllis M. Lubbock)
「我摘了一枝櫻草」
I Picked a Primrose
鮑德朗(Francis William Bourdillon)
黑夜有一千隻眼睛
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
濟慈(John Keats)
大地的詩
The Poetry of Earth Is Never Dead
明亮的星呀
〔附〕袁水拍譯: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
希臘古瓶歌
Ode on a Grecian URN
繆蕾爾‧魯克色(Muriel Rukeyser)
歌
Song
懷阿特(Sir Thomas Wyatt)
給一位女郎的最後通牒
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
死
Death
你底名字
Well I Remember How You Smiled
為什麼
Why
無名氏(Anonymous)
義務
Duty
戀歌(約1600年作)
Madrigal (c.1600 A.D)
後記
序
風媒集自序
從小孩子的時候起,我也曾有過多少壯志和願心,無論是實際的或是空想的,平凡的或是光怪陸離的,哪一樣沒有?只是從來不曾想到要翻譯什麼新詩。
我還不認識字的時候,姐姐就教會我背熟了《對子書》、《唐詩三百首》、和《千字詩》裡面的句子。後來發覺,爸爸要老師首先教我的是《聖經》,以後唸「人,口,耳,刀,弓,牛, 羊……」我十二三歲時最初在報紙上和雜誌上發表的作品也是詩。這樣看來,我和詩從小就有了密切的關係了。可是也就從那時候起,我就有了一種動機,總想把詩戒掉,像一個在道德上和衛生上有了深痛的覺悟的人立志要戒掉鴉片煙一般。我寧願談戰略,搞政治,評論政策和國事,鼓吹時代思潮,或者研究自然科學,寫小說或劇本,什麼都高興,只是絕對不想做詩,更不想譯詩。襲定庵(自珍)那許多「戒詩」的詩曾經給過我深刻的印象。
但是這是真的我?興趣卻有點兒矛盾。我雖然每次寫過一些詩後就反悔,卻從來不討厭「看」詩,而是喜歡「聽」我爸爸讀詩或談詩。一個不願吃鴉片煙的人卻喜歡躺在坑上聞聞香氣,這當然是夠危險的了。我中學時代寫了一千多首詩,正式從這種矛盾的心情裡擠出來的。我終究沒法兒「解除這蠱惑了我許久的符咒」。
後來我又讀了好些西洋的詩,我發現這個世界上的詩的花園多的很,每個詩園裡都有許多美麗的花朵。我雖然自己不想去做一個園丁,可是往往信步走過那些花園時,有時也不免偷偷的摘下一些零花剩草,或者在地上拾起些沒人注意的落了的花瓣,藏在衣襟裡,想拿回去向朋友們誇耀。―這就是我譯的這些小詩。他們不只來自一個花園,他們原來生長在各種不同的土壤裡,開放在各種不同的角落裡。他們不一定都是頂偉大的或頂好的;只是因為當我走過他們身旁時,投合過我當時的偏好,曾經引起過我注目,曾經感動過我一次或多次,我就顧不了別的,居然把他們譯出來了,把他們採摘回來了。我明明知道:花朵是不可摘的,詩是不能譯的。我「採摘了他底花瓣,卻並沒有時得他底義」。我恐怕這帶回來的花瓣早已失去了那原有的顏色和香氣。但是讀者啊,我已經盡了我底心了,除了這,我還能做什麼呢?
東風吹來了,滿園丁裡的花給吹散了,不同園裡的花朵無計畫的,無目的的給吹在一起了。路旁人咒罵這無情的風,這沒有天才的風,摧殘了那嬌嫩可愛的花容。然而這不討你的風卻盡了個媒婆的職務。從前創造社的人,為了譏諷文學研究會,就說:翻譯只是個媒婆,創作才是處女。但媒婆底職務又有什麼可懺惶的呢?風沒帶來美,它卻希望在詩底紅繩下傳播些種子,讓我們詩園裡將來能開出我的花朵,結出我的果實。這開花結果原是讀者自己底事。「一個孩子底自願就是風底自願。」譯者底志願也只是一個「風底志願」罷了。
真的,我在園裡拾起了一些花瓣,就問她們做我底人。但是她們漲紅了臉不答我,我卻不能忍心把她們放下,我是要「尋遍花蕊,想找到可能長著一顆心的幽境。」
從小孩子的時候起,我也曾有過多少壯志和願心,無論是實際的或是空想的,平凡的或是光怪陸離的,哪一樣沒有?只是從來不曾想到要翻譯什麼新詩。
我還不認識字的時候,姐姐就教會我背熟了《對子書》、《唐詩三百首》、和《千字詩》裡面的句子。後來發覺,爸爸要老師首先教我的是《聖經》,以後唸「人,口,耳,刀,弓,牛, 羊……」我十二三歲時最初在報紙上和雜誌上發表的作品也是詩。這樣看來,我和詩從小就有了密切的關係了。可是也就從那時候起,我就有了一種動機,總想把詩戒掉,像一個在道德上和衛生上有了深痛的覺悟的人立志要戒掉鴉片煙一般。我寧願談戰略,搞政治,評論政策和國事,鼓吹時代思潮,或者研究自然科學,寫小說或劇本,什麼都高興,只是絕對不想做詩,更不想譯詩。襲定庵(自珍)那許多「戒詩」的詩曾經給過我深刻的印象。
但是這是真的我?興趣卻有點兒矛盾。我雖然每次寫過一些詩後就反悔,卻從來不討厭「看」詩,而是喜歡「聽」我爸爸讀詩或談詩。一個不願吃鴉片煙的人卻喜歡躺在坑上聞聞香氣,這當然是夠危險的了。我中學時代寫了一千多首詩,正式從這種矛盾的心情裡擠出來的。我終究沒法兒「解除這蠱惑了我許久的符咒」。
後來我又讀了好些西洋的詩,我發現這個世界上的詩的花園多的很,每個詩園裡都有許多美麗的花朵。我雖然自己不想去做一個園丁,可是往往信步走過那些花園時,有時也不免偷偷的摘下一些零花剩草,或者在地上拾起些沒人注意的落了的花瓣,藏在衣襟裡,想拿回去向朋友們誇耀。―這就是我譯的這些小詩。他們不只來自一個花園,他們原來生長在各種不同的土壤裡,開放在各種不同的角落裡。他們不一定都是頂偉大的或頂好的;只是因為當我走過他們身旁時,投合過我當時的偏好,曾經引起過我注目,曾經感動過我一次或多次,我就顧不了別的,居然把他們譯出來了,把他們採摘回來了。我明明知道:花朵是不可摘的,詩是不能譯的。我「採摘了他底花瓣,卻並沒有時得他底義」。我恐怕這帶回來的花瓣早已失去了那原有的顏色和香氣。但是讀者啊,我已經盡了我底心了,除了這,我還能做什麼呢?
東風吹來了,滿園丁裡的花給吹散了,不同園裡的花朵無計畫的,無目的的給吹在一起了。路旁人咒罵這無情的風,這沒有天才的風,摧殘了那嬌嫩可愛的花容。然而這不討你的風卻盡了個媒婆的職務。從前創造社的人,為了譏諷文學研究會,就說:翻譯只是個媒婆,創作才是處女。但媒婆底職務又有什麼可懺惶的呢?風沒帶來美,它卻希望在詩底紅繩下傳播些種子,讓我們詩園裡將來能開出我的花朵,結出我的果實。這開花結果原是讀者自己底事。「一個孩子底自願就是風底自願。」譯者底志願也只是一個「風底志願」罷了。
真的,我在園裡拾起了一些花瓣,就問她們做我底人。但是她們漲紅了臉不答我,我卻不能忍心把她們放下,我是要「尋遍花蕊,想找到可能長著一顆心的幽境。」
周策縱
一九五七於安娜堡
一九五七於安娜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