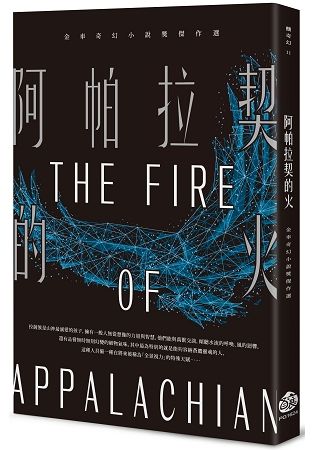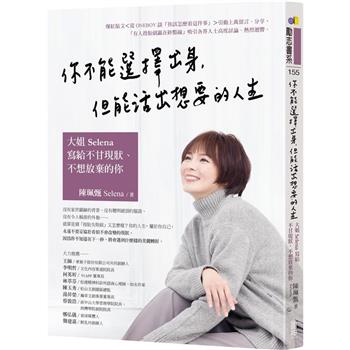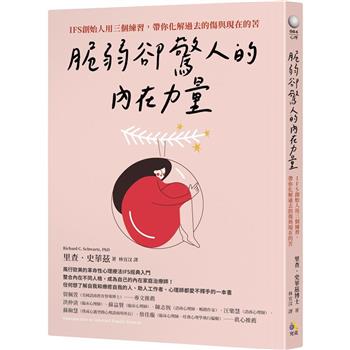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阿帕拉契的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小說 |
$ 221 |
現代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奇幻小說 |
$ 252 |
小說 |
$ 252 |
現代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 270 |
小說/文學 |
電子書 |
$ 280 |
奇幻\科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拉薩族是山神最溺愛的孩子,擁有一般人無從想像的力量與智慧,他們能與萬獸交談,傾聽水流的呼喚、風的迴響,還有品嘗無時無刻幻變的植物氣味。其中最為特別的就是能夠容納蒼鷹靈魂的人,這種人具備一種在將來被稱為「全景視力」的特殊天賦……
西式奇幻(《魔戒》、《哈利波特》、《冰與火之歌》)X中式玄幻(黃易《尋秦記》、霹靂&金光布袋戲)的本土繼承者──就在這裡!
台灣原創奇幻唯一指標──金車奇幻小說獎.得獎傑作選奇想展翼第四卷!
王麗雯〈流放矢車菊〉
混種人魚容克海倫有著古怪的姓名,顯赫的家世,在種族肅清運動中被流放至荒涼苦熱的矢車菊島。在荒島上她被迫照顧一種神秘野獸,因長官莫名的器重成為少數享有自由的囚徒模範。流放期間她反覆思索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我」是什麼身分,卻始終沒有滿意的答案。
邱常婷〈阿帕拉契的火〉
來自東方的人類學系副教授與其學生,前往阿帕拉契山脈尋找一棵千年巨樹,卻遇到了守護古樹的少數民族耆老,這名老者於是向他們娓娓道來一個從未有人知曉的秘密……關於神秘的拉薩族,桑奇與萊昂,以及那些曾經存在最終卻滅絕的生物,牠們最終的天堂。
林子瑄〈蕭月孟國離野納三界〉
滿洲國有著滿清最後的皇帝、擅於戰爭的東北漢子、爭取韓國獨立的革命家、以及中國軍隊的菁英軍官,還有俄國人與蒙古人。在如此眾多的種族民族身分裡,有著幾位擁有異能的奇才,他們效忠所屬的政治軍事團體,在烽火蔓延的時代裡,為主子解決科學軍事武力無法解決的案件。在深夜的烽火領土間,這群人領了主子的命令,翻山越嶺抵達荒野,著手處理正在發生的詭譎異象……
沈琬婷〈峽海紀年〉
「如果一個民族,從來沒有文字、沒有史書傳世,那會怎麼樣?」自由潛水的好手王亭在一次深潛意外中,無意間來到了一個異樣的世界──峽海。峽海為兩座陡峭山壁間的孤獨海洋,以海生的種族為統治者,統治著海洋與山壁石洞間的哺乳類。峽海沒有文字,國族歷史倚靠御用詩人代代相傳,改朝換代時,必先殺前朝詩人。王亭受當朝詩人所託,將峽海的歷史以文字寫下,以便日後攜回峽海流傳,但當王亭返抵峽海,時間卻已經過百年,正逢王室兄妹爭權,她手中的史書意外成為了必爭之物,而她也陷入了王室鬥爭與歷史正偽的衝突中………
江尋〈狐狸城〉
燈籠火光照耀的原野景色不斷向後退,長草往兩邊被撥開,這座城自己在動,以近乎奔馳的速度往某個不知名的方向移動著,而我認知裡的泉水聲,其實是這座宅邸踩濺泥沼的聲響。
這城跑著、向何處跑著?為何而跑著?如果這不是夢,實在無法解釋我身在哪裡。
作者簡介
[策劃]金車文教基金會
奇幻文學作品可以奔馳在浩瀚宇宙、穿越時空,讓作者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在這個獎項中,奇幻風潮因眾多優秀作品而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在未來,我們期許讓這股奇幻的河流,陸續地匯入各屆傑出作者的想法,提供讀者徜徉在這片時而寧靜、時而洶湧的奇幻海洋。
王麗雯
台大中文所碩士,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金車奇幻小說獎、台大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菊島文學獎、台北市青少年文學獎等獎助。
邱常婷
一九九○年夏天出生,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畢業。對於撰寫故事異常執著,也從事同人小說、類型主題的創作,期望像卡森.麥卡勒斯一樣,與所創造的人物生活在一起。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瀚邦文學獎、金車奇幻小說獎等。目前任職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閱讀的島》獨立書店誌雜誌編輯,出版有小說《怪物之鄉》。考慮在人生的後半段,到家鄉的海邊開一間小書店。
林子瑄
現職為雇員,主要於整理糾結事件的文書工作,於假期時才能從事創作,對於文學創作仍抱有理想,自我期許能有更多作品問世。
沈琬婷
作家,劇場藝術工作者。台北出生、新竹長大,在嘉義的鄉間度過童年時光。台灣文學獎與台北文學獎雙料得主,劇本作品於台灣、香港等地多次上演,同時也以偶戲工作者身分於亞太傳統藝術節擔任駐村藝術家,現居於上海進行駐地寫作計畫。
江尋
世新大學數位愛文芒果設計學系畢,現職為秋刀魚。
最近的煩惱是不想動,最近發生的特別開心的事情是發現每工作五天就有兩天可以躺在家裡動也不動,如果可以隨便許一個願的話希望快點世界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