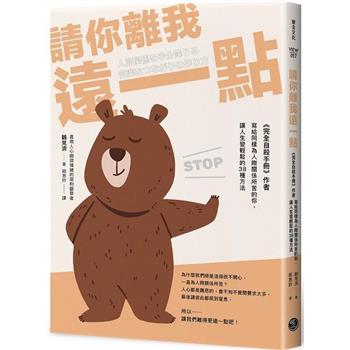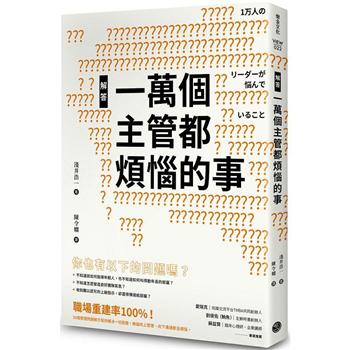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第一章 七年後的台中】
七年後,我終於回到台中了。
我站在大樓落地窗前,俯瞰前方的校園,育才中學。
那裡,是我踏入台中黑道的起點。
落地窗外,成片的幽深烏雲像一塊巨大的簾布蓋住整片天穹,磅礡大雨從昏暗的天空中倒灌而出。雨珠,紛紛從天空摔落地面。
這座寧靜的盆地裡,總是下著不寧靜的雨。
七年前,在一次次的戰爭和算計中,那些大人物們就像那些雨珠,紛紛從權力的頂端驟然墮入深淵,儘管有人先有人後,但最終都只能淪為一攤攤被車子輾過的水窪。
但我原該是陷在泥灘裡的水滴,卻在被疾駛的車子輾過時意外濺起,乘著風飛上高空,脫離地心引力的桎梏,越飛越高。
越飛越高。
育才中學,台中市,直到看見整個台灣。
我走出大樓,撐起傘走在育才中學校門前的街道上,隔著雨幕仔細尋覓著我記憶裡的台中,這個我又愛又恨,卻又害怕得逃避了七年才再次回來的城市。
在育才中學側門對面,有一間用鐵皮隨意搭蓋起來的簡陋麵店,我收起傘走進去找位置坐下,跟老闆叫了一碗麵。此時店內已經先來了三名育才中學學生。麵店老闆一面煮麵,一面和那些學生閒聊。
「老闆,七年前的台中到底有可怕啊?我爸媽打死都不肯跟我們講以前的台中是什麼樣子,我上網查了以前台中的資料,照片裡的街道到處都是屍體和血跡。」
其中一名身材纖瘦的學生問到了過去的台中,麵店老闆眉頭緊皺,似乎不願意回想起來。
麵店老闆望著店門外滂沱大雨,沉默了足足有一兩分鐘,然後嘆出一口長長的氣。
「七年前的台中啊,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直接由黑道治理的城市,那時候還和墨西哥市、西西里島並稱為世界三大黑道之都。哪個人能打下地盤,他就可以在那裡收保護費,當時的賭場和酒店附近,每天晚上幾乎都有槍戰和械鬥,這樣子當然到處都是屍體和血跡,一到早上,清潔隊員除了要掃馬路,也要順便幫忙收屍。」
那些學生聽了麵店老闆的話,紛紛驚呼出聲。
「老闆,那台中黑道是怎麼消失的?」
另一名帶著粗框眼鏡的學生問道。
「你們聽說過『夜梟』嗎?」
麵店老闆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反而又拋出了一個問題。
「我有聽過,好像是……台中黑道上一個非常厲害的殺手。」
染著咖啡色頭髮的學生回答道。
麵店老闆將煮好的麵放到托盤上,端到那些學生的桌面上,接著說下去。
「『夜梟』他可能是當年台中黑道裡面最強的殺手。那時候台中黑道上原本的四大王牌殺手,他們後來有三個人就死在『夜梟』手上,『夜梟』的實力你們可想而知。據說,當時隻手遮天的台中黑道突然倒台,就是因為他。」
「『夜梟』再怎麼厲害,也不可能一個人摧毀掉當時的台中黑道吧。」帶著粗框眼鏡的學生聽了麵店老闆的話,立刻反駁道。
「『夜梟』他不只是一個殺手,他曾經控制整個台中海線,還是當時台中黑道首領陳總的重要左右手,只是誰也沒想到他後來居然會背叛台中黑道,掀起一連串摧毀台中黑道的戰爭……。」
麵店老闆一邊將我點的麵端到我桌上,一邊繼續和那些學生敘說七年前的往事。我吃著麵,靜靜聽著。
我叫謝哲翰。七年後,已經沒有人知道,我就是夜梟。
【第二章 大哥,無所不在】
自從我有記憶以來,黑道就根植於台中的土壤中。
大人們總是不停地提醒著我和所有生長於台中的孩子們:「你要聽大哥的話。」因為,台中是由大哥們控制的城市,他們的手緊緊抓握著台中每一個角落。
大哥,無所不在。
有的大哥在整個台中都有著呼風喚雨般的力量,他能夠決定眾人的命運。
陳總,他是台中黑道的領袖,也是台中實際上的市長,台中市的市中心是直屬於他的地盤。坤哥,他掌管台中的山線地帶。而台中海線,則是由洪阿彪掌管,但我們海線人大多叫他「洪董」。
有的大哥只控制一個區,一個里,甚至只是某一條巷子裡的住戶。
我從小就習慣聽到家裡附近如連串鞭炮炸響般的槍聲,而且懂得不要多問關於這些槍聲的事,當槍聲響起時,我通常是在母親嚴厲的眼神暗示下,乖乖回房間裡躲好。等到我大一點之後,也就明白那些都是忘了上繳保護費或是得罪了控制我們社區的大哥的倒楣鬼。
但台中人卻也不能沒有這些大哥,我的鄰居和長輩們既對那些大哥們心懷畏懼卻又心存感激,他們最常說的話就是「如果不是這些大哥,我們哪有錢賺?看看台灣其他地方的人,都窮到快餓死了。」
大多數的台中人都只是討口飯吃的普通人。有的人在南區的豪華賭場裡發牌。有的人在神岡的鐵皮屋工廠裡組裝槍枝零件。有的人在外埔的製藥廠裡提煉海洛因。而許多漂亮的女孩子,上了高中後就會有人找她們到西區的那些酒店裡上班。但台中人不管在哪工作,無非都是在這些大哥手下的公司裡,若不是選擇進入黑道,就是成為大哥的奴僕。
在台中,只有極少數人能成為例外,我們家是其中之一。
我父親在大甲開了一間小武館,收了十來個徒弟,教授一些講求實用的徒手綜合格鬥技和刀術。在台中,到處都開著像這樣的武館。畢竟,在台中這個黑道之城,許多人都是以拳腳和刀械討生活。
父親總是自豪地說,我們謝家是世代相傳的武術世家,我從十二歲開始,他就帶著我學習綜合格鬥技和刀術,起初我仍然不太相信,我們家不過就開了一間普通的小武館,算什麼武術世家。
我十四歲那年,我父親便帶著我前往他朋友開設的武館,和裡頭的人進行切磋。經過一場場對戰後,我發現我的對手裡頭,竟然沒有一個人是我的對手,他們的出手時機和臨場判斷在我眼中簡直跟沒練過格鬥的普通人差不了多少。此時,我才相信父親的說法,我們家或許真的世世代代累積了豐富的戰鬥經驗和技巧,才會讓我和其他武者有著巨大的差距。
那時候,讀書和練武就是我生活的一切。我天真地以為,我家和周遭那些鄰居不一樣,我們可以不跟台中黑道打交道,安安穩穩地過著自己的日子。而我的未來,如果不是把書唸好帶著家人離開台灣,不然就是回到家裡像父親一樣平淡地經營著武館。
在我進到育才中學之前,都是一直這麼堅信著。
育才中學是台中第一志願高中,儘管我因為花了許多時間在練武,在校綜合成績並不算太好,但我在數理方面有些天分,透過參加育才中學舉辦的數理資優特考後,也考上了育才中學。
能考上台中第一志願高中,我父親當然非常高興,他對於我就讀育才中學唯一不滿的地方只有育才中學位在台中市中心,實在離家裡太遠了,因此我必須住在學校宿舍裡。
我還記得,開學第一天的清晨六點,父親原本要親自開車送我到育才中學,我一再拒絕後,他才打消這個念頭,讓我自己揹著書包搭公車到學校,但父親仍然堅持要陪著我走到公車站。
在前往公車站的途中,會經過鄰居翁媽媽的家。那天我走到她家門口時,翁媽媽的女兒剛從家中走出來,翁媽媽的女兒大我一屆,也是就讀位在台中市區的高中,就在翁媽媽的女兒扣上家中大門時,翁媽媽急促的聲音從門的另一頭傳出來。
「阿妹仔!」
翁媽媽的女兒聽到她母親的呼喚聲,停下腳步,臉上露出不耐煩的表情。
「幹嘛啦,我要趕公車。」
「你又忘了帶槍了,每次都要提醒你。」
翁媽媽從家裡衝出來大聲喊道,她左手拿著手槍右手抓著三個彈夾,急忙追上她女兒,把手槍和彈夾塞進書包裡。
「你喔,就是不聽話,去台中市區上課還不帶槍,這樣很危險知不知道,妳昨天有沒有好好練槍……。」
父親看到翁媽媽急著跑出家門送槍,在她女兒耳邊嘮叨,似乎也想到了什麼,轉頭望向我。
「阿哲,你需要配槍嗎?」
我想了想,還是拒絕。
「我唸的是育才中學的數理資優班,那裡的同學應該沒有混黑道的,帶槍去上課,反而好像怪怪的。」
父親點了點頭。
「育才中學畢竟還是台中第一志願,不像其他高中都充滿細漢流氓,不過你還是要小心一點,在育才中學裡面有個特殊班,裡面的學生都是台中道上大哥的小孩,千萬不能招惹他們,不要以為你很會打,惹到台中黑道,我們全家就完蛋了,知道嗎?!」
「我知道,我會遠離那些人。」
前往公車站的這一路上,父親不停提醒叨念著大大小小的事,無非是要我好好照顧自己用功讀書之類的話。最後,他在公車站一直待到看見我上了公車,和我揮手道別後,才轉過頭走回去。
許多年後回想起來,這是父親第一次送我去上學,但也是最後一次了。
【第五章 山鬼】
一個月後,我拿著林敬書給我的試驗資格書,前往台中南屯一處郊區,等豺狼的人前來接我。
豺狼沒有透露關於他的試驗的任何資訊,只曉得參與者須在指定地點時間內出現,允許攜帶一件冷兵器,熱武器統一由豺狼提供,至於其他具體規則和地點沒有任何人曉得。
早上十點三十七分,我看了一下腕錶,這時間豺狼的人該來了。
我正想著這件事時,一輛 BMW 汽車開到我身旁,車門打開,一個身材魁梧的撲克臉男人打開車門走出來。
他看了我一眼,再拿出事先約定好要讓我看的驗證文件,這是為了避免有人冒充豺狼的人殺掉參與者。
「謝哲翰?」
撲克臉男人冷冷問道。
「對。」
「戴上。」
撲克臉男人從車上拿出一只頭罩。
「這是做什麼用的?」
「為了不讓你知道試驗的地點,你必須戴上頭罩,你可以放心,那個地方對於所有試驗者都沒有優勢,老闆對每位參與者都一樣,你們都要戴上這個頭罩,另外,這輛車有特別的隔音和避震設計,你們是絕對無法從視覺外的任何感官得知你們所在地點大概位置。」
撲克臉男人解釋完也不囉唆,粗暴地把頭罩套到我頭上後,就把我推進去車裡。確實如他所說,在我心中估算約三小時的車程中,我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聞不到任何具辨識意義氣味也感覺不到震動,這車程也未必是抵達目的地的最短車程。抵達目的地後,撲克臉男人才解開我的頭罩。
我一睜開眼下車,發現四周就只有我和撲克臉男人,沒有其他參與者。
我在山裡,全然陌生的山林。
「這裡是哪裡?」
「你不需要知道。」
撲克臉男人依舊是異常冷漠的姿態。
「其他人呢?」
「待會你就會見到了。我現在先告訴你遊戲規則。試驗方式是這樣,包括你在內的所有人現在都已經被丟進這座山裡,他們處境跟你一樣,也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替他們解說,你們每個人手上會有一張地圖,一把手槍和一把突擊步槍,還有一些彈夾,每個人的彈匣數都是一樣的,地圖上會有路徑圖,你們只要走在路徑上就一定會相遇,目的地則是在山頂。當你抵達山頂後,在場的人中,包含自己的地圖,手中地圖數最多的兩個人,就是老闆要的人。當然,如果你害怕不想玩了,沿原路走回去,或是乖乖交出地圖就能活命。」
聽完他的說明,我開始提問。
「如果不走在預定路徑上的話會怎麼樣,這試驗既然是在山裡,你們怎麼掌握過程不會出亂子?」
撲克臉男人露出殘忍的笑容。
「因為啊,這座山,就是『山鬼』的地盤。這裡是我們跟山鬼約定好的借用場地,你們出了路徑,就算是進了山鬼的地盤,別想活著走出去了」
「山鬼?」
我疑惑問道。
撲克臉男人鄙夷地看著我。
「原來你不知道山鬼,我看你恐怕連『獵人』是什麼也不曉得,現在還有點時間,我就再仔細講,讓你不要不知好歹跑進不該去的地方。」
這次撲克臉男人終於願意多說一些了。
「『獵人』是一種保護目標不被暗殺的職業。獵人和殺手不一樣,殺手為了追求隱密性,執行行動時人越少越好,但獵人是守方,人當然是多一點好,甚至還有他們擅長的狩獵地點,那些付得起錢又怕死的人,知道有人想暗殺他,就會躲進獵人的地盤,直到獵人殺掉殺手為止。」
「山鬼就是所謂的獵人?」
「山鬼,就是台灣最強,也是亞洲數一數二的獵人組織,這片山林就是那些山鬼對付頂尖殺手的最佳獵場。」
撲克臉男人接著說起山鬼的由來,談話中,他的臉上竟然出現懼意。
所謂的「山鬼」,指的不只是那個獵人組織,也是他們首領的綽號,他本名叫莫那‧伊旺斯。
莫那是山地原住民,他靠著怪物般體能進了台灣最強特種部隊之一的涼山特勤隊。
莫那的部落位在台中山區,當年政府將莫那的部落強迫納入管轄範圍之後,部落裡的男人只能下山進城市當奴工,女人一個個被台中黑道拐賣進妓院裡。當莫那退伍後,才發現到自己的族人生活的慘況。
有一天,莫那路過位在台中北區的一間妓院時,看到他認識的一名部落少女,全身僵硬地被妓院裡的人從妓院門口抬出來丟到馬路上,那名部落少女,當然是死在妓院裡。據說那一天,莫那就單槍匹馬把整個妓院裡的人全部殺光。
自從莫那大開殺戒之後,他就開始隨機屠殺台中黑道中的人,並且放話,這一生中,他能殺多少台中黑道就殺多少,他要比台中那些惡鬼更殘忍。
莫那靠著軍中人脈,招來了一群軍中弟兄以及跟隨他的族人,訓練出亞洲最強的獵人組織之一─「山鬼」。在山林裡,他們就是跟魔神仔一樣的神靈,台中黑道每年都要死上好幾個大角頭和重要幹部,道上的人都曉得是山鬼幹的,但也從來沒有人敢踏進山鬼的地盤裡找他們報仇。
我聽完撲克臉男人的說明後,對台中黑道的處境毫不同情,在心裡為山鬼暗暗叫好。
「所以豺狼就故意向山鬼借場地,來確保他的試驗中道上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動手腳?」
撲克臉男人微微頷首。
「所以我要提醒你,你想離開預定路徑,想不遵守遊戲規則,依據老闆和山鬼的約定,這種參與者就隨便山鬼處理了。
我聽完撲克臉男人的說明突然想到一件事。
「參加人進到山鬼的地盤後,多久之內他們會動手?」
「一分鐘。你離開預定路徑一分鐘他們就會出手,可能是活抓你,也可能是直接殺掉你,看你的利用價值。不過能來參加試驗的人都不是普通貨色,你想的到的事他們也想的到。關於這次試驗的資訊我們只能提供到這樣,剩下的還是憑你自己的本事。」
男人馬上就看穿我的想法,我知道其他人肯定和我一樣,對於山鬼的復仇執念毫無畏懼,反而想利用他們來幫自己殺掉對手。
男人解答完我的問題後,便打開後車廂拿出一把M4A1和一把沙漠之鷹,連著地圖一起交到我手上。
「你們每個人同樣都會拿到這兩把槍和兩個彈匣,如果你有辦法殺掉對方,對方身上的東西全歸你所有。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都瞭解了。」
「那麼,試驗正式開始,希望我還有機會看到你活著出現。」
男人話說完,便開車離開,這片山林放眼望去四周就只剩我一個人,但我相信,沿路中一定佈滿了山鬼和豺狼的人。我將M4A1背在身上,左手握著沙漠之鷹,右手握刀,往地圖上的路線前進。
我一邊探路,一邊換算地圖上的距離所需的行走時間。山鬼佔據這座山本來就是為了改造成用於保護客戶、獵殺前來的殺手的陷阱,所以能供人行走的路徑極為曲折,我踩踏在遍地枯葉上,眼前的視線全被一顆顆巨大的老樹佔滿,看不見半個人影,對手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突然出現,我只能豎起耳朵仔細聆聽周遭環境的聲音,時時刻刻保持警戒。
我停下腳步,把身體重心壓低,走得更慢,一遇到轉角就停下來藏身探查,我往前走了十五分鐘,終於在遠方看到一個微小的人影,我一看到那個人影的同時,對方也立刻停下來,顯然對方也發現我了。
我們同時做了相同的事,迅速取出狙擊鏡裝設在M4A1上,朝對方扣下板機。
沒中,子彈飛出去的剎那,我快速估算出我們之間的距離,七百公尺。
此時,我和對手做出不同的選擇,對方停在原地不動,準備再開一槍,我則提著槍忽左忽右以蛇行姿勢向前狂奔,我一口氣衝了兩百公尺才又向他開了一槍,這一槍雖然也沒能打中他,但他不再停留在原地,放棄遠距離狙殺我的念頭,選擇和我近距離接戰。
對方顯然是經驗豐富的老手,他也知道在五百公尺以內到二百公尺之間的距離是不可能用M4A1打中動態目標,而在二百公尺之內手槍更為有用,我們互相朝對方開了幾槍都被閃了過去,直到距離相差三公尺,我們同時抽出身上刀械加速衝向對方。
幾秒鐘之內,我手中的刀就和他的刀對上了。
一時間,我和他都想將對方手上的刀壓下去,就在雙方僵持之際,我持刀手的小拇指慢慢往下移,扣壓手中的刀握柄底部的開關,刀柄靠近護刃的位置驟然射出一道疾影衝向對方頭部,那人頭稍一偏就立刻躲過暗器,但他顯然被激怒了,爆發出一股力道把我的刀壓下去,在他眼裡我似乎已經支撐不住,等他攻破我的架子就能殺掉我。
所以,他到死前都不曉得自己是怎麼死的。
剛才朝對方射出的東西不是單純的暗器,那是一個前端成尖錐狀的微型飛行器,遙控器也藏在刀柄上,當他再次舉刀要砍向我時,微型飛行器同時刺進他的頸動脈中。
對手從頸動脈爆出的血噴的我滿臉都是,他瞪大著眼睛往後倒下,直到此時,我才仔細觀察起他。這是一個年紀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子,或許不到十八歲,我們沒有交談過,我也不曉得他是誰,但短短十分鐘內,他就死在我的手上,我沒有太多的感慨,在台中黑道裡,生死的邊界無比模糊,甚至,活著的人反而更辛苦,死掉的人反而安詳。
我從山道旁的樹上摘了樹葉隨意擦了下我的臉和飛行器,把飛行器重新收回刀柄裡,便開始收繳他身上的地圖和彈匣。
我收拾東西的時候,忽然聽到山道旁的樹叢有呼吸的聲音,旋即又消失了。我知道這就是山鬼裡的獵人,以他的本事是不可能讓我發現的,他是以這種方式提醒我,山鬼的獵人們正隨時盯著我們。
我已經沒有後路了,為了活下去,我必須踏過更多的屍體。
我殺掉第一個遇到的對手後,略為鬆了一口氣,我把東西收拾好才繼續往前走,因為下一步開始,隨時都可能會遇到下個對手。
我以為我已經夠小心,但我思路上的一個小小盲點,差點讓我一不留神就被殺掉了。
當我走到一處僅能讓一人通過的小徑時,一隻粗壯的手臂突然從山道茂密的樹林裡冒出來勒住我的脖子,那隻手臂的力氣大的嚇人,把我箝制的連喘氣都沒辦法。第一次,我產生了恐懼的情緒,我所有的本事在這瞬間都派不上用場了。
就在我大腦陷入空白時,我的腹部傳來一陣劇痛,讓我徹底清醒過來。對方應該是在看不見我清楚身形情況下逮住我,開了一槍,子彈擦過肚皮而已,讓我逃過死劫。
這瞬間,我把手中長刀的暗器發射口轉向後方,從我感應到的對方身形位置射出,對方終於頓了一下。
我沒有試圖把刀向後刺或是拔出我腰上的槍,現在他手上正拿著槍對著我,我的任何反擊絕對都比他的子彈慢,我當下立刻選擇衝進樹林裡,把對方撲倒在地,和他糾纏在一起,我忍著痛開始大聲倒數。
「五九。五八。五七。」
「沒用的。」
對方不停嘲諷著,我忽略他的聲音,死命壓住他,讓他無法有任何動作。
「我和你們這些菜鳥不一樣,我從一開始知道規則後,就利用一分鐘的漏洞拼命往兩旁的樹林裡鑽,每經過四十秒我就再回到路線裡。利用這個方法,我已經把山鬼和豺狼的人的分佈位置摸透了,他們的人可沒多到佔滿整座山,他們只是在某個固定範圍裡巡邏,只有你們這些白痴會以為山鬼有辦法在時間一到就能動手。」
我明白對方的策略了,但我相信,我的作法是對的。
「三九。三八。」
「白痴,繼續喊吧。」
我身下的人拼命掙扎,他手中的槍在我剛才那一撲擊時掉落,但他還想騰出手拔刀殺我。
「你可是中了一槍,距離最近的山鬼至少再一分鐘才能走到射擊位置,我看你還能再撐幾秒。」
我和對方都看見山鬼了,山鬼現在才出現在六七百公尺外山道的另一側,由於樹木和山道坡度的關係,山鬼至少要再花一分鐘,才能取得能夠殺掉他的位置,這一瞬間我心涼了一截,我猜錯了,對方說的對。
在遠處的山鬼突然就在原地停住,取出了一台約與機關槍差不多大小的機件出來,瞄準我們所在的位置,但這一點意義都沒有,從他那個位置開槍,子彈會被一堆樹擋住,從那麼遠的地方,就算他想連我一起殺也根本打不到。
但山鬼開得不是槍。
就在我快壓制不住的瞬間,對方身體忽然一僵,就徹底脫力了,我一感覺到對方脫力,毫不猶豫就跳回到預定路徑中,接著將對方也拖回來。
一把樣式怪異的短箭不偏不倚地穿過這個狡猾對手的脖子。
此時我才有機會仔細觀察這個差點殺掉我的人,他身上扎滿樹葉樹枝,連皮膚都抹上泥土。
「我們山鬼說要殺人就一定有辦法殺人。」
在遠處狙殺我的對手的獵人,此時慢慢走過來,聲音帶著濃重的原住民腔調,皮膚黝黑體格壯碩,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山鬼中的獵人,就憑剛才他那隻能夠繞過障礙物以弧線方向前進的箭,在這樣的山林裡絕對稱得上是鬼魅。
「你遇到的這個人叫扁鑽,十三歲就開始搶劫殺人,跟過好幾個角頭,在台中黑道混了五年,經驗可比你豐富多了,所以就把我們當傻子。」
「他到底是怎麼躲過我的視線的?」
我以為我已經夠小心了,沒想到還是中了埋伏。
「扁鑽在樹林裡拼命鑽,他找出我們真正的位置分佈後,就一路在樹林裡跑,時間快到時他就回到原路徑,找好適合隱蔽點,利用身上的偽裝藏好。他靜止不動時,在遠處你根本看不出他的形體,他準備殺你的時候,就會拉開我們跟他的距離,在你會經過的樹林裡埋伏。」
「你的箭是怎麼辦到的,居然能夠轉彎?」
站在我身前的山鬼輕蔑一笑,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轉頭帶著他剛才使用的武器,又走進山林裡。
「山鬼的箭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稱呼,我們是把這東西叫做甩箭,甩箭的發射動力也是用火藥,所以射程和一般的子彈一樣遠,但是他們的短箭在結構上的特殊設計,還有我們完全不曉得的發箭手法,讓他們的箭飛行時可以透過氣流作用來調整他們想要的前進弧線。」
一個穿著黑色衣服的陌生男人等到山鬼離開後也走過來,豺狼的人果然也在這裡,他解答了我的疑惑。
「剛剛山鬼也是利用規則上的漏洞想讓你和扁鑽一起死,這算是我的疏失,我會幫你做好簡單的包紮,再送你兩個彈夾做為補償,這樣應該可以吧。」
「這樣就夠了,謝謝。」
我並沒有要求什麼,豺狼的人已經盡力維持了規則的公平性,事實上,我會中招還是因為我太大意了,我讓豺狼的人幫我包紮好傷口後,我在原地休息了半個小時,又繼續前進。
下一次的對決我就沒這麼倒楣了,對手用槍的本事不如我,我憑著火力上的優勢輕易殺掉對方,又多爭取到一些時間休養。
依照地圖上的路線示意,我若在下一個岔路遇到對手,只要擊倒他就能走上山頂了,只是不曉得同樣爬上山頂的人有幾個。
在下一個岔路又遇到一個對手,這次遇到的對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個外型亮麗的長髮少女,當我們一看到對方的身影時,就互相朝對方開槍,對方也是個用槍老手。
因為不曉得攻上山頂的人還有多少個,能多保留一些子彈就多留一些,我定下計畫後,便不斷以蛇行姿態往前狂奔,偶爾開個一槍做防禦性反擊,沒有多久我就衝到她的身前,將刀抵住她的脖子。
她漂亮的大眼睛瞪著我,臉上充滿驚慌的表情,她發現我抵住她脖子的刀開始陷入肉裡後,便趕緊放下手上所有的武器,用哀求的眼神看著我。
「不要殺我,我給你地圖,放我回去好不好?」
她的樣子就像一個可憐而無辜的小女孩,而不是一個殺手,她沒有耍任何花樣,小心翼翼地從身上取出地圖交到我手上。
「我可以走了嗎?」
長髮少女的聲音又甜又柔,如果不是剛剛還在和她對戰,我根本不相信這女孩子會是殺手,地圖上頭有著和她身上一樣的香水味。
突然間,我的腦袋有些暈眩。我原本抵住長髮少女脖子上的刀從手上鬆開,拿著槍的那隻手,也垂放在腰間。
「把槍給我嘛。」
少女嘴裡向我撒著嬌,但她雙手可沒閒下來,硬是將我手上的槍搶過去。
「乖乖站好,不准動唷。」
少女用甜膩的娃娃音下了第二道指令後,便舉起手上的槍,對準我的頭頂。
不過,下一秒發生的事,是她絕對想不到的。
我一腳把她踹進了山道旁的樹林裡,拔出藏在褲檔裡的另一把沙漠之鷹對著她。
「我的槍已經對準妳,你只要敢動我就殺了妳。」
她用不可置信的表情看著我,但臉上哪裡還有一點剛才嬌弱的模樣。
「你怎麼抵擋住我的香水。」
「只要稍微有點警覺心的人都會感覺到不對勁,怎麼可能進來這種地方還會在身上噴香水。你身上的香水竟然還有迷暈人效果,確實讓我大開眼界,不過我一聞到你的香水就立刻閉氣,我的肺活量還夠支撐到殺掉你。」
雖然她不可能活著離開,但我對她非常敬佩,一點輕視的意思都沒有,她的殺人手法確實是獨出心裁。
她的眼神裡充滿了不甘願和憤怒,但沒有槍的她只能任我宰制。
「山鬼大哥,我故意留著不殺她,就是要給你享用的,不拿去嗎?」
她愣了一下,頓了一秒鐘才明白我的用意,一分鐘到了。
就這麼一瞬間,一隻短箭不知從何方猛然射進她的尾椎裡,一根套索隨之出現,套在她的身上,把她給拖進山林深處,我沒有如預料中再一次見到山鬼的身影,但還是看到我所要觀察的山鬼手段。
「不要啊!不要啊!豺狼哥,救我!」
她哭得淒厲無比,但沒人救得了她,她的四肢已經癱瘓動彈不得,恨死台中黑道的山鬼,不知道會怎麼凌虐她,但如果當初她真的願意交出地圖不再反抗,或許她就能平安離開了。
我聽著那女孩子的聲音慢慢消失在山林裡,也不曉得她會怎麼被山鬼凌虐,但我已經不想再去思考這件事了,接下來我就可以直接走上山頂了。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亂世無命:黑道卷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52 |
其他武俠小說 |
$ 25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84 |
中文書 |
$ 284 |
現代小說 |
$ 317 |
武俠小說 |
$ 324 |
現代小說 |
$ 324 |
文學作品 |
$ 324 |
武俠/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亂世無命:黑道卷
發跡於林榮三文學獎、奠基台中在地的異色作家
大哥正看著你!反烏托邦 ╳ 黑道江湖 原創社會派武俠作品
台中的孩子們從小就知道要聽大哥的話,因為這是一座由黑道控制的城市。台中人若不是加入黑道,便是成為黑道的奴僕,遵循著「反抗者橫屍街頭、歸順者分到甜頭」的邏輯為生。在台中之外,台灣各地的老百姓則成了財團和政客的犧牲品,在貧窮線上苦苦掙扎。
謝哲翰出生於武術世家,在父親培養下成為武術奇才,身懷「謝家刀」與「魚龍變」這兩項絕頂殺人武術。從未打算與黑道沾上瓜葛的他,卻陰錯陽差被迫踏入台中黑道,為求生存而展開一連串的打鬥搏殺。
謝哲翰很快明白,要自江湖抽身,唯有打倒江湖;但要打倒江湖,就必須控制江湖。他必須忍受肉體的凌虐、親信的背叛與心靈的孤獨,變得無堅不摧、六親不認,又不失去自我,才能找到出路。
在這個爾虞我詐、一山還有一山高的「人吃人」世界,面對無所不在的腐敗、欺壓與欺瞞,謝哲翰能否憑藉著一己之力,改寫江湖規則?
「每個時代的武俠,都是映照當下對社會的思考及批判。」──林立青
作者簡介:
Fant,曾獲文學獎若干,不務正業的生科人,寫過科學論文也寫過新聞報導時事雜文,寫純文學也寫通俗小說,喜歡挑戰新題材,希望作品《亂世無命》能帶著武俠小說爬過金庸這座高山,開拓屬於這個時代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社會派武俠。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七年後的台中】
七年後,我終於回到台中了。
我站在大樓落地窗前,俯瞰前方的校園,育才中學。
那裡,是我踏入台中黑道的起點。
落地窗外,成片的幽深烏雲像一塊巨大的簾布蓋住整片天穹,磅礡大雨從昏暗的天空中倒灌而出。雨珠,紛紛從天空摔落地面。
這座寧靜的盆地裡,總是下著不寧靜的雨。
七年前,在一次次的戰爭和算計中,那些大人物們就像那些雨珠,紛紛從權力的頂端驟然墮入深淵,儘管有人先有人後,但最終都只能淪為一攤攤被車子輾過的水窪。
但我原該是陷在泥灘裡的水滴,卻在被疾駛的車子輾過時意外濺起,乘著...
七年後,我終於回到台中了。
我站在大樓落地窗前,俯瞰前方的校園,育才中學。
那裡,是我踏入台中黑道的起點。
落地窗外,成片的幽深烏雲像一塊巨大的簾布蓋住整片天穹,磅礡大雨從昏暗的天空中倒灌而出。雨珠,紛紛從天空摔落地面。
這座寧靜的盆地裡,總是下著不寧靜的雨。
七年前,在一次次的戰爭和算計中,那些大人物們就像那些雨珠,紛紛從權力的頂端驟然墮入深淵,儘管有人先有人後,但最終都只能淪為一攤攤被車子輾過的水窪。
但我原該是陷在泥灘裡的水滴,卻在被疾駛的車子輾過時意外濺起,乘著...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推薦序/林立青】
這是我第一次推薦武俠小說。在我的閱讀經驗裡面,武俠小說像是時光機一樣,一但翻開了,就不覺自主的往下看下去。畢竟架空的世界裡面,所有的人性都放大了一些,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小孩,而每個小孩,都曾經希望自己是個俠客,當一個俠客必定會有現實中無法取得的絕世武功,至於武功有多強,武功怎麼用,都吸引人繼續看下去,暫時地逃離一下現實,也從虛構的故事中,更看清楚現實世界的人性,看清楚每個角色的位置、選擇及無奈。
這部《亂世無命》,故事設定在中學,讓我回想起自己依舊年少時,對什麼好像都懵懵懂懂...
這是我第一次推薦武俠小說。在我的閱讀經驗裡面,武俠小說像是時光機一樣,一但翻開了,就不覺自主的往下看下去。畢竟架空的世界裡面,所有的人性都放大了一些,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小孩,而每個小孩,都曾經希望自己是個俠客,當一個俠客必定會有現實中無法取得的絕世武功,至於武功有多強,武功怎麼用,都吸引人繼續看下去,暫時地逃離一下現實,也從虛構的故事中,更看清楚現實世界的人性,看清楚每個角色的位置、選擇及無奈。
這部《亂世無命》,故事設定在中學,讓我回想起自己依舊年少時,對什麼好像都懵懵懂懂...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林立青
推薦序/鄭立
人物介紹
第 一 章 七年後的台中
第 二 章 大哥,無所不在
第 三 章 入學
第 四 章 冬蟲夏草
第 五 章 山鬼
第 六 章 勝者即是正義
第 七 章 魚龍變
第 八 章 殺破狼
第 九 章 真正的殺手
第 十 章 滿洲國,寂寞如雪
第十一章 權貴譚家
第十二章 開戰時刻
推薦序/鄭立
人物介紹
第 一 章 七年後的台中
第 二 章 大哥,無所不在
第 三 章 入學
第 四 章 冬蟲夏草
第 五 章 山鬼
第 六 章 勝者即是正義
第 七 章 魚龍變
第 八 章 殺破狼
第 九 章 真正的殺手
第 十 章 滿洲國,寂寞如雪
第十一章 權貴譚家
第十二章 開戰時刻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