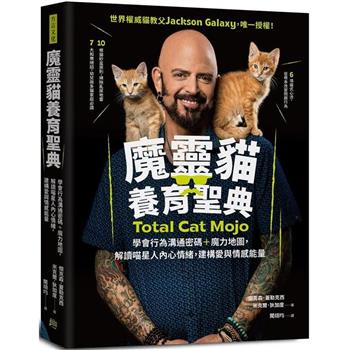隨著那顫動的音符,我彷彿看見光拍著翅膀
閃動於淒迷的月夜
棲歇在農舍初醒的寧靜屋頂上,徘徊駐足於窗邊
一轉身又迴翔縱情於原野之中,兀自低吟──
獨奏的琴音,悠緩地與自己對話,貼近靈思,引人冥想的鋪展出內在的極地風景。
《陽台上的手風琴》收錄了作者近十五年來的散文作品,篇篇意涵深蘊,文字優美,讓人感受到文章的悠遠與浪漫典雅。
琹川以詩、畫之筆來寫散文,在詩、文、畫三線藝術的「互文」之下,溶成她的精緻之形與溫婉之神。散文仍然沿襲著詩創作的彈性密度,如集中〈漫步在時光中〉所顯示詩化的情景交融。
琹川的創作到此,那已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新的桃源。在前只是妳偶然經過的客舍,今後,真希望妳能重視常住。
她使我了解到「伯樂」之「樂」。那是在你著力經營的一片園田之中突然開出了嶔崎之花,青青子衿非但足可承繼甚且已可超越,那一份欣慰何可言宣?
琴音迴盪,琹川清冽。願妳的詩、文、畫藝在長保自我風格之外更能溯洄向上,聲形終得成天籟之音,而質神則必是荊山之玉。──楊昌年教授
本書特色
1.收錄了琹川近十五年來的散文作品,搭配優雅畫作和珍貴照片,更顯風情。
2.篇篇意涵深蘊,文字優美,讓人感受到文章的悠遠與浪漫典雅。
3.楊昌年教授專文推薦。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陽台上的手風琴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03 |
華文創作 |
$ 229 |
中文書 |
$ 229 |
現代散文 |
$ 255 |
現代散文 |
$ 261 |
現代散文 |
$ 261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290 |
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陽台上的手風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琹川
本名洪嘉君,台南市新營人。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結業。曾任教職、專欄作者、蘭溪秋水主編等。作品選入《現代女詩人選集》、《台灣詩選》、《台灣飲食選》、《1960世代詩人詩選集》、《漢語新詩名篇鑑賞辭典》、《二十世紀華文愛情詩大典》、各詩社詩選及國內外各選輯等;小詩〈相思〉選入「台北捷運公車詩文名家經典作品」 。
著有:
詩畫集:《寂靜對話──琹川詩畫集》
新詩評論集:《詩在旅途中》
詩集:《凝望時光》、《風之翼》、《琹川短詩選》(詩集中英對照)、《在時間底蚌殼裡》、《飲風之蝶》、《琹川詩集》
散文集:《種藍草的女子》
筆記書:《貓咪小寶貝》
小說:《夢裡玫瑰》,後以《我是你的北極星》再版以及其他專著等。
曾多次應邀國內外舉辦詩畫展,畫作《供花》、《天馬行空》現為國家圖書館典藏。
琹川
本名洪嘉君,台南市新營人。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結業。曾任教職、專欄作者、蘭溪秋水主編等。作品選入《現代女詩人選集》、《台灣詩選》、《台灣飲食選》、《1960世代詩人詩選集》、《漢語新詩名篇鑑賞辭典》、《二十世紀華文愛情詩大典》、各詩社詩選及國內外各選輯等;小詩〈相思〉選入「台北捷運公車詩文名家經典作品」 。
著有:
詩畫集:《寂靜對話──琹川詩畫集》
新詩評論集:《詩在旅途中》
詩集:《凝望時光》、《風之翼》、《琹川短詩選》(詩集中英對照)、《在時間底蚌殼裡》、《飲風之蝶》、《琹川詩集》
散文集:《種藍草的女子》
筆記書:《貓咪小寶貝》
小說:《夢裡玫瑰》,後以《我是你的北極星》再版以及其他專著等。
曾多次應邀國內外舉辦詩畫展,畫作《供花》、《天馬行空》現為國家圖書館典藏。
目錄
序 洄溯琹川成天籟/楊昌年
│寧靜之外│
清晨微雨
血印梅春
火車飛過
邂逅花田
季節的陽台
緣於秋風
善意
我的遊樂園
藍色迴旋曲
默劇
尋寶
閒情
因為有光
一棵花樹
陽台上的手風琴
青春的容顏
旅行回來
寧靜之外
山居隨筆
靜聽那聲音
人間四月天
仲夏的花約
秋風裡的祝福
孤挺花
露易絲湖上的琴音
遇見
下著春雨的早晨
桐花盛開
慕夏之光
夏日遐想
自然的密語
仙客來
母親的南瓜飯
花園拼圖
│漫步在時光中│
春箋
夏花
秋遊
冬艷
雨桐
夏鬧
山居
雲箋
秋歌
冬眺
春信
風的顏色
三月的油桐
一日流逝
月光香水
秋日黃昏
諦聽
變天
夏之旅
蟬聲落處
時光海岸
之外
驚夢
風晨
復始
│流轉的風景│
戀戀龜山島
女兒國風情畫
詩路之旅──第二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紀行
青海塔爾寺之行
重回特勒吉
│閱讀手記│
我看金絲鳥
舞影者〈兼談海明威六篇短篇小說中之死亡〉
後記
│寧靜之外│
清晨微雨
血印梅春
火車飛過
邂逅花田
季節的陽台
緣於秋風
善意
我的遊樂園
藍色迴旋曲
默劇
尋寶
閒情
因為有光
一棵花樹
陽台上的手風琴
青春的容顏
旅行回來
寧靜之外
山居隨筆
靜聽那聲音
人間四月天
仲夏的花約
秋風裡的祝福
孤挺花
露易絲湖上的琴音
遇見
下著春雨的早晨
桐花盛開
慕夏之光
夏日遐想
自然的密語
仙客來
母親的南瓜飯
花園拼圖
│漫步在時光中│
春箋
夏花
秋遊
冬艷
雨桐
夏鬧
山居
雲箋
秋歌
冬眺
春信
風的顏色
三月的油桐
一日流逝
月光香水
秋日黃昏
諦聽
變天
夏之旅
蟬聲落處
時光海岸
之外
驚夢
風晨
復始
│流轉的風景│
戀戀龜山島
女兒國風情畫
詩路之旅──第二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紀行
青海塔爾寺之行
重回特勒吉
│閱讀手記│
我看金絲鳥
舞影者〈兼談海明威六篇短篇小說中之死亡〉
後記
序
序
洄溯川成天籟
楊昌年
琹川以詩、畫之筆來寫散文,在詩、文、畫三線藝術的「互文」之下,溶成她的精緻之形與溫婉之神。散文仍然沿襲著詩創作的彈性密度,如集中〈漫步在時光中〉所顯示詩化的情景交融。
集中的〈詩路之旅〉曾使我眼睛一亮,不禁反芻起曩昔:經歷過的青海湖,雖然只是乘船繞行一角,但已能感受到碧波萬頃的氣象萬千。由大湖想到長江、黃河,全都發源於這青海一省, 那可是孕育我華族生命、文化,橫亙南北的兩道巨流。其中的長江又與我的一生大有關聯,是我出生在長江下游,曾經沿著長江之湄,辛苦流浪到江的中段,又復跋涉到岸上有著點點金沙的上游。這江寬廣處有由此岸望不見彼岸,而湍急的三峽又竟是狹長如斯。它可是我永遠的魂夢牽縈呵!憶念當下,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蒼茫之情如浪湧來,使我愴然。湖海壯遊者何止千萬,人人感受不同。是我昔年飽經戰亂,飄蓬江海的坎坷伶仃經歷影響形成的感受,自然與琹川姑娘的有所不同。
感受最深的是集中的〈閱讀手記〉。一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述:重來崔護論評創作的形神兩勝使我驚喜。只是琹川她自動降等,把評價中的「最」高,降成為「頗」高。就是她使我了解到「伯樂」之「樂」。那是在你著力經營的一片園田之中突然開出了嶔崎之花,青青子衿非但足可承繼甚且已可超越,那一份欣慰何可言宣?
就「舞影者」這篇而言:我所佩服海明威的是他能以一己雄力來抗拒死亡。生與死歷來原就是人生調適的重要命題,總覺得我華族的「生寄死歸」不免有故示淡然的矯情。欣見他海明威另闢蹊徑,以雄力肯定存有挑戰死亡。不採慣性的坐等你死神光臨,我這就主動首途來找你,生與死的你我咱倆路上會面。一如遍歷十八層地獄的目蓮,非僅以他不凡的經歷足可睥睨傲世;更重要的是那一份充分發揮,肯定自我極其珍罕的人生價值。
當然,也如李太白在「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返」的了悟之後,終必有他「水中撈月」的決然奮身一躍。芸芸眾生與死亡的爭戰,總輸在吾人困守在短促、狹小時空的無奈命定。夕照蒼黃之後即是再無轉機的黯黑。即使櫪馬壯志未已又其奈時不我與何!誠如古挽歌「薤露」所吟:「薤上露,何易晞」道盡了人生悲涼。面對著看不到、摸不著,偏又能感覺得到虛無的死亡,力不從心的海明威的勇決轉向,面對自己扣下了板機。
這一集有詩有文復有評論,予人的感受各各不同:詩作的點有如針刺;散文的線可有牽引;更為龐沛的該是作用一如小說之面,戲劇之球的論評。琹川的創作到此,那已是「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新的桃源。在前只是妳偶然經過的客舍,今後,真希望妳能重視常住。
此後,一如教學之以自得助人,也就是迄今我們猶可仗恃著前行,並藉著這些點滴的快樂來與虛無調適的了。人生的「得」與「失」即在於此;我與妳前行後繼的轍迹亦是如此。
琴音迴盪,琹川清冽。願妳的詩、文、畫藝在長保自我風格之外更能溯洄向上,聲形終得成天籟之音,而質神則必是荊山之玉。雖然此一境界甚難企及,但誠如南宋詞作中的豪語「算事業須由人做」,又安知那些達標者中沒有我所期望的雋者琹川?
是為序
洄溯川成天籟
楊昌年
琹川以詩、畫之筆來寫散文,在詩、文、畫三線藝術的「互文」之下,溶成她的精緻之形與溫婉之神。散文仍然沿襲著詩創作的彈性密度,如集中〈漫步在時光中〉所顯示詩化的情景交融。
集中的〈詩路之旅〉曾使我眼睛一亮,不禁反芻起曩昔:經歷過的青海湖,雖然只是乘船繞行一角,但已能感受到碧波萬頃的氣象萬千。由大湖想到長江、黃河,全都發源於這青海一省, 那可是孕育我華族生命、文化,橫亙南北的兩道巨流。其中的長江又與我的一生大有關聯,是我出生在長江下游,曾經沿著長江之湄,辛苦流浪到江的中段,又復跋涉到岸上有著點點金沙的上游。這江寬廣處有由此岸望不見彼岸,而湍急的三峽又竟是狹長如斯。它可是我永遠的魂夢牽縈呵!憶念當下,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蒼茫之情如浪湧來,使我愴然。湖海壯遊者何止千萬,人人感受不同。是我昔年飽經戰亂,飄蓬江海的坎坷伶仃經歷影響形成的感受,自然與琹川姑娘的有所不同。
感受最深的是集中的〈閱讀手記〉。一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述:重來崔護論評創作的形神兩勝使我驚喜。只是琹川她自動降等,把評價中的「最」高,降成為「頗」高。就是她使我了解到「伯樂」之「樂」。那是在你著力經營的一片園田之中突然開出了嶔崎之花,青青子衿非但足可承繼甚且已可超越,那一份欣慰何可言宣?
就「舞影者」這篇而言:我所佩服海明威的是他能以一己雄力來抗拒死亡。生與死歷來原就是人生調適的重要命題,總覺得我華族的「生寄死歸」不免有故示淡然的矯情。欣見他海明威另闢蹊徑,以雄力肯定存有挑戰死亡。不採慣性的坐等你死神光臨,我這就主動首途來找你,生與死的你我咱倆路上會面。一如遍歷十八層地獄的目蓮,非僅以他不凡的經歷足可睥睨傲世;更重要的是那一份充分發揮,肯定自我極其珍罕的人生價值。
當然,也如李太白在「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返」的了悟之後,終必有他「水中撈月」的決然奮身一躍。芸芸眾生與死亡的爭戰,總輸在吾人困守在短促、狹小時空的無奈命定。夕照蒼黃之後即是再無轉機的黯黑。即使櫪馬壯志未已又其奈時不我與何!誠如古挽歌「薤露」所吟:「薤上露,何易晞」道盡了人生悲涼。面對著看不到、摸不著,偏又能感覺得到虛無的死亡,力不從心的海明威的勇決轉向,面對自己扣下了板機。
這一集有詩有文復有評論,予人的感受各各不同:詩作的點有如針刺;散文的線可有牽引;更為龐沛的該是作用一如小說之面,戲劇之球的論評。琹川的創作到此,那已是「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新的桃源。在前只是妳偶然經過的客舍,今後,真希望妳能重視常住。
此後,一如教學之以自得助人,也就是迄今我們猶可仗恃著前行,並藉著這些點滴的快樂來與虛無調適的了。人生的「得」與「失」即在於此;我與妳前行後繼的轍迹亦是如此。
琴音迴盪,琹川清冽。願妳的詩、文、畫藝在長保自我風格之外更能溯洄向上,聲形終得成天籟之音,而質神則必是荊山之玉。雖然此一境界甚難企及,但誠如南宋詞作中的豪語「算事業須由人做」,又安知那些達標者中沒有我所期望的雋者琹川?
是為序
二○一九年二月三日於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