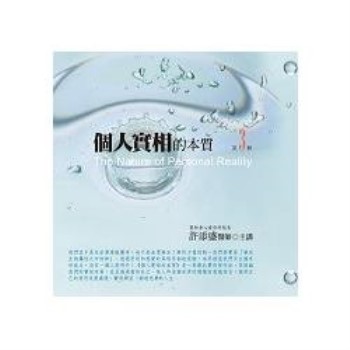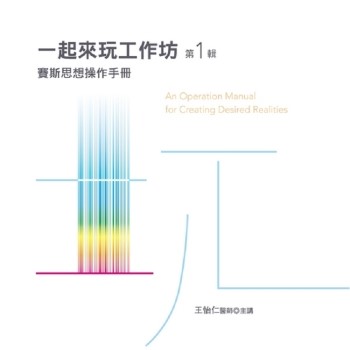罩在白紗裡的新娘子……她唯一能確定的是,
以後再也不用聽那些惱人的語言。
「妳該結婚了。什麼時候喝妳的喜酒?要快啊!」
那麼對她來說,好歹總是一個春天。
我們坐在這海邊上,營火照亮了我們的臉。遠方漁火點點,海潮輕聲拍岸。我們攜手同行,我們結伴尋歡。愛也要勇敢的愛,笑也要大聲的笑。
把握今天,莫負良宵,人生要及時行樂。──節錄〈我們攜手同行〉
本書為十篇短篇小說合集:〈祭壇上的紅蘋果〉、〈小蘋的夢〉、〈年終獎金、〈我們攜手同行〉、〈金耳環〉、〈金鎖記〉、〈鋼筆的故事〉、〈總是一個春天〉、〈花落知多少〉、〈父親〉。喬木秉持一貫流暢樸實的風格,題材皆為日常所及;用雋永的文筆,刻劃這些可能是你我身邊曾經發生過的故事。語調傳神、劇情真摯感人,彷彿冬日的太陽,在現代人忙碌冷峻的生活步調中,注入一股溫熱,溫暖彼此的心。
本書特色
●喬木,手持一支溫柔的筆,藉由文字,勾勒出暖暖的心意。
●文筆雋永傳神,故事真摯感人,擅長刻劃人物心靈的轉折與曖昧!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總是一個春天:喬木短篇小說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10 |
小說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小說 |
$ 270 |
小說 |
$ 270 |
現代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Literature & Fiction |
電子書 |
$ 30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總是一個春天:喬木短篇小說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