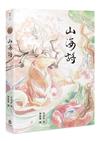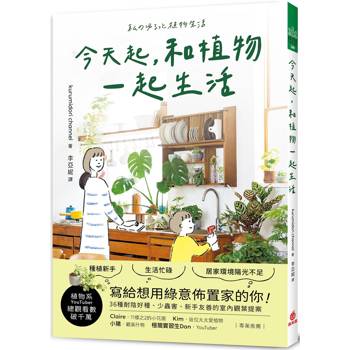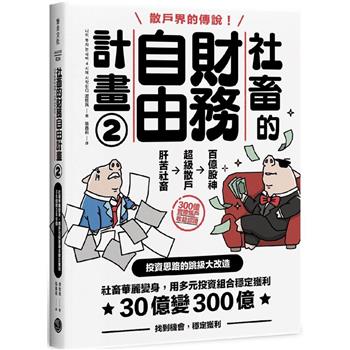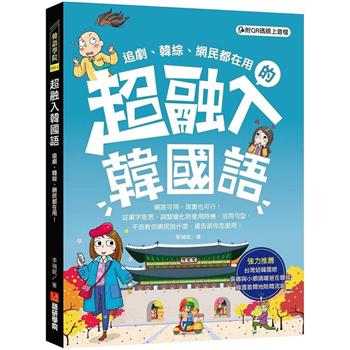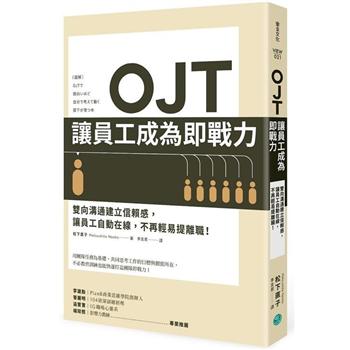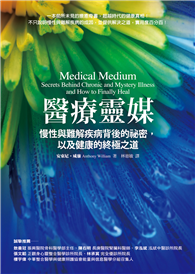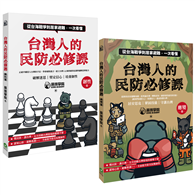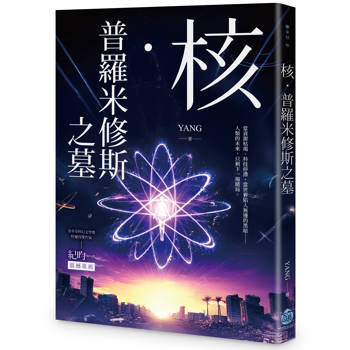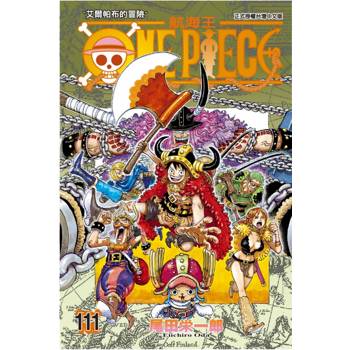★題材極為廣泛,結合了臺灣與世界諸地的神話書寫而成,宛如山海遼闊。
★上百個形式多元的「彩蛋」藏匿於圖文之中,發現便能引發新的感悟。
「當世界崩壞,人們該如何抉擇?」
以《易經》中八卦為基石,記錄了「風見雞」在八十八座山與海間冒險,看見不同的生命風景,找尋自己的解答。面對「世界傾頹,人們當何以自處」此一難題,詢問了諸位賢哲的解答,最終如獲頓脫,得以安處。
這不只是一本現代詩集,也是一本瀰漫奇幻氣息的神話圖鑑,以「藏寶圖」概念出發,所有詩篇皆有精美的獨立插圖,將上百個形式多元的「彩蛋」藏匿於圖文之中,讓讀者探索,按圖索驥,重返翻閱紙本書的感動。
《山海詩》記錄世界與每個生命個體。
所涉題材極為廣泛,大至經濟、政治、宗教、社會現象,狹至親情、愛情、友情及自我探求,並結合了臺灣與世界諸地的神話書寫而成,內容宛如山海遼闊。將實際面的社會議題,到心靈層面的生命難題,用富含故事性的口吻深入淺出、娓娓道來,是一本會觸動每一個世代與族群,帶來不同感悟與感動的繪本詩集。
作者簡介:
洪逸辰
INFP,Ω,火雷噬嗑,與松鼠為伍的人。
東吳大學中文系、日文系,北海道教育大學日本文化學程,臺北市立大學華語文教學所。
曾獲詩人流浪計畫、北海道函館市民文藝獎。
繪者簡介
陳馥蕓
澤風大過,間諜牡羊,性向是毛茸茸,胃裡住著一隻海月水母。
畢業於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主修立體造型藝術,結果畫了一本插畫。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陳芳明(詩人、史學家、文化評論家)
林士棻(插畫家)
羅智成(詩人、文化評論家)
陳義芝(詩人、文化評論家)
張曼娟(小說家、散文家)
鹿憶鹿(神話學家、散文家)
紫鵑(詩人)
楊宗翰(詩評家)
陳依文(詩人)
「這位年輕詩人的想像力,已經到了呼風喚雨的地步。當他的生命與整個天地結盟時,便掙脫了許多人為的禁錮。充滿生命力的詩行,從此就獲得無邊無際的空間。」──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專任教授
「《山海詩》這本書,說是現代詩,又像一個個小故事,一個個關於現實卻又奇幻的篇章,搭配馥蕓的插畫,是一本特別而有趣的書,希望大家都能在這片超現實的山和海之間翱翔。」──林士棻(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講師、插畫家)
「準備充分,編織細心,喜歡他一意孤行地用文字建構自己的心靈世界。」──羅智成(詩人、文化評論家)
名人推薦: 陳芳明(詩人、史學家、文化評論家)
林士棻(插畫家)
羅智成(詩人、文化評論家)
陳義芝(詩人、文化評論家)
張曼娟(小說家、散文家)
鹿憶鹿(神話學家、散文家)
紫鵑(詩人)
楊宗翰(詩評家)
陳依文(詩人)
「這位年輕詩人的想像力,已經到了呼風喚雨的地步。當他的生命與整個天地結盟時,便掙脫了許多人為的禁錮。充滿生命力的詩行,從此就獲得無邊無際的空間。」──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專任教授
「《山海詩》這本書,說是現代詩,又像一個個小...
章節試閱
〈神話〉
面對巨大的海洋
陽傘下的人事不關己,只用炭筆
塗黑面龐,曝曬肉體
岸邊的人撿撿回憶與貝殼
踏踏水,偶爾眺望遠浪翻白
打上灘岸,僅潑及足踝
鬱結的人徘徊沙濱
終於浸水,被海腰斬
再一步,又懼怕水中重力
當浪的手熊熊搧上臉頰,承受痛楚
便心滿意足,連同死去的貝
任軀殼沖上陸地
熱愛海洋的人水淹及頸項
隨波濤跳躍,以為能征服海洋
當巨浪鋪蓋,喫進一口海
只好感歎海的偉大 自身渺小
又再次愛上海洋
而我,在一次孤獨的浪潮中被捲去
就一直躺在海洋的中央
仰望天空 思考,星宿如何幻化聖獸
木火金水、司掌天地
凱斯托與普勒克斯難分難捨
指指緊扣,旋向天堂
耳在水中靜靜幽幽
美人魚的聲線如菌絲鑽入耳蝸
分生、蔓爬我的腦褶
每當思想如緒抽發,便朵朵綻放
釋放孢子,茸茸密密如蜂毛擴散
覆蓋腦面,萌芽,開成一片
蔥蔥蘢蘢、濃白的黴之原
終於侵占水晶體、藤布視網膜
睜開眼,眼珠的虹彩僅剩一簇白
黴從瞳孔竄出、拉線,隆隆
扭轉成強碩的母樹
枝條延展溢出了天邊,枒尖上
蕾苞珠珠攤瓣
吐露顆顆新星
閃爍了整座天空
臥於海心
我替祂們寫下一段段
你還沒聽說的神話
────────────────────
〈積水海〉
天空下起一場大雨
雨滴變成貓貓狗狗
各種奇怪又可愛的生物掉了下來
我是隻小螞蟻
經過一灘縮在路面窟窿裏
還在變形的積水
突然你踩過,濺了我滿身
悠悠地爬到邊邊
看見車子來來去去
大廈搖搖欲墜
雲朵撕扯融化
人們毫不猶豫地路過
完售的自動販賣機與海洋
偷偷跟你說
其實海裏頭,還有一塊油漬
迷幻著彩虹的光芒
────────────────────
〈文字海〉
每年的今天,天空
都會下一場文字雨。
數千年前,小鎮安恬
一卷陀螺似的暴風
突然天降
在山尖的藏書館上
萬本書捲入颫颻,渦旋、撕扯
文字傾灑而出
天空便下起文字雨
密語山為心,漪繞而散
田野村莊、零星島嶼
蔓至海外都市
全被文字的豪大雨侵襲
雨量驚人,積淹成海
人們左驚右詫地往高塔逃生
僥倖逃過的
卻也溼黏滿身
而絕大多數的人們沒頂、虛脫
漂浮於文字的海洋
數千年後,小鎮安恬
天空又下起一場文字雨
站在地窪,我們
雙手捧接
────────────────────
〈昏睡山〉
西方有一地,
棲息大量的催催蠅,
無人敢靠近。
傳說被催催蠅叮到
會得昏睡症
像吃了安眠藥
酣然入夢
所以失眠的人都聚集過來
失戀的人都聚集過來
失意的人、失語的人、
失格的人類全都匯聚過來
一塊昏睡,相互取暖
攀附坐臥,堆疊如山
只因身在多數
使人心安
於是人們盛傳
這兒是失眠者樂園
昏睡的山
〈密語山〉
傳聞密語山,
是世界最高的山,
纏繞真理的鎖鏈,
蘊蓄文字的源泉,
寄寓世上萬象的知識,
這裡,無惑不解。
肉體抵達不了密語山
只能透過靈魂
鍛鍊過的靈魂
穿越山中之山
像自然焚燒的森林得到解答
感應的人們
偷下未來的光譜
通曉命運
可沒有關係
命運不會受到改變
因為你的竊盜
也記錄在命運之上
不必沾沾自喜
是命運讓你找到祂
命運在密語山颳起了一陣風暴
知識與符號應然而飛
飛到人們的手上
請珍惜
那將是你畢生的寶藏
────────────────────
〈觀〉
我佇立瓦片鱗布的屋頂
注視著這個世界
有風拂動
我銅紅的翅羽
靜靜默默、直指向
風去的彼方
當我第一次,睜開雙眼
孩童翻越籬笆
於牛羊間欣喧
中央廣場人們瀏覽著
吟遊詩人的句法
午後市集商旅兜售著希奇珍寶
偶爾傳來村長的廣播
安於小鎮的詳和
我漸漸明白
凝望
稻田似漣漪讓風淪散
遠處山巒間,藍靄浮動
專注著月圓漸瘦、月弓漸豐以及
星辰漸昇的角度
慣於一切景色相關的細節
我學會了一種眼光
透視
崩沱夏雨中能看見星星
偵感紅葉上是否飽蘊溼氣
翅翼被海風輕蝕、冬陽呵暖
春日中靜默,能嗅聞淑氣
看穿時間的遞嬗
而勢必將學成一種,迴停的姿態
巧立如茶莖靜靜
暗喻,一道最終的捷徑
輕啜,漣漣波動
卻直浮不動
闔著眼,我目睹
三重山外,一位旅者負笈經過
一隻蠅被蛙舌捲食
以及一珠露滑過葉脈
萬萬事物隨冥思
瞭若掌脈
並逐一觀照個體
不摒除憤怒、怨懟、厭煩、
盲點,還是種種盛開如地獄之華
不發揚善的意念,任其生息
學會一種順應的儀姿
隨之旋舞
然後用光速,
陀螺似地,旋動
貌似靜止卻又疾馳穩妥
我開始能看見,四萬公里以外的事物
最終,見到自己
赤金的背羽反映銅澈的光澤
我看見自己軀體前方
下一秒有青鳥掠過
開始能看見,
明日
再次睜眼
仍是町鎮的安逸
我注視著整座世界
不遺漏一個角落
我是一尾風見鷄
靜靜、默默
佇立在命運的屋脊
洞悉微颸的指引
不曾偏移
〈神話〉
面對巨大的海洋
陽傘下的人事不關己,只用炭筆
塗黑面龐,曝曬肉體
岸邊的人撿撿回憶與貝殼
踏踏水,偶爾眺望遠浪翻白
打上灘岸,僅潑及足踝
鬱結的人徘徊沙濱
終於浸水,被海腰斬
再一步,又懼怕水中重力
當浪的手熊熊搧上臉頰,承受痛楚
便心滿意足,連同死去的貝
任軀殼沖上陸地
熱愛海洋的人水淹及頸項
隨波濤跳躍,以為能征服海洋
當巨浪鋪蓋,喫進一口海
只好感歎海的偉大 自身渺小
又再次愛上海洋
而我,在一次孤獨的浪潮中被捲去
就一直躺在海洋的中央
仰望天空 思考,星宿如何幻化聖獸
...
作者序
推薦序
抒情的神話與童話
洪逸辰獲得詩人流浪計畫,是在二○一八年十一月。他當時提出的寫詩計劃,是要去日本大阪中低收入戶生活區。那時我擔任評審,閱讀他的計劃與詩作,非常訝異如此年輕的詩創作者,擁有一份不尋常的人文關懷。在那之前,他的名字於我非常陌生。他提出計劃時,也附帶幾篇詩作,夾帶著豐富想像力,那時就強烈感覺這位詩人具有敏銳的心。在臺北齊東詩舍頒獎時,我才第一次與他認識。他的神情有些內向,表達語言時也有些羞澀,似乎與他計劃中所顯現的果決,頗有一些距離。獲獎後,他依照計劃前往大阪,停留期間在貧困地帶四處造訪。他可以使用日語,顯然與當地居民互動非常頻繁。對這位年輕詩人,我看得特別高,只因為他非常果敢,態度也親切溫和。更重要的是,他擁有豐富的想像力。所謂想像(imagination)是所有詩創作的原動力,通過想像才有可能釀造詩的意象(image)。走過他的詩行之間,總是會遇到突如其來的意象,那是從他內心底層湧發出來的真實感覺。
在完成《山海詩》這部詩集之前,他已經獲獎無數次。詩集中的作品,已經具備一種氣勢,而那樣的氣勢,則是由他無數的創作過程中所釀造出來。一位年輕詩人的誕生,並不必然要具備豐富的生活經驗,但至少他需要有勇氣去探索陌生的社會領域。閱讀他的詩作時,我才明白他為什麼要去大阪的貧民生活區。透過陌生水域的摸索,顯然可以使他的靈魂加寬加大。當他寄來《山海詩》這部作品時,我終於窺見他非凡的想像世界。捧讀《山海詩》之際,我立刻聯想到中國的古典作品《山海經》。在這部古典作品裡,可以看到許多奇怪的命名,例如:丹穴山、非山、陽夾山、雞山等。裡面充滿了神話與傳說,中文系畢業的洪逸辰想必對這部經典毫不陌生。
《山海詩》包含了許多山與海的故事,在傳說與真實之間,有意彰顯詩人靈魂深處的想像力。他對詩行的營造,充滿了各種嚮往與夢想。在虛實之間穿梭時,總是會帶出他個人真實的感覺。那是青春生命的活潑想像,也是他對理想國的嚮往與幻滅。很少有年輕詩人,敢於如此大膽探索自己身體內部的各種感覺。每種感覺就是一座山,每一種夢想就是一個大海。在痛苦與歡愉之間,往往出現相生相剋的意象。真與幻的文字,是那樣生動觸探了無法觸及的靈魂深淵。其中有卡通式的表演,也有喜劇式的擬仿,更有悲劇式的耽溺。在捧讀之際,不免會與這位詩人一起喜悅,一起悲傷。他的文字演出,似乎已經突破了非常遙遠的疆界,甚至已經涉入了情慾的禁區。這是我多年來,所遇到非常罕見的試驗與實驗。
這位年輕詩人的想像力,已經到了呼風喚雨的地步。當他的生命與整個天地結盟時,便掙脫了許多人為的禁錮。充滿生命力的詩行,從此就獲得無邊無際的空間。他的語言與文字,也因此而完全不受到羈絆。似乎海洋有多寬,天空有多高,他的遣詞用字就有無限的可能。那種童話式的語言,既帶著神祕的暗示,也帶著鮮明的感覺。讓所有的讀者受到牽引,去發現生命裡所未曾發現的世界。詩的前面兩行,如此引導著讀者:
每年的今天,天空
都會下一場文字雨。
以突發奇想的手法,勾引讀者的好奇心,不免會揣測什麼是「文字雨」。這樣奇妙的聯想,顯然是從童心出發,否則不可能把「文字」與「雨」連結起來。詩人有意把自己幼稚化,也把自己徹底矮化,才能夠以平視的眼光看見兒童的世界。對於大人而言,長期受到社會化與成人化的影響,最純真的心靈慢慢受到遮蔽。尤其受到教育體制的灌輸,便逐漸失去最純潔的想像力。文字最能夠彰顯人類的想像力,把具體事物化為抽象表現,是人類獨有的能力,所有的文字沒有固定意義。它之所以能夠那麼活潑,完全是因為透過人類的思考,而轉化成為意義的傳達。文字所及之處,也是人類生命力的延伸。詩人能夠化文字為雨,正好彰顯他能夠把扁平的意義,化為活潑的想像。
如果沒有具備一顆童心,就不可能超越所有文字障礙。他讓自己縮小,也讓自己矮化,就能夠看到成人所看不到的世界。詩集中的一首短詩〈日出海〉,只有六行,非常精緻:
安棲海底
涼冷如我的體溫
以為,已是最合宜的溫度了
直到一次躲不過日出
才愛上
太陽所溫熱的海面
歌頌太陽一直是現代詩永恆的主題,詩人擅長使用反語的方式,彰顯正面價值。長久棲息在海底的生命,可能已經習慣冰涼的水溫。只是不經意迎接一場日出,他才感受到海面的溫暖。童話式的語言,反襯一顆純潔的心。如果從未感受到日出的美感,這首詩似乎就無法誕生。他總是偏愛一閃即逝的美感,如果錯過就錯過了。這首詩的底層,暗藏了冰肌玉骨的想像。詩人所釀造的感覺,因為詩的存在而保留下來。另一首近乎童詩〈魚缸海〉的短作,也令人偏愛:
面著你
我成了豢養在透明水缸的金魚
緋紅著雙頰
「啵、啵……」
開口欲言
又說不出話語
啊啊,視線像水草纏繞我的鰭
游不出你的眼睛
水缸是一種囚禁的隱喻,被感情所苦惱的生命,唯一能夠逃脫的方式,便是獲得對方的回應。暗藏在內心的洶湧語言,似乎無法脫口而出。那種自我囚禁或自我監禁,暗示了多少千言萬語的感情,彷彿豢養在透明的水缸裡。只能受到觀看,卻無法說出滿腔的語言。這種單戀式、耽溺式的感情,以這樣的形式彰顯出來,正好定義了詩人的純真無邪。
相對於海的存在,詩集也集中描述山的羅列。海,主要表現於它的廣闊,還有它的深邃。山,則是強烈帶有崇高的意象,也有它堆疊的繁複。那種強烈的對比,顯然是在彰顯他內在世界的崇山峻嶺。許多遮蔽的風景,都暗藏在山的羅列之間。相較於水的透明,山則充滿了過剩的神祕。詩人想像便是透過山與海的辯證關係,而梳理出感情的矛盾,理想的嚮往。無論是崇高或是縱深,正好可以拉出詩人內心的繁複。夾在神話與童話之間,正好可以探測出詩人的聯想能力,透過隱喻、象徵的表現,而終於把許多欲語還休的語言呈現出來。真實的感情不可能給予確切定義,只能用迂迴的、隱喻的、間接的抽象語言呈現出來。詩集裡充滿了愛,卻又無法給予精準的表達。詩人這樣那樣的象徵手法,卻總是讓讀者在不經意之間感受到了。
充滿了童趣的〈糖果山〉,不免讓人聯想到從前童年時期讀過的一本《糖果屋》。童年是純真的原鄉,也是純潔之愛的故鄉,這首詩特別動人之處,便是詩行之間處處夾帶著童趣。其中有詩行特別迷人:
巨人的世界裏
是巧克力蝙蝠
蜜糖蜘蛛
棉花的狼
蝙蝠、蜘蛛、狼都是帶著負面的形象,但是在兒童的眼睛裡,因為還未經過成人世界的馴化,所以看待每一種生命都非常貼心。兩種悖反的事物並置在一起,就產生既和諧又相剋的意象。尤其是「棉花的狼」,不免使讀者會心一笑,甚至使人有一種想要擁抱的錯覺。巨人的世界其實就是兒童的世界,他們不知天高地厚,也無法分辨純潔與邪惡。他們可以把整個世界,無論善惡美醜都裝進小小心靈裡。詩人的童心在此又得到印證,內在的心靈有時非常膨脹,有時卻非常縮小。在極大與極小之間,正是兒童心靈的最佳寫照。
這首詩還夾帶了兩首短短詩行,一是「巨人笑了/氣息將我吹上雲端」;一是「巨人哭了/淚釀成我的水災」。在哭笑之間,正好烘托出詩人內心世界的純真。那樣無邪,那樣無垢,恰好可以用童詩的形式表現出來。詩人可以讓自己的心靈收放自如,也可以隨時膨脹、隨時萎縮。另一首詩〈水晶山〉,也表現了詩人晶瑩剔透的想像。這座水晶山住著大量的小孩,無論是肉體或內臟,全部都是水晶體。最奇妙之處,就像詩行所表現那樣:
水晶小孩注視彼此的瞳紋
透過光的折射
便能理解對方的思維
而肉體沒有侷限
可以是鬚髯綹綹的老人
童話的世界極大也極小,可以膨脹也可以縮小,可以遠眺也可以近望。他們的想像力豐富,詩人刻意貼近他們,使整個世界變成透明而活潑。這種童話式的表現,其實是在描摹愛的感覺。在愛裡充滿了想像,也充滿了生命力,只有把自己縮小成小孩,才可以使愛在每天成長。小孩的心廣闊如海,崇高如山,就像愛情那樣,整個世界隨時都可以變形。詩人刻意使用童趣的方式,重新看待這個世界。幼稚的心靈,正是詩的世界,許多雜質都已經過濾,剩下來就是純粹。
詩集裡令人喜愛的一首詩是〈夜空海〉,描述著兩地相隔的情人:
在一個平凡無奇、非朔非望的日子
分隔兩地的我們,不約而同
發現夜
其實就是一座海洋
詩人的心就是童心,只有在那世界裡,完全不受成人的污染;也只有在情愛裡,也完全不受庸俗價值的遮蔽。這是最典型的把時間化為空間,黑夜屬於時間,海洋屬於空間,這種轉化使扁平的想像,立刻翻轉成為立體。詩的想像從來不是空洞的,詩人的思考所到達之地,都是可以觸及的。如果永遠停留在抽象的思考,這首詩就欠缺容許讀者介入的空間。童話式的思考,正是詩人風格最動人之處。沒有這樣的聯想,沒有這樣的跳躍,整首詩就歸於平淡。
許多奧妙的想像,往往使讀者感到意外。他的另外一首詩〈聯想海〉,處處充滿了辯證思考,既矛盾又和諧。開始的前四行:
你在乎的是鹽之鹹與糖之甜
我則在乎鹽之白和糖之白有何區別
然後你提到霧之白
其實我在乎的是霧之溼濃撲面
鹽與糖是屬於味覺,但是「我」在乎的是視覺,味覺比較容易分別出來,而白色卻容易產生錯覺。這是一種辯證式的表達方式,使得單純的議題變得特別繁複。這首詩又提到你看見霧之白,而我在乎的是霧之溼濃。這是一首正反思考的思辨,產生了相生相剋的無窮聯想。面對的海洋,詩人反而聯想到鹽與糖、雨與霧,海洋是無窮無盡的空間,也是無窮無盡的想像。「Be water」是一種流動式的思維方式,也是一種流動式的群眾運動。它沒有形狀,也無所不在,可以轉化成不同的空間形式而呈現出來。詩人在寫這首詩時,以〈聯想海〉作為題目,又使他看到的世界充滿各種變化。
你說瞬間會想到雨後的彩虹
繽紛透明,為萬物填色又不奪其形
可我想看的是虹之長
盡頭,在哪兒呢?
詩人再次把空間的議題延伸出去,那種聯想力變幻莫測。從糖與鹽之白,轉化成彩虹的多彩。這是相當引人入勝的一首詩,如果繼續演化下去,也許可以完成一首長詩。詩人適可而止,終於結束於最後六行:
我陷默不語
只左手拈鹽,右手捉糖
扭萬花筒似地看
啊啊,
終於分出
二白的距離
顏色不能輕易分辨,但是味覺卻相當清晰可辨。這位年輕詩人的終極關懷,就是愛的追求。所有的愛,從來都無法定義。恰恰就是無法定義,才能夠彰顯詩人的思考是無窮無盡。這位詩人的誕生,夾帶著太多的神話與童話,容許讀者在他的作品裡,產生連綿不斷的想像。神話充滿了祕密,童話充滿了純真,在說與不說之間,詩的重量便呈現出來。
與這位年輕詩人的初識,是一種幸運。他所創造出來的全新語言,已經塑造出一個前所未見的世界。他有他自己的腔調,也有他自己的語法。他的文字所到之處,都開啟了一個陌生而新鮮的世界。他的潛力還未全然釋放出來,他就是一座山,也是一座海。現在他已經伸手邀請我們探索他的世界,無論是神話或童話,都可以讓我們全心接受。
陳芳明
政大臺文所2020.3.12
超現實的山海間翱翔
身為一個記得學生作品比學生名字還要清楚的老師,當馥蕓寄信過來託我幫她創作插畫的詩集《山海詩》寫序時,我得承認一時間真的想不起她是誰,畢竟每年插畫課班上都有四十多個學生,而我們每週只有短短三小時相處。然而,當聽她在我面前細細地介紹這本作品,腦中的印象也慢慢清晰起來,原來是那個安靜的女生啊!只不過與當年的課堂不同,現在換她努力地說,而我仔細地聽,一樣的是我依然問了很多問題。
不管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從事插畫這工作都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每隔幾年,就會有一些同業離開這個市場,畢竟長江後浪推前浪,不進步的創作者很容易就被市場所淘汰。而插畫在臺灣又尤其困難,除了市場大小之外,臺灣的大學並沒有完整而系統的插畫教育。學校裡我也只能在一年的有限時間中,努力地將我所學濃縮後教給學生,並希望他們能以此為基礎繼續努力,自己茁壯成長。重要的是,創作一直是一條漫長的路,或許的確有些人極具天賦,但能走到最後的往往都是那些努力不懈的人。
因此,當我聽到馥蕓說到她花了五年時光慢慢地完成這本書的插畫,有種學生長大的感覺。對任何創作者而言,完成任何一件作品都不是容易的事,更遑論這本詩集的插畫逾百幅了。
在馥蕓的插畫作品中,能夠看到受到學校薰陶的筆觸,卻又不被所學侷限,這也是身為老師特別欣慰的事。如卷首的〈神話 〉就展現出超現實主義的異想天開,也為整本插圖的風格定調;也有如〈日誌海〉以解構方式呈現的作品;而在〈垃圾山〉、〈荒謬山〉 等作品也看得出馥蕓想用魔幻寫實之筆寄託欲諷喻的事物;在卷末的〈觀〉及整個系列以西方裝飾性筆法結合東方山水畫的圖騰,呈現出中西合璧的創意。
雖說我並不覺得在馥蕓漫漫五年的創作過程中,我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可當她願意回來告訴我出版的喜訊,甚至邀我寫序,我仍然十分高興而感動。我只是將她領進門,而這些成果都是她慢慢努力的收穫,我相信她在完成這些創作的過程一定也獲得了諸多成長。我也期待馥蕓在未來能有更多的創作。
《山海詩》這本書,說是現代詩,又像一個個小故事,一個個關於現實卻又奇幻的篇章,搭配馥蕓的插畫,是一本特別而有趣的書,希望大家都能在這片超現實的山和海之間翱翔。
林士棻
推薦序
抒情的神話與童話
洪逸辰獲得詩人流浪計畫,是在二○一八年十一月。他當時提出的寫詩計劃,是要去日本大阪中低收入戶生活區。那時我擔任評審,閱讀他的計劃與詩作,非常訝異如此年輕的詩創作者,擁有一份不尋常的人文關懷。在那之前,他的名字於我非常陌生。他提出計劃時,也附帶幾篇詩作,夾帶著豐富想像力,那時就強烈感覺這位詩人具有敏銳的心。在臺北齊東詩舍頒獎時,我才第一次與他認識。他的神情有些內向,表達語言時也有些羞澀,似乎與他計劃中所顯現的果決,頗有一些距離。獲獎後,他依照計劃前往大阪,停留期間...
目錄
楔子
卷首
神話
北海
積水海 瓢蟲海 文字海 蝸牛海 美之海 寶石海
牛奶海 鞋子海 雷之海 純粹海 火燄海 漂沙海
北山
燈火山 鯨魚山 垃圾山 糖果山 蝴蝶山 水晶山 冰霧山
東海
愛之海 日出海 日誌海 模糊海 等待海 魚缸海
顱中海 毛毛海 夜空海 思想海 誓言海 瘋狂海
東山
肋骨山 星星山 遙遠山 那座山 雲朵山 日界山 龍血山
南海
葉子海 眼淚海 腥紅海 時鐘海 荷葉海 聯想海
光闇海 情緒海 刺刺海 晶花海 刀礫海 月生海
南山
女夷山 繭蛹山 荒謬山 土狗山 萬象山 頭髮山 疏影山
西海
熱鬧海 紙漿海 成長海 鐵球海 釦子海 緊張海
舌苔海 玻璃海 信息海 碎片海 汽水海 數字海
西山
白玉山 樂園山 昏睡山 人造山 小說山 玩具山 太陽山
大荒
大大海
中山
貝殼山 存在山 山中山 密語山
中海
生命海 洞穴海 風之海 小小海 靈魂海 流星海 地心海
卷末
觀
楔子
卷首
神話
北海
積水海 瓢蟲海 文字海 蝸牛海 美之海 寶石海
牛奶海 鞋子海 雷之海 純粹海 火燄海 漂沙海
北山
燈火山 鯨魚山 垃圾山 糖果山 蝴蝶山 水晶山 冰霧山
東海
愛之海 日出海 日誌海 模糊海 等待海 魚缸海
顱中海 毛毛海 夜空海 思想海 誓言海 瘋狂海
東山
肋骨山 星星山 遙遠山 那座山 雲朵山 日界山 龍血山
南海
葉子海 眼淚海 腥紅海 時鐘海 荷葉海 聯想海
光闇海 情緒海 刺刺海 晶花海 刀礫海 月生海
南山
女夷山 繭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