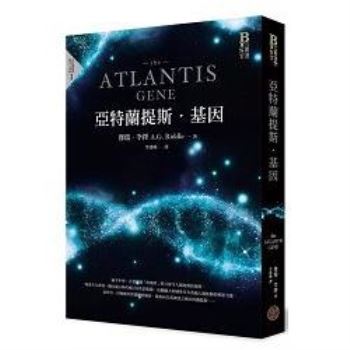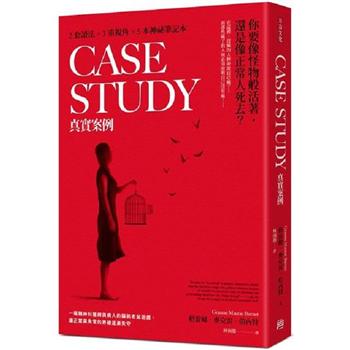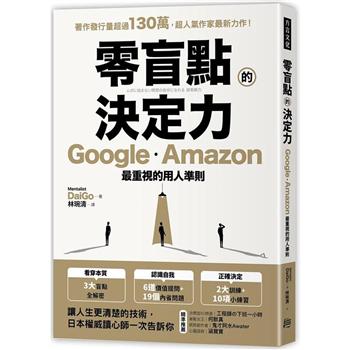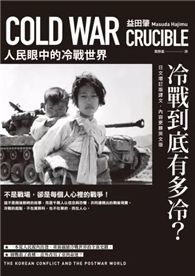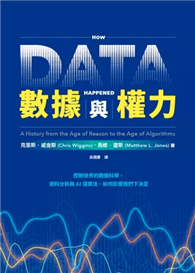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序章〉
豐川,一個不起眼又異常溫順的小鎮。
古早時代,它曾是有著豐富農產資源、像河流一般滋養周邊城市的文化中心。九二一大地震後,小鎮的發展凝結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豐川終究沒落,淪為一個市的邊緣區域。它的小,是一個謠言只需十分鐘就能遍佈全鎮的那種。小到早上剛和愛人分手,晚上就能見到他牽著新人出現。
人們總說,在豐川度過的青春,是停格的時光膠囊。時間在這麼小的城鎮空間裡被壓縮了,情感也是。唯一不變的,是正午的太陽未曾受到暖化的影響,數十年來,陽光的溫度總是烈得綿密,伴隨著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雨後破土的味道,一切生機被埋藏在登山步道的小山丘上,不再發芽。
* * *
客運站裡人來人往,上方掛著大圓形SEIKO時鐘,儘管鐘面跟站邊雜貨店的玻璃櫃一樣佈滿著灰,黑色大小指針仍堅持指著數字三的方向。
「我不想要誰給我快樂,因為快樂總帶給我不快樂。」單聲道的廣播正播送著新生代歌手孫燕姿的歌,一對少男少女站在離群眾稍遠的牆邊,兩人的氣氛明顯不在一個世界。男孩神情沮喪抓著背上的肩包,寶礦力一直掛在女孩的手上,她眼神在乘客與男孩之間飄蕩。
「三點半到臺南的。」提著大包小包的乘客湧向報站聲音的方向,形成綿長的隊伍。女孩換了個姿勢還在等男孩緩過來,直到旅客一個個遞進上了車,在大廳裡排列著的候位椅又現出了剝落的天藍色油漆,他們仍沒動身。
女孩正盯著新來的旅客重新填滿了候位區的陷落。過不了多久,她發現身邊的男孩不見了,男孩身影夾雜在不斷走進室內的人群中,快速出了站外。
女孩馬上反應過來,快步追上去。室外的陽光格外刺眼,視線籠罩著的白光漸漸淡去,她看到男孩蹲在不遠處,車水馬龍的大路似河流,而他是猶豫過久的跳河者。
「楊俊豪!」少年的臉埋在膝蓋裡,後背包朝地掛在身上,完全忽略了女孩的喊叫。
「是因為他嗎。」女孩語氣有些氣憤,堵在俊豪和車流之間的岸線。俊豪並沒有答話,輕輕把手放在女孩的布鞋上,她因為他的脆弱而慢慢把拳頭鬆了下來,手心撫上俊豪頭頂。
「對不起……」俊豪終於開口,女孩心軟,蹲下來緩緩將手環上他弓著的背。她安撫著少年說道,「放心,沒有人會知道的。」俊豪雙手跟著攀上女孩的肩頭,像找到上岸的繩索,他親吻了女孩的脖子,又再次說了聲對不起。
站內,廣播主持人換了首歌,說是送給所有的千禧年寵兒。伴隨著客運駛離的聲音,小指針已經在數字八了。
二十一世紀之初,平凡的早晨,警局的紅磚牆面微微閃著榮光,一樓走廊上穿著制服的男人們來來去去,但他們看起來並不像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那樣挺拔,更多的是帶著一種暗物質的氣場,他們可能在走廊上衝著你打招呼,進入偵訊室之後,犯人不順從就會在別人手背烙上菸疤。
穿梭在眾多黑色西裝褲之間,有個矮小的米黃色裙襬,她走路的節奏像是黑夜裡進了宰場的羔羊,幽微地感到生命受威脅,卻不知敵人來自何方。只有父親的大手領著她在沉浮的海中前行,每每有人注意到她,總像受驚嚇般抓緊父親的手心。父親一路上和走廊經過的不少人打了招呼,他們叫他順仔、阿順、小順,話題無不是打聽彼此的家庭近況與科室八卦,請他有閒來自己處室泡茶。在走到鋪著紅色塑膠硬皮的大樓梯口前,順子停下腳步,女兒杵在他與一個男人的褲管之間。
這一個和順子寒暄的男人長相很模糊,不是因為看不清,而是父母生給他一副沒有出差錯、不令人討厭的臉。就算是大眾定義上的醜,至少也有醜的特色。至於他,頂多只能稱作五官端正,無任何記憶點,第一印象亦說不出性格是溫順或是暴烈的,可以輕易地喜歡上又忘卻的一張臉。
不過順子認得他。
「阿發,怎麼樣還習慣嗎,比在南部忙吧。」
「還在熟悉業務,忙是應該的。這你女兒嗎?」
阿發警官輕拍了小女孩的後腦勺,像是不習慣跟孩童打交道,疲乏的笑臉略顯現出溫度。
「對啊,她媽晚點來接她。叫叔叔。」
「叔叔好。」
女孩只是盯著阿發看,沒有特別的表情。順子像是想起什麼,刻意找話題的那種。
「你老婆懷孕多久了,還在學校教書啊。」
「預產期還要半年,之後打算讓她課排少一點。」
「要好好休息,當初生小萍差點小產,還不都是因為我老婆不肯停工。」
小女孩聽到自己的名字懵懂地看著父親。順子像一支球棒找到了發球機的定點,高頻率的談天中夾雜對妻子的細碎埋怨,阿發微笑應和著,一邊提起手中的文件夾。
「嗯我會好好跟她說……學長我們再聊,我先去勤務中心。」
「好好,有空來交通隊泡茶。」
兩人點頭允諾。小萍盯著阿發遠去的背影,不自覺抓緊了父親手心。順子以為女兒想被抱,便一把抱到肩頭,邊碎唸女兒變重了邊緩慢走上樓,小女孩環抱著父親的頸子又轉過來看向阿發。
她的眼神中有種成年人察覺不到的不安與篤定,像是早早知道了對方的真實身分。
* * *
「爸!」小萍的一聲呼喚,把順子從十八年前的記憶裡拉回來。他手裡抱著更久之前的警校畢業紀念冊,躺在沙發椅上睡著。翻到的那一頁是同學出遊的大合照,青春洋溢的氣息蓋過了所有人的面目,以至於無法仔細分辨誰是誰,像一群開心的雄麻雀。
「我要出門了,要睡去樓上睡啦。」面對女兒的叮嚀,順子盡是中年男人的狼狽,略大的肚子讓他遲緩起身,把紀念冊挪到前面的茶几上。小萍在一面鏡子掛鐘前猶豫上衣要紮進去還是露出來,邊注意鏡子反射出父親默默的身影。她回頭走近順子,把紀念冊轉向自己,邊整理頭髮。
「裡面哪個是你?」小萍隨口一問,順子便指了大合照裡站後排左邊的那個,小萍敷衍地點兩下年輕順子的頭髮,邊論道,「髮型好俗……你要載我去火車站還是我搭公車去?」
「你媽不是說要過來載你去。」
「她還沒跟朋友吃完飯,叫我自己去。」
「又在跟朋友吃飯……到底還顧不顧自己女兒了。浩浩呢?」
「他在樓上啊。」
小萍仍在忙著打理造型,順子唸完自顧自往樓上走,在樓下依然聽得見他走進房間的聲音。順子的金屬皮帶扣套上西裝褲的聲音喀喀響,他沿著偏暗的小走廊走到一個採光度極佳的房間,少年浩浩背對著他屈膝而坐,帶著耳機敲擊腿上放著的iPad,「要不要跟我送你姊去車站。」順子說完發現兒子沒有聽到,走近挑他的頭髮。
「頭髮要剪,太長了。」順子話沒說完,浩浩就搖搖頭驅逐父親的手,表示沒有意願。
「我跟同學約兩點在中友,再不走會遲到!」小萍衝著樓上喊,擺明打算讓父親載。順子顧不及倔強的兒子,只好丟下玩iPad對眼睛不好的話。浩浩繼續埋頭抽他的虛擬卡牌,順子匆忙拿了錢包和鑰匙便快步下樓。
「我載你去,順便去剪頭髮。」等待父親把車開到門口的時間,小萍僥倖地懶坐在沙發上,拿起紀念冊胡亂翻著,以父親年輕的容貌在給他同期弟兄們的顏值評分,她又翻回剛剛大合照的那頁,仔細檢驗大家的時尚品味,跟著,瞇起眼看著其中一個男人。
這人蹲在父親前面,順子的雙手靠在他肩上,同樣是露齒笑,小萍卻覺得有種寒顫的熟悉感。
是張能輕易喜歡上也能迅速遺忘的臉龐。
〈第一章〉(節選)
「你是不舉嗎!出列!」儀隊老師又開始挑楊俊豪的毛病。選擇儀隊作為社團,與俊豪白淨孱弱的長相太不相襯,但這是他人生中少數有決心要參與的事,與鍛鍊心志有關。每次他因為動作不準確而被老師留在操場舉槍時,世界回歸寂靜,他感到安全,並且悄悄驕傲著內心滋生的強大。
七月的中臺灣不若北部時常下雨降溫,也不如南部有海風吹撫。烈日不費力就能侵蝕青少年嬌嫩的肌膚,但俊豪無懼於此,只有在日光最惡之時,能將體內最深沉的罪隨著汗水排出,而後,是多巴胺帶來的快樂。若要他指出背負的罪,他也說不明白。可能是他的出身、長相、老師和同學的評價,這些是不知哪時就悄悄爬上身的十字架,等他感覺到重量時早已取不下來。只不過他身下還有人要保護,從他有記憶以來手裡就拿著剪子的母親,一個人在警局附屬理髮廳裡忙進忙出,他除了不給她惹麻煩也沒有什麼可做的,母親總是拒絕獨子的幫助,她一人就能撐起整片宇宙。
相對於那股自卑感延伸出自我保護和叛逆的同齡人,楊俊豪的青春期情緒顯得過於穩定,並非是成熟,而是被動的、巨大石塊壓著的平靜。這種安靜在青少年之間是不被許可的,躁動才是所謂的「正常」,因此他成為許多人下意識發洩的對象。
「李憶潔愛楊俊豪!楊俊豪愛李憶潔!」
不知道是誰在黑板上值日生那欄畫上一支雨傘,底下是風紀股長李憶潔和楊俊豪的名字,其實俊豪才是今天的值日生。上課鐘響,俊豪只是默默地上去擦黑板,順帶把雨傘跟李憶潔擦掉,絲毫不費力的樣子。李憶潔從辦公室回來吃午飯的時候,才聽隔壁的女同學說這件事,她尷尬地笑了笑,並瞄了俊豪的側臉,那不是愛慕的眼神,而是心疼。
俊豪的異性緣比班上男同學好很多,可能是他對異性同性一視同仁的態度,讓女生感覺更容易親近他。他也交朋友,並不刻意孤立自己或顯擺非主流的邊緣與特異,但他並無認定自己跟誰是最好或隸屬於哪個小團體這種概念。
他負責的打掃區域在孔子銅像附近,那是一個半公共空間,展演廳的騎樓過了正午,樹蔭遮蓋著的角落,是他第一次接收到異性愛意的場域。那個女孩是七班的,點點他的肩,把一封摺成玫瑰形狀的信給他。木訥的俊豪也不會想到對方是羞澀,反而是對自己給人陰沉的印象感到抱歉,導致對方不敢和他說話。
「十五票!沒有異議的話,楊俊豪當選風紀股長。」李憶潔上週辦好了轉學手續,曾經會在楊俊豪被某些調皮的男生惡整的時候,站起來替他說話的她終究也離開了,所以大家異口同聲要俊豪接下「前女友」的擔子。
七班女生的情書被他忘在體育褲的口袋,直到這週的社團課才被同學抄出來,原本是一陣打鬧,肉體的擠壓碰撞,在其中一個男生把俊豪推到更衣室門前戲謔地輕啄臉頰之後,變調。
他褲襠裡揚起的欲望,抹去最後的一點自尊心。
大家繼續調侃他想上李憶潔又只敢打手槍的慣性勃起,好似男性欲望的填空題中女性代表了一切對應的答案。俊豪躲到廁所裡,並加以應和大家對做愛的想像。對!她走了之後,我多麼想念她的小乳!細緻的肌膚!甚至自己也不知怎麼稱呼的私密部位!如此可笑的我和我的器官!
他以為自己夠強大去抵抗流言蜚語,但對於不造成麻煩的執著,除了自己再無他人可信任的倔強,已種下這整個暑假所有喜怒哀樂的因果。
楊俊豪在警局的醫務室醒來,微弱的白燈透過老式霧面燈罩發散著,使他有種靈魂出竅的錯覺。轉過頭去是醫務室的阿姨在用小電視看命理節目,他慢慢地支撐起自己的上半身,鐵架組成的病床嘎吱發出聲音。
「醒了喔?」阿姨瞄了俊豪一眼,但眼睛離不開電視,主持人正在分析生肖屬豬的流年運勢。「你媽有客人,剛幫你換完衣服就回去了。」俊豪摸摸身上乾淨的T恤,阿姨拿起一旁的餅乾口糧吃起來。「我媽送我來的?」俊豪覺得頭好脹,聽自己說話腦袋裡都有嗡嗡的聲音。「你媽哪那麼大力氣!」俊豪才看到枕頭邊的櫃子上擺了一罐冰過的舒跑。
看到阿姨全神灌注在預知自己命運的同時,俊豪又躺回床上。他努力回想早先發生的事,畫面像碎片一樣湧來,卻拼湊不出任何一條可靠的線索。只感覺中午的陽光炙熱到操場可以煎蛋,但肉體的記憶還是慣常地直立不動。接著腿一軟,恍惚的視線中是他跌跌撞撞去投幣、搭公車、按公車鈴、有人向他招手、風吹過龍眼樹的味道與聲音,穿過警局主大樓走廊的時候,視線開始變暗,每個人的臉像罩了一層面紗,俊豪嘴裡已經有點止不住的酸味,在樓梯轉角撞上了一個比他大一號的柱子,跌坐下來。
不,那應該是一個人,他身上有種肥皂水的味道,可能是他慣用的洗衣粉,俊豪看到他胸前的兩顆星跟一條線。現在他就在這個警官的懷裡,但他意識不到這一點,從胃到食道的通道滿溢著不知何物,隨時都要奪口而出。斷裂的聽力裡也有嗡嗡聲,是對面這個男人在呼喚他的聲音。俊豪的臉被捧起輕輕搖晃,他突然覺得自己可以安穩睡去,就在這個警官所產生的氛圍宇宙裡。
俊豪猛然從病床上坐起來,阿姨被驚動了。他摀著自己的耳朵,那個嗡嗡聲還在,不過他接壤著耳朵跟頸子的皮膚都紅得發燙。
「喂!」剛午休結束的時間,楊俊豪就被後面的不良少年小黑用國文課本打醒。俊豪不耐地撫平頭髮,並轉過去瞪小黑。
「借我一百。」小黑眼神確認沒人在盯著他們並偷偷地說著,像是全人類都在覬覦俊豪的一百塊。
「沒錢。」俊豪無趣地答道,回到座位趴著。
「拜託,下午考數學幫你寫。」小黑抓著俊豪的肩膀搖動。
「你數學有比我好嗎。」俊豪又冷冷地說了句。
兩人一來一往,等到上課鐘響小黑才打消了念頭。
班長要大家把校外教學的家長同意書跟費用交上來,俊豪從抽屜裡打開自己空白的同意書,上面標著,「費用一千五百元整」。
他看看左鄰右舍,大家都泰然自若地拿出錢跟同意書往講臺走去,一邊討論著去七星潭之前要相約去買零食,順便帶上撲克牌玩心臟病。小黑跟後排的同學借到了一百,手上拿了一疊現鈔挑釁地往俊豪臉上揮。俊豪反手一拍,紅色的一百元散落一地。
「幹林老師咧……」小黑碎罵了一句,把地上的錢撿起來,往班長走去。
「班長,楊俊豪他家太窮沒錢去。」小黑不帶好意地大聲說著,邊把自己的錢交上去。
班長看了看俊豪的方向說,「不去也要交同意書喔。」
不少同學都轉過來看俊豪,旁邊的女生小聲問正在冒冷汗的俊豪,「你不去喔?」
俊豪把雙手藏在抽屜深處,像在撈東西邊說,「不要聽他胡說八道。」起身就往講臺上交同意書,上面已經簽字同意。
班長拿起來看,在登記表上打勾又說,「錢最晚週五給我喔,廠商要來收。」
小黑站在講臺前斜眼看著,俊豪理都沒理便回到座位。
回家的路上,俊豪經過一扇破牆,碎裂的磚頭石塊堆在本是房屋的空間中,牆上用噴漆寫著「臨時工04-5296357」,他盯著看了一會兒便離開。
到達警局大門的時候,有一輛黑頭車正駛出,俊豪抓著書包在一旁等候,車窗捲了下來,待守衛敬禮後才走。
「放學了啊。」守衛先認出他來招手,俊豪只是點頭快速進入警局。
走近窄小的理髮廳時,母親秀琴正在替警官啟源理頭,他是警局裡的好好先生。秀琴穿著大地色的碎花連身裙,頭上夾著個青色鯊魚夾。整個髮廊只擺了三張鏡子跟椅子,毛玻璃將光線變得柔和,窗花的影子倒映在磨石子地板與擺放剪子、毛巾的三層小推車上。
「媽。」俊豪直接往髮廊後面垂著珠簾的小房間走,母親來不及看俊豪一眼,視線又回到警官的頭頂,手上喀喀喀地剪著。
「你兒子都這麼大了啊?秀琴你很有福氣喔。」啟源看著鏡子裡的秀琴問道,秀琴點頭笑笑。
「我女兒剛上國中,資優班的,花費真的很傷。買課本、學才藝、同學流行電子雞還要跟著買。哪像我們小時候,能去挖番薯、抓田雞就不錯了。」啟源說著有點油膩起來,講得自己不知道是褒是貶。
俊豪沒有開燈便把書包丟到床上,從旁邊櫃子底層拿出一個鐵盒,裡面有張紙條寫著「英文講義500」,盒內零錢哐哐響,但連紙鈔都沒有,俊豪數了一會兒塞了幾個零錢到口袋,便把鐵盒放回原位。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正午的圖書 |
| |
正午 出版日期:2021-03-17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小說 |
$ 264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70 |
現代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推理/驚悚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正午
那天,烈日當空,刑警阿發在槍械室舉槍自盡。
同時,少年俊豪逃家失蹤,從此渺無音訊。
千禧年對整座島的年輕人來說,都代表著希望。歷經大地震後的中部小鎮,本該回歸溫暖平靜,人們心中卻潛藏著斷層之下,蠢蠢欲動的暗流。一樁舞弊案令縣警局上下惶惶不安,為了利益而自保的小螻蟻,下意識地開始尋覓可能的犧牲對象。
大太陽下過度操練的虛空感,是拯救俊豪高中生涯的聖光。被栽贓偷竊班費的他,想到單親母親的無助與導師兇惡的態度,便對世界感到絕望,僅有新來的轉學生筱雯,嘗試著接近與理解他。
來自農村、被原生家庭遺棄的阿發,以為考上警察就是他翻身的機會。新婚後他憑藉岳父人脈升調當刑警隊小隊長。妻子美惠懷胎數月,無力說服父母對丈夫放下懷疑;阿發承受著妻子娘家嘲諷與人事壓力,努力表現出好警察、好丈夫、好男人的形象,但他內心卻深深感到孤立無援。
如此脆弱的兩條生命線因不可告人的貪瀆舞弊而相遇,受難以自禁的同性情欲所牽引──直到那個熱天午後的一聲槍響,嘎然而止。
時隔多年,老警官順子在舊時警局理髮阿姨家中剪頭,聊起那位選擇自絕的年輕同僚,意外攪亂了人生的記憶之湖。羞恥感是人類的起源,未解的親子關係與社會標籤,揭露了人性的殘暴與溫柔。
以中部小鎮懸案展開的封閉人性宇宙,社會寫實與同志異色纏繞融合。在道德束縛之下的人生充滿無常,因果祈來的愛戀,但求無悔……
作者簡介:
小惑星
臺中人,電影導演與製片出身,流浪歐亞大陸多年。曾獲文化部短片輔導金與文策院動漫劇本獎,不在寫劇本的路上,就在寫小說。作品兼具視覺化潛力與異色趣味,目前以「光庵」為故事IP開發品牌活躍中。
章節試閱
〈序章〉
豐川,一個不起眼又異常溫順的小鎮。
古早時代,它曾是有著豐富農產資源、像河流一般滋養周邊城市的文化中心。九二一大地震後,小鎮的發展凝結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豐川終究沒落,淪為一個市的邊緣區域。它的小,是一個謠言只需十分鐘就能遍佈全鎮的那種。小到早上剛和愛人分手,晚上就能見到他牽著新人出現。
人們總說,在豐川度過的青春,是停格的時光膠囊。時間在這麼小的城鎮空間裡被壓縮了,情感也是。唯一不變的,是正午的太陽未曾受到暖化的影響,數十年來,陽光的溫度總是烈得綿密,伴隨著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雨後破土...
豐川,一個不起眼又異常溫順的小鎮。
古早時代,它曾是有著豐富農產資源、像河流一般滋養周邊城市的文化中心。九二一大地震後,小鎮的發展凝結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豐川終究沒落,淪為一個市的邊緣區域。它的小,是一個謠言只需十分鐘就能遍佈全鎮的那種。小到早上剛和愛人分手,晚上就能見到他牽著新人出現。
人們總說,在豐川度過的青春,是停格的時光膠囊。時間在這麼小的城鎮空間裡被壓縮了,情感也是。唯一不變的,是正午的太陽未曾受到暖化的影響,數十年來,陽光的溫度總是烈得綿密,伴隨著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雨後破土...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正午》的城鎮原型來自我從小生活的家鄉,成年之前的時光都在那裡度過。小學經歷九二一地震後,小鎮位處縣轄中心的優勢似乎也隨著天災消失,縣市合併導致我父母的工作起了變化,當然,我的家庭也在城鎮歷史中發生巨變。
二○○○年的設定,對來自九二一重災區的我有著重大意義,當時跨越千禧年與政黨輪替帶來的生機,是無限的,就像阿發給俊豪的期待一樣。但就我個人的歷史而言,迎接新時代帶來的是停止成長的城鎮發展,我不得不去思考關於城鄉、關於世代、關於變化與停滯的相互輝映。
看似與個人無關的大時代與居住空間變化,其實對個...
二○○○年的設定,對來自九二一重災區的我有著重大意義,當時跨越千禧年與政黨輪替帶來的生機,是無限的,就像阿發給俊豪的期待一樣。但就我個人的歷史而言,迎接新時代帶來的是停止成長的城鎮發展,我不得不去思考關於城鄉、關於世代、關於變化與停滯的相互輝映。
看似與個人無關的大時代與居住空間變化,其實對個...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序 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終 章
序 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終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