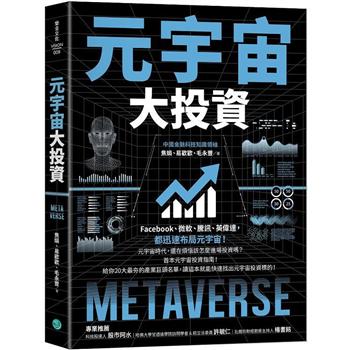一、天馬行空 Across Imagination
老船長要死了。
船員之間的竊竊私語迴響在艙內和甲板上;他們彼此以眼神交流著,心領神會這傳言。
老船長要死了。
別忘記他們是時沽號(The Timesworth)的船員。她是王國內最優秀的商船;她的船長是王國的傳奇、船員則是最傑出的男女。流言萬萬不可拖慢他們手頭上的工作。船索緊繫、桅帆股風,地板穩定的上下搖晃使人相信船仍在移動。時沽號船身長達百呎,表面以令人稱羨的結實木料覆蓋,歷久不衰;船型既屬漂亮的長寬比例,也具流線型的身軀。這艘船除了後端的航行室之外,甲板下還有兩層艙房以及一層貨櫃。三組船桅的帆布皆以進口斜織白布製成,三角狀的帆揚起時簡直能稱作是藝術。
從遠處看來,時沽號幾乎是黑色流線底座上頭點綴白色的叢瓣,插花似的美極了。多諷刺啊,現下船員們心裡所想的只有這白色船帆如何象徵著純潔的靈魂,更象徵死亡。六個人合力將鏡環(Effigon)扛出甲板,架設在掌舵處旁邊。鏡面廣如浴缸,覆著一片抹不去的濛灰,活像個放大數倍的更衣鏡。甲板上一處空缺始終如芒刺在背,每過幾秒就有人不安地轉頭查看那位置上的人有沒有回到崗位,因為掌舵者不是大副、因為坐鎮一切且經驗老到的大副正前往老船長的艙室匯報船的狀況―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現下船長重病臥床,大副這稱謂變為船長,也是遲早的事。
遲早死神會提出價碼,而人類將無力議價。
「有、有聲音。」阿閃(Flee)緊張地說。他將拳頭握得更緊,掌心有枚老舊的硬幣。
「只是個鐘。別大驚小怪的。」幣崔絲(Beatrice)走在前面說。
她熟門熟路的來到木門前,敲叩兩聲。
「鐘。」阿閃咀嚼著這個字。走廊牆壁的木板間,不斷傳來儀器運轉的滴答聲,他明白那低沉難辨的聲響是計時的神妙儀器。
幣崔絲開口道:「等會進去,站在原地,一句話也別說。」
阿閃嚥了口水,點頭答應。他從未踏足船艙此區,甚至未曾見過船長的正面。自從登上時沽號以來都是大副在管事,其餘的人只有在特殊場合或是靠岸時才見過老船長。阿閃更別說了,他是地位低下的船員,負責打雜清掃等工作。
―然而沒有人不認識船長,沒有人不認識傳奇般的「拉雷恩‧譚沃」。
阿閃記得家鄉的農場獸欄,曾養過一頭老野獸。
將野獸從森林裡捕回來的父親說那野獸叫「棕熊」,父親曉得養肥之後毛皮、熊肉、甚至內臟都能賣到好價錢,所以一直沒宰掉。父親離開後,母親改稱棕熊為「汙霉頭」,只因怎麼也賣不掉,家裡更沒人懂得如何宰殺。阿閃每天負責把廚餘帶出去獸欄,而很快地,只吃廚餘和泥土苟活下來的的汙霉頭已經又老又病;毛皮失去光澤,獨自住在自己的餿水之中。那段日子裡阿閃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明白心裡的疙瘩代表什麼―他並不是害怕汙霉頭會獸性大發、衝出獸欄然後暴走傷人。他更在意的是老熊身上的器官皮肉,那些符合人類認知「價值連城」的物品。他日日經過獸欄前,倒完廚餘後一溜煙的跑走,就是沒看過老熊展現統御森林的野性。汙霉頭的髒熊毛與髒熊膽真的值很多錢幣嗎?汙霉頭……不,老棕熊最後被買下了,連同阿閃的第一份勞力被賣到鄰近鎮上。這都是好幾年前的事了。
時間還在固執地流逝。
門內有人走近。
一位身穿黑袍且肅容滿面的男人開了門,他的瞳孔和衣服同為墨黑,瞧了幣崔絲和阿閃一眼,隨後准許他們進入。
深棕色的牆壁和嚴謹的擺飾讓這裡比起臥室,更有會議廳的感覺。光線由房間左側的窗戶透進,照亮迷路的灰塵、灑在房間的角落;就連收拾整齊的辦公桌和書櫃都積了層薄灰。牆上的大型機械鐘比人還高,下半部的漆木外表和透視的玻璃讓人看見晃蕩的鐘擺、轉動的齒輪,上半的鐘面是打磨過的白色大理石,黑色指針穩定的跳動,將時間切割為緊密的小段。
阿閃佇立房間一角,目光被櫃子上閃亮的東西吸引―象牙色的盤狀金屬躺在櫃上,形似羅盤、約大過手掌、上頭還畫有刻度;然而那些刻度未標示東南西北,而是幾個毫無意義的圖樣,而且沒有指針。就是它―傳奇船長的傳奇信物。
其他兩人在書櫃旁小聲談論著。
幣崔絲問:「沒有其他療方了?」
「不盡快靠岸補給的話,是的。」黑袍船醫面無表情的回答。
「現在只怕船速快不起來。鏡環故障了。」幣崔絲壓低聲解釋。
醫生瞄了床一眼說:「……有話快說吧。他時間也不多了。」
大副與醫生都將船長看作行將就木的病人。在阿閃想來,床上躺臥的,說不準正是曾稱霸森林原野的棕熊。
素白的簾子將床鋪與其他隔離。拉雷恩‧譚沃(Ralein Timesworth)躺臥在乾淨床單上。堅毅的臉龐被歲月侵蝕。曾經英俊深邃、威武萬分的大氣五官喪失其鋒利和稜角,健康的皮膚在時間的魔爪之下枯萎病白;肩膀不再有壯年男子的寬廣,剩下虧薄的體格和毫無贅肉的瞿瘦身軀。歲月並未手下留情,令老船長的手掌也被皺紋和灰斑覆蓋。阿閃認出王室贈與的榮耀勳章在老船長的胸前;頸上戴著月族的祝福鍊飾、五色的異族椹果擺在床邊盤上,一口也沒動過。
隔著白色帳幕,後頭的模糊人臉顯得略有那傳奇人物的殘貌―縱橫廣海數十載的傳奇人物拉雷恩,以女王之名參戰建功數次、與月皇族過從甚密,此時只給人一種崇高峻嶺削為斷垣殘壁的錯覺。阿閃在創造歷史的偉人的病榻旁呆站,甚至不清楚自己為何會身在船長的臥室。
窗櫺的灰影被天光投射到船艙內,那一格格的光亮籠罩榻上的人,為其增添微不足道的生命力。它吸引著阿閃的目光,讓他不禁靠近床頭往玻璃另一頭觀察著。
「找到她。一定要找到她。」
低穩的嗓音說道,有如古鎮的銅鐘。聲音雖乾涸,卻有種不容質疑的凝斂力道。阿閃在驚嚇之餘不自覺挺直了背。
幣崔絲也聽見了。她二話不說推開阿閃,說:「大副在此,船長。」
「嗯……。」老人吃力地移動脖子:「告訴我,大副,今天的風如何?」
幣崔絲皺了皺眉,兩手背在背後答道:「本船乘風勢穩定的前進,船長。預計三天後抵達王城港口。」
老船長一呼一吸,深沉地像是在回憶王城的廣大、皇宮的輝煌。
「時沽號的貨物,不得遲。」老船長隔著簾幕說。
「……遵命。」幣崔絲回道。
三個站立的人中,只有大副心知肚明一件事:貨艙裡根本空無一物。或者該說,貨物本就是年邁重病的船長。幣崔絲只覺得船長睡糊塗忘了,但豈敢戳破。
「船長。」大副她正色道:「巫師回報,鏡環的魔法失調難以修復。若是缺乏對岸聯繫,本船……」
「有話直說,大副。」船長小聲打斷:「老夫時間已無多。」
幣崔絲面露難色:「……若是無法盡早靠岸,則本船無法提供您……適當的治療。」
拉雷恩‧譚沃的表情被簾幕遮擋住。
他說:「貨物要緊。為何不走西方的捷道?」
大副眉頭深鎖,回道:「船長,鏡環損壞前王城的巫師曾寄來最後消息:西方沿海區有動盪,靠近乃不智之舉。」
阿閃看著滿不耐煩的大副,不禁回想起家鄉的母親;那女人一邊要照顧農場、管教小孩,還須一邊訓斥老頑童般成天瘋言瘋語的公公……還有獸欄裡蟄伏的棕熊。怪不得母親和幣崔絲一樣,竟日皺著眉頭。
「動盪?」老船長不解地問。
「是的。」幣崔絲用著最後一點耐心說:「混血月族的叛亂軍盤據西方航線。我已經在上一次報告中向您提起過了,船長。」她眼神冰冷地說出最後一句話。
老船長無視著對方的情緒:「西方沒路走了。這麼說,我的時沽號正在碎磷森林(Phosphorest)間航行。」
「對。」幣崔絲冷道。她斷然轉身,朝門口走去,再也無法忍受癡呆老人的無謂提問。她承認來到船長室探望根本就是徒勞,因為老人連周遭發生的事都搞不清楚了。與其在這浪費時間,還不如去督促巫師盡快修復鏡環。
黑袍的船醫眼看兩人一言不合,趕緊向船長勸道:「船長您別著急。有大副領航,本船想必會在時限內抵達的。」
「嗯……碎磷阿……,」老船長在榻上感慨著,又對著走至門口的幣崔絲補上一句:
「磷石的山壁,總是引來善變的風呢。」
無知的阿閃聞言,不自覺的看向床頭窗戶外的景象。
深青色的石柱夾岸。拔地而起的磷石壁透著粼粼青光,在船尾兩側有如莊嚴神木,近的彷彿隨時會擦撞上來。呼嘯的風兒雖透明無色,但任誰都能想像她們沿著礦石崎嶇的表面,無比快速的竄行、無比吵鬧的嬉戲;她們使船艙玻璃喀喀地響,似有妖精在敲打。風絲牽著雲。阿閃不解得看著龐大雲團,在船後不到一里之處不受陽光阻攔的增生橫行。
呼吸間,船醫與幣崔絲兩人面面相覷。
「月火阿!」船醫駭道。
至於經驗豐富的大副,她當然知道那團不詳的雲代表什麼。只怪自己竟忘了航行的基本道理:天象無常。氣壓在此處的巨變使灰雲在不到一哩之外醞釀。只要出航過的人,便一定知道這代表什麼。在磷石柱的森林間航行,光是要閃避擦撞便已困難重重,更何況還要偵查周遭的所有天候情況。身為大副的她犯下如此疏失!若是船長此時正掌權,恐怕她早已人頭落地。
這時,牆壁另一頭傳來嘎然巨響與木材扯裂的聲音,似是船身尾端擦撞到了山壁。
船身猛然搖晃。
「哇啊!」笨拙的阿閃忽覺視線天旋地轉、撲倒在地,手裡的硬幣落地後滾呀滾,與木地板接觸發出獨特的聲響。
「大副。」拉雷恩‧譚沃平臥於床緩緩說道。
幣崔絲回過神抬頭:「是……是!」
「收尾帆、穩固船桅。」
這不是提醒,而是命令。
「……!」幣崔絲牙一咬,旋身往外衝去:
「全船注意!」她甩開門、扯開嗓大喊:「風暴來襲,收尾帆!!」大副一邊喊著一邊跑出船艙。她聲音遠離之際身後衣襬甩動,穩健的腳步也讓騷動蔓延至整艘船,隔著木頭天花板傳來十數位船員們倉皇的腳步聲,人人往各自的崗位奔去。至於阿閃,他徬徨無助的坐在地上。他的腸胃和腦袋皆不斷翻攪著;在他眼中船艙四面牆壁好像正在向內擠壓變形,而後方牆上的鐘、鐘內的針、針下的數字,仍任由時間不停健走。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錯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中文書 |
$ 237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64 |
奇幻小說 |
$ 270 |
華文奇幻/科幻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科幻/奇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錯舷
「我們選擇待在其中一側,持續忽視欲望的你推我擠、持續冷對文明的迎風墜落。」
金車奇幻小說獎優選《彩畫師.孤棋》同世界觀壯闊新作!魔盒的開啟來自人性根本的欲望。戳破魔法城邦的美好幻象,探究和平與文明建立於犧牲弱者的人類劣根──
這是一個「魔法」讓世界變得生氣勃勃、飛船翱翔在天際貿易的時代。
他是白手起家的商船大副。
是心懷憤慨的探險者。
也是個一無所求的自由人。
一只釋放出各種魔法的魔盒消息引來各方覬覦。眼看志在稱王的爵士、高深莫測的月族智者和神祕的殺手各懷鬼胎,志在奪取埃庇斯女神的遺物。滿載寶藏的商雀號老船長瘋癲酗酒,船舵似乎逐漸脫離掌握之中……
大副拉雷恩不願白白送命,又無心苟且偷生,既不想淌魔法的渾水,又執意釐清商雀號寶物的幕後真貌。他什麼都不要,卻無法脫離以捍衛夢想為名爭權奪利的惡客。在殺機四伏的雲海怒濤中,拉雷恩意外發現世界得以運行的灰暗真理,並做出慘烈的決斷,然而故事並未就此結束──
作者簡介:
唱無
臺中人,臺大外文系畢業。著有小說《彩畫師:孤棋》、《錯舷》、《點燈人》、《空門》等。
章節試閱
一、天馬行空 Across Imagination
老船長要死了。
船員之間的竊竊私語迴響在艙內和甲板上;他們彼此以眼神交流著,心領神會這傳言。
老船長要死了。
別忘記他們是時沽號(The Timesworth)的船員。她是王國內最優秀的商船;她的船長是王國的傳奇、船員則是最傑出的男女。流言萬萬不可拖慢他們手頭上的工作。船索緊繫、桅帆股風,地板穩定的上下搖晃使人相信船仍在移動。時沽號船身長達百呎,表面以令人稱羨的結實木料覆蓋,歷久不衰;船型既屬漂亮的長寬比例,也具流線型的身軀。這艘船除了後端的航行室之外,甲板下還有兩層艙房以及...
老船長要死了。
船員之間的竊竊私語迴響在艙內和甲板上;他們彼此以眼神交流著,心領神會這傳言。
老船長要死了。
別忘記他們是時沽號(The Timesworth)的船員。她是王國內最優秀的商船;她的船長是王國的傳奇、船員則是最傑出的男女。流言萬萬不可拖慢他們手頭上的工作。船索緊繫、桅帆股風,地板穩定的上下搖晃使人相信船仍在移動。時沽號船身長達百呎,表面以令人稱羨的結實木料覆蓋,歷久不衰;船型既屬漂亮的長寬比例,也具流線型的身軀。這艘船除了後端的航行室之外,甲板下還有兩層艙房以及...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章
一、天馬行空 Across Imagination
二之一、貴族與面紗 The Rich and the Masked
二之二、薔薇與刺 The Thorned Rose
三、故事與床邊 Story and its Lair
四之一、雲端之境 Gates to the Clouds
四之二、河床結冰時 Riverbed
四之三、必經之路 Pathway
五之一、最古老的故事 Ancient Tale
五之二、羊和鳥 Sock and Buskin
五之三、無人的天空 Manless Sky
六、眾神之禮 Gift unto Them
七、林中歡笑 Bewitching Laughter
八、夜的鞠躬啟奏 She Wrote and sang, and bowed and Danced
九、日的織光編影 He Wove and cut,...
一、天馬行空 Across Imagination
二之一、貴族與面紗 The Rich and the Masked
二之二、薔薇與刺 The Thorned Rose
三、故事與床邊 Story and its Lair
四之一、雲端之境 Gates to the Clouds
四之二、河床結冰時 Riverbed
四之三、必經之路 Pathway
五之一、最古老的故事 Ancient Tale
五之二、羊和鳥 Sock and Buskin
五之三、無人的天空 Manless Sky
六、眾神之禮 Gift unto Them
七、林中歡笑 Bewitching Laughter
八、夜的鞠躬啟奏 She Wrote and sang, and bowed and Danced
九、日的織光編影 He Wove and cut,...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