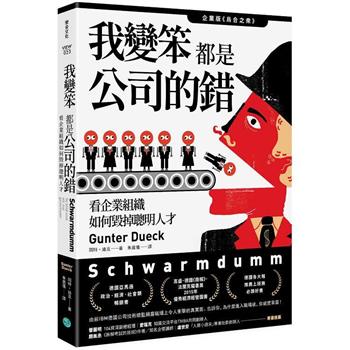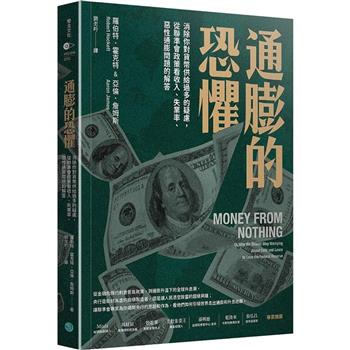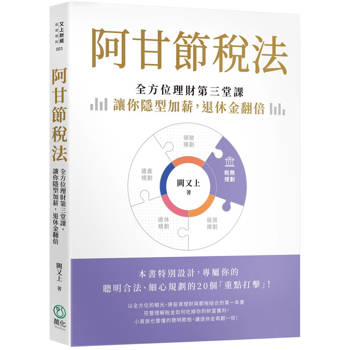一幅日治時代的佚名人物像,如何跨越七十五年的歲月,牽動著兩名女子──大稻埕藝旦月檀、藝文線記者林悅雪的命運?
參訪前田集團舉辦的〈HOPE!戰後日本藝術展〉時,悅雪不經意間瞥見一幅人物畫像,畫的竟是反覆出現在她夢中的旗袍女子!為了尋訪神祕女子身分,悅雪結識了策展人、同時也是集團執行長前田光,兩人輾轉查到一九四三年的大稻埕,日本畫師古谷遼為參加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請來豔冠群芳的藝旦月檀擔任模特兒。
悅雪和光逐步追尋著月檀、古谷遼的人生:江山樓初遇、龍山寺參拜、臺北城漫遊……最後在台南小學校塵封已久的校舍中,找到了另一幅古谷遼的畫作──此時鳳凰花燃燒如野火,月檀是否能逃出藝旦「命比紙薄」的宿命?古谷遼最後的身影為何出現在和歌山無量寺?而逐漸相知相惜的悅雪和光,該如何面對出身背景差異所帶來的現實考驗?這段旅程是否能重新點燃他們追尋自我、實踐夢想的勇氣?
作者考據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史,以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西鄉孤月等日籍畫師經歷為藍本,旁及1940年代臺北大稻埕的藝旦生活、酒樓文化,寫就這部結合史實、奇幻、愛情的時代小說,獻給所有熾烈如鳳凰花的追夢者。
本書特色
★以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史為背景,描寫1940年代臺北大稻埕的藝文生活。
★以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西鄉孤月等日籍畫師作為角色藍本,創造出一部融合藝旦生活、酒樓文化、歷史事件的浪漫時代小說。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下一次鳳凰花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52 |
愛情小說 |
$ 284 |
中文書 |
$ 284 |
Books |
$ 317 |
大眾文學 |
$ 324 |
現代小說 |
$ 324 |
文學作品 |
$ 324 |
武俠/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下一次鳳凰花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瑪西
喜愛世上美好的事物──美食、閱讀和旅遊。曾從事護理工作十餘年,現為自由工作者、部落客。厭倦市面上過度強調正面能量書籍,畢竟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生命的體驗是從中汲取平衡,而非當影子不存在。
部落格:瑪西隨筆
FB:瑪西小姐Ms. Marcy
瑪西
喜愛世上美好的事物──美食、閱讀和旅遊。曾從事護理工作十餘年,現為自由工作者、部落客。厭倦市面上過度強調正面能量書籍,畢竟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生命的體驗是從中汲取平衡,而非當影子不存在。
部落格:瑪西隨筆
FB:瑪西小姐Ms. Marcy
目錄
第一章 楔子
第二章 元辰宮的秘密
第三章 光輝裡的相遇
第四章 收藏者
第五章 蒲公英般的人生
第六章 陽光下的陰影
第七章 幸福的極光
第八章 詛咒之畫
第九章 如是因果
第十章 輪迴的考驗
第十一章 遙寄星空的思念
第十二章 希望的力量
第十三章 終章
後記/敬最絢麗的年代,最亮眼的藝術家們
第二章 元辰宮的秘密
第三章 光輝裡的相遇
第四章 收藏者
第五章 蒲公英般的人生
第六章 陽光下的陰影
第七章 幸福的極光
第八章 詛咒之畫
第九章 如是因果
第十章 輪迴的考驗
第十一章 遙寄星空的思念
第十二章 希望的力量
第十三章 終章
後記/敬最絢麗的年代,最亮眼的藝術家們
序
後記
敬最絢麗的年代,最亮眼的藝術家們
《下一次鳳凰花開》並非向壁虛造的一部小說。
去年十一月偶經和平東路二段,被懸掛於北師美術館外的《不朽的青春》文宣所吸引,進而踏入藝術鑑賞世界。我乃素人,未經專業美術教育培育,亦未接受過任何鑑賞訓練,但初見黃土水《少女》胸像時,卻深深為其美所撼動。《少女》胸像,栩栩如生,大理石透出瑩白的光輝,圓潤的線條刻鑿出平和端詳的神情,將時光凝結在最靜謐一刻,瞬間即是永恆,亦為不朽。這樣隨心的一次藝術鑑賞,讓我重新思考何謂美;細緻、典雅、新穎、大膽、活潑都是不同風格的美,然而真正能感動人心的,卻是畫家的生命力。
我來來回回遊走不同樓層,佇足於畫作、書簡、黑白相片前,就像穿越時空藩籬,一次次返回明治、大正、昭和時期,逐一認識陳澄波、陳植棋、石川欽一郎、陳進、呂鐵州等台日藝術家。進一步探究其生平,更是美得不可思議。在那最顛簸、壓抑的年代,他們試圖在畫布上綻放心靈的自由,在貧困、孤絕、病痛裡燃燒生命,孜孜矻矻地創作。
窮盡心神究竟想要彰顯什麼?陳植棋說:「用赤誠的藝術力量讓台灣人的生活溫暖起來。」那麼藝術已然超越自我表現層次,而是對土地、文化,乃擴展至對人群的愛。
我是這麼由衷感動,但也遺憾,前人遺留的瑰寶,我們幾乎是遺忘了它。我們熱心搶購每張西洋美術展覽預售票,風靡每場海外文物特展,卻疏於珍視自己擁有過獨一無二的藝術家。撇開政治立場,日治年代是不同族群、文化的融合,創作元素更多元,西洋畫、東洋畫、國畫交融出豐沛活潑的藝術品,璀璨如萬花筒。有感於台灣曾經有這麼優秀的藝術家,而我輩卻對台灣美術史了解甚少,遂起心動念欲盡一己之力,去詮釋那遠去的年代,進而點燃《下一次鳳凰花開》的構思。
為圓滿這個夢,除查閱彼時藝旦生長環境外,更反覆觀看公視藝術很有事製作的《追尋不朽的青春》、《探尋未竟的山水》紀錄片。藉由鏡頭,隨著中研院顏娟英教授暨團隊、藝術家後人探尋畫作,喚醒沉寂已久的熱忱,拂去畫框上灰塵,再次對世人展示台灣藝術的光輝。但也讓我不禁反思,藝術如何與商業共生共榮,畢竟沒有商業的支持,收藏家的珍藏,何以將作品留存、修復?
《下一次鳳凰花開》雖以一九四五年日治時代為舞台,考據大稻埕藝旦風華、台南大正町、民俗與歷史事件,但非歷史小說,僅能視為時代小說,人設皆為虛構。古谷遼人設主要參考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西鄉孤月等日籍畫師經歷,再編撰其生平。而我刻意將男主歸為狩野派,主因為狩野派雖是日本最大畫派別,卻融合漢畫技巧,到了明治維新時代,又面臨西化浪潮的衝擊,故取其融和的涵義。再者,每每造訪日本佛寺古城時,也總為屏障畫古典精細筆觸所折服,自然男主設為狩野派的信徒,儘管當時狩野派已沒落。
偶然的一場展覽觸發一本小說的完成,似乎是很羅曼蒂克的事,但我不願它只停留在愛情小說的層次,特別發生在那絢麗年代,它該是有生命力、韌性、本土感的,所以書中除涉及台灣藝術史外,眾多角色從最初追尋一幅畫的真相,到激發改變人生的想望,全緊扣《不朽的青春》兩大元素——精神不朽與再發現。
依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公布一九二六到一九三○平均餘命,男性三十八歲,女性四十三歲,當生命相對有限、短暫的狀態下,人生的目的為何?黃土水〈出生於臺灣〉寫到:「人類要能永劫不死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精神上的不朽。」依我個人闡譯,我等雖非藝術家,然一樣能達到精神上的不朽;精神不朽並非社會認可的成功富裕一途,而是一種自我實現需求(self - actualization needs),哪怕你的理想難以被他人認同,只要能忠於自我,心之所願,那即是真正的自由,即是一種不朽。
在《下一次鳳凰花開》,我以愛情包裝理想追求,因為愛情本身就是一個美好理想。然則追尋理想不是人人都能成功,難免挫折,遭逢痛苦,許多人會氣餒,將付出視為徒勞,卻忽略不論愛情或理想不是非得要Happy Ending才有意義,有時候在尋索的道路上我們已經得到饋贈,豐富彼此的人生和靈魂。
《下一次鳳凰花開》就是在這樣背景誕生出來,也是我回饋給藝術家的感動。這是我的第一本小說,感謝秀威資訊賦予出版的機會,讓故事得以呈現於世,也感謝編輯人玉的細心協助,以及不停鼓勵我創作的皮皮、佳琪、沛慈、家禾、姿葶,也感謝正在閱讀的你。
敬最絢麗的年代,最亮眼的藝術家們
《下一次鳳凰花開》並非向壁虛造的一部小說。
去年十一月偶經和平東路二段,被懸掛於北師美術館外的《不朽的青春》文宣所吸引,進而踏入藝術鑑賞世界。我乃素人,未經專業美術教育培育,亦未接受過任何鑑賞訓練,但初見黃土水《少女》胸像時,卻深深為其美所撼動。《少女》胸像,栩栩如生,大理石透出瑩白的光輝,圓潤的線條刻鑿出平和端詳的神情,將時光凝結在最靜謐一刻,瞬間即是永恆,亦為不朽。這樣隨心的一次藝術鑑賞,讓我重新思考何謂美;細緻、典雅、新穎、大膽、活潑都是不同風格的美,然而真正能感動人心的,卻是畫家的生命力。
我來來回回遊走不同樓層,佇足於畫作、書簡、黑白相片前,就像穿越時空藩籬,一次次返回明治、大正、昭和時期,逐一認識陳澄波、陳植棋、石川欽一郎、陳進、呂鐵州等台日藝術家。進一步探究其生平,更是美得不可思議。在那最顛簸、壓抑的年代,他們試圖在畫布上綻放心靈的自由,在貧困、孤絕、病痛裡燃燒生命,孜孜矻矻地創作。
窮盡心神究竟想要彰顯什麼?陳植棋說:「用赤誠的藝術力量讓台灣人的生活溫暖起來。」那麼藝術已然超越自我表現層次,而是對土地、文化,乃擴展至對人群的愛。
我是這麼由衷感動,但也遺憾,前人遺留的瑰寶,我們幾乎是遺忘了它。我們熱心搶購每張西洋美術展覽預售票,風靡每場海外文物特展,卻疏於珍視自己擁有過獨一無二的藝術家。撇開政治立場,日治年代是不同族群、文化的融合,創作元素更多元,西洋畫、東洋畫、國畫交融出豐沛活潑的藝術品,璀璨如萬花筒。有感於台灣曾經有這麼優秀的藝術家,而我輩卻對台灣美術史了解甚少,遂起心動念欲盡一己之力,去詮釋那遠去的年代,進而點燃《下一次鳳凰花開》的構思。
為圓滿這個夢,除查閱彼時藝旦生長環境外,更反覆觀看公視藝術很有事製作的《追尋不朽的青春》、《探尋未竟的山水》紀錄片。藉由鏡頭,隨著中研院顏娟英教授暨團隊、藝術家後人探尋畫作,喚醒沉寂已久的熱忱,拂去畫框上灰塵,再次對世人展示台灣藝術的光輝。但也讓我不禁反思,藝術如何與商業共生共榮,畢竟沒有商業的支持,收藏家的珍藏,何以將作品留存、修復?
《下一次鳳凰花開》雖以一九四五年日治時代為舞台,考據大稻埕藝旦風華、台南大正町、民俗與歷史事件,但非歷史小說,僅能視為時代小說,人設皆為虛構。古谷遼人設主要參考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西鄉孤月等日籍畫師經歷,再編撰其生平。而我刻意將男主歸為狩野派,主因為狩野派雖是日本最大畫派別,卻融合漢畫技巧,到了明治維新時代,又面臨西化浪潮的衝擊,故取其融和的涵義。再者,每每造訪日本佛寺古城時,也總為屏障畫古典精細筆觸所折服,自然男主設為狩野派的信徒,儘管當時狩野派已沒落。
偶然的一場展覽觸發一本小說的完成,似乎是很羅曼蒂克的事,但我不願它只停留在愛情小說的層次,特別發生在那絢麗年代,它該是有生命力、韌性、本土感的,所以書中除涉及台灣藝術史外,眾多角色從最初追尋一幅畫的真相,到激發改變人生的想望,全緊扣《不朽的青春》兩大元素——精神不朽與再發現。
依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公布一九二六到一九三○平均餘命,男性三十八歲,女性四十三歲,當生命相對有限、短暫的狀態下,人生的目的為何?黃土水〈出生於臺灣〉寫到:「人類要能永劫不死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精神上的不朽。」依我個人闡譯,我等雖非藝術家,然一樣能達到精神上的不朽;精神不朽並非社會認可的成功富裕一途,而是一種自我實現需求(self - actualization needs),哪怕你的理想難以被他人認同,只要能忠於自我,心之所願,那即是真正的自由,即是一種不朽。
在《下一次鳳凰花開》,我以愛情包裝理想追求,因為愛情本身就是一個美好理想。然則追尋理想不是人人都能成功,難免挫折,遭逢痛苦,許多人會氣餒,將付出視為徒勞,卻忽略不論愛情或理想不是非得要Happy Ending才有意義,有時候在尋索的道路上我們已經得到饋贈,豐富彼此的人生和靈魂。
《下一次鳳凰花開》就是在這樣背景誕生出來,也是我回饋給藝術家的感動。這是我的第一本小說,感謝秀威資訊賦予出版的機會,讓故事得以呈現於世,也感謝編輯人玉的細心協助,以及不停鼓勵我創作的皮皮、佳琪、沛慈、家禾、姿葶,也感謝正在閱讀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