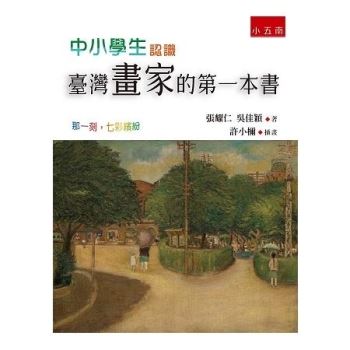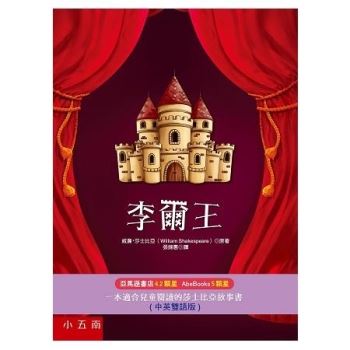第五章 渴望被愛的女人(上)
男孩接過麗雅手中的三明治,說了句謝謝。
小男孩是三天前溜進來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廚房裡翻箱倒櫃,麗雅正從堆疊的早餐桌下,摀著腫脹的腦袋爬了起來,正巧撞倒一旁的酒瓶和安眠藥罐。
他發出了驚呼,一隻手緊緊地握住美工刀,麗雅只在手機的微光中瞟了他一眼,他的手在發抖,比起傷人,他更有可能不小心傷害了自己。她只是逕自打開了斷電的冰箱,翻了翻幾個還不算發霉太嚴重的冷凍麵包,然後從櫃子裡撈出鮪魚罐頭,胡亂就想打發一餐。
她遞給了男孩一片,男還沒敢接過,她就擱在了桌上,比起拿刀的男孩,她更害怕拿攝像機的和麥克風的那些人,因為那遠比刀械,更能在她平靜的日子裡割出一道狹長的口子,令她的世界血流不止。
麗雅問了他很多問題,他沒有回答,除了他的名字,他說,他叫盧男。
他吃完了麵包,奇怪的是,他沒有走,他像是也沒有地方去,而後來門外記者時有時無的敲門聲,還有潑漆叫囂的義勇人士,讓盧男只好乖乖揀了個角落,坐了下來。
他和麗雅的話不多,大多是麗雅問,而盧男選擇性地回答,盧男的個頭不高,瘦瘦小小的,麗雅總會在麵包切片上,多裹上一些罐頭餡料,他這個年紀的孩子,就應該要多吃一些,畢竟還在發育呢!他應該比冠軍大個三、四歲吧?會不會在學校也被欺負呢?麗雅腦中閃過很多很多的問題,但她也不是真的想要從這些問題裡得到答案,這幾個月以來,她不知道她究竟想要得到的是什麼。
她突然想起了那個直播主,下意識的,她撈起了桌上的手機,想找找關於她的訊息。
直播主叫楊思敏,就是許太太口中棄屍殺人案的主角,她和李心惠都是知名的網路紅人,李心惠最後被人發現的時候,是在山上的亂葬崗裡,她的五官被劃得面目全非,令人髮指!而最後一通的通聯記錄,則是從她的好友楊思敏的手機撥出的,目前警方雖沒有確切證據,但仍不排除楊思敏和她的男友游俊瑋串通殺人。
楊思敏自從事發之後,便鮮少主動在鏡頭前露面,她的代言、活動、廣告、主持全給撤了下來,但她的新聞卻沒有隨著她的銷聲匿跡而減少,記者和網友總能努力不懈地扒出她的歷史、住處乃至於她的家人。
她不知道為什麼還在關注她的消息,是因為覺得案情不單純嗎?是因為她過得和自己差不多悽慘嗎?還是因為想藉由內心的道德去公審別人,證明自己和世界沒有對立,自己並沒有站在道德的對立面嗎?她不知道,麗雅沒念過多少書,她不知道自己關注這條新聞的意義是什麼,更多的,應該只是想要轉移對冠軍的注意力吧。
突然一則網友的評論跳了出來,扔了一個網址,把黃麗雅帶到了一個直播間。
原本銷聲匿跡的女孩,脂粉未施地,出現在了直播間裡。
她出現在最熟悉的螢幕裡,她們這一行像是掌心裡的商品,每一個鏡頭前的買主,或許都用著不潔的手掌一手握著螢幕,更有的,另一手還握著生殖器。
她知道,她怎麼會不知道?她在這樣的一個花花世界裡築起了一座粉紅色的城堡,糖果的雲朵、琉璃的馬車、彩虹的吊床和雲霞砌成的一磚一瓦。楊思敏不是一個富裕環境下出生的孩子,她是一個不知道父親的孩子,而母親早早就和別人另組了家庭。
因此楊思敏必須很乖、很聽話,她必須懂得怎麼察言觀色,她必須在繼父酒醉後跪在門口,任他打罵、任他奚落,任他對自己逐漸成熟的胴體恣意妄為,她曾經在直播裡和李心惠說過,她說過不喜歡自己的大胸部。李心惠是大學後才認識楊思敏,她並不知道她的過去,只以為是在和自己開玩笑,就像那些考九十九分的孩子,卻還在抱怨為什麼丟失了那一分?而如今,鍵盤俠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句話,論壇上早已經被做成了各種戲謔的梗圖和創作文。
楊思敏也不是天生就懂得討好,沒有人應該一出生就懂得卑微。但她的母親總在被繼父家暴後,告訴她,要不是因為她,母親應該獲得更好的人生。而她的繼父在對她毛手毛腳後,總會告訴她,她現在張口的每一粒米,甚至連月事用的衛生棉,都是從他褲襠裡生出來的。
她記得高中的歷史老師曾經說過,部分的基督教派,倡導原罪論,這「原罪」,來自於被惡魔蠱惑的男女,偷嘗了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園。因此,人的終其一生,都在贖罪、都在懺悔,就像她高三那年的某個深夜,險些被繼父強暴,衣衫不整地逃出了家門,原罪,來自於被歲月逐漸催熟的女體。
後來的事情,她不想回憶,半工半讀,上了大學,接觸了直播軟體,也認識了李心惠。直播裡的世界太過新鮮,對楊思敏而言,就像是烏托邦裡的世界,她原本平庸的歲月、拖累生母大好人生的原罪、令繼父覬覦那逐漸臻於成熟的胴體,一切的一切,在這裡成了褒獎和激賞。
她換掉了發霉的床單,換了小窗簾,為自己買了一台代步的摩托車,也從男女混雜的雅房,換成了有電梯的小套房。她開始喜歡化妝,開始喜歡照鏡子,淋浴後,她會趁著蒸氣,在霧濛濛的鏡子前面,悄悄地端詳自己的肉體。
她開始說服自己,即使是這樣的自己,也不必太過厭惡,或許,可以試著喜歡自己。那些個勵志書上不是說過嗎?人要先喜歡自己,別人才會喜歡妳。在直播的世界裡,每個男人都說愛她,都說想要娶她,連鏡頭彼端陌生的那些人,都喜歡上這樣的自己了,母親,如果相遇,一定也會喜歡自己的吧?
她一直想著有一天,當她足夠愛自己,能給母親過上好生活的時候,她要去見母親,她相信母親不會再對她辱罵,她要彌補因為自己的誕生,而將後半生葬送在繼父手裡的母親。
可就在楊思敏準備好一切以前,母親,還是毫無防備地,闖進了她的人生,更確切來說,是闖進了她工作的場域。她還記得她受邀到了汽車展場,她的第一場秀,久久未連絡的生母,衣衫襤褸的,就在圍觀的人群堆裡。
她熱淚盈眶,怎麼結束了上半場秀她已經不記得,只記得中場休息的時候,母親開口跟她要了十萬,後來,就是好幾個十萬。聽說母親也開始酗酒,開始沾賭,不知道是被繼父感染了,還是繼父是那條纏繞在禁果樹上的惡魔,而母親,只是剛好被誘發了本性。
她還記得那天,她本來想給母親一個擁抱,可最後,卻只從皮夾裡掏出一疊現鈔。
螢幕下方跳出了各種辱罵的對話評論,她幾乎忘了自己正在開直播,楊思敏從來沒有這麼赤裸地暴露在螢幕前,她大大的黑眼圈掛在眼窩下方,油光和蠟黃的肌膚赤條條地暴露在觀眾面前,她脂粉未施,凌亂的髮絲掛在嘴角,那些「母豬」、「妓女」、「殺人犯」、「狗男女」等等惡毒的言論她這陣子沒有少聽過。
那些曾經對著她直播打手槍的男人,如今一個個成了捍衛正義和司法的完人。有什麼辦法呢?她的城堡、她的王國、她的琉璃馬車,全是從他們褲襠裡撈出來的,就像那個她幾乎快忘了長相的繼父一樣。而那些平常喚她姊姊妹妹的姊妹們,如今卻像是她得了傳染病一樣,一個一個開始隔離,更有的,在她們的直播裡狠狠踩上她一腳,再創點閱新高峰。
比如,尋歡力捧的直播甜心,廖子喬。
楊思敏擦了擦眼角的淚光,她在開直播前就告訴自己,這個世界,不值得這麼多眼淚。
「各位小寶貝們晚安,我是你們的敏敏,答應你們的十萬粉絲Q&A今天一次回答給大家。」
楊思敏的尾音有些顫抖,她還記得自己是多麼努力才爬到三十七萬的追蹤人數,那些現在用骯髒字眼辱罵她的帳號,她都曾在深夜一則、一則回覆他們每一個人,哪怕,只是說一句晚安。她仍然記得自己剛滿十萬追蹤的心情,那種久久未能散去的悸動,到現在都還不曾冷卻。
「或許我是第一個因為被退追蹤,而重複舉辦十萬問答的直播主吧!」她一面說,一面打開了她的臉書,然後說道:「謝謝熱心的網友將『楊思敏滾出直播圈』的粉專連結貼給我,熱心的站長BITCHYANG748還幫敏敏整理了各項網友們想問敏敏的問題,我從三萬八千則留言裡,過濾掉單純辱罵的訊息,有七千多人想問我,心惠每天晚上壓妳,妳睡得好嗎?」
楊思敏苦笑,然後說:「謝謝各位網友擔心我的身體狀況,我最近確實失眠,但是一次,一次心惠也沒來到我夢裡。」她說完緊接著回答第二題:「另外六千多人想問我,左乳頭是不是有一顆痣,因為曾有網友爆料我在東區夜店公廁和男人亂搞,是嗎?」
右下角的評論頓時達到了沸騰,一則又一則正氣浩然的評論像一隻又一隻無形的手,從螢幕裡伸了出來,想要撥開女孩最後一道,也是最私密的防線。他們大義凜然、他們剛正不阿、他們集天地浩然之正氣,只是想要替李心惠討一個公道,是吧?是嗎?
楊思敏咬著下唇,盯著數百、數千、不,或許數萬則,那些認識的、不認識的,全都想看她的笑話;她是個女孩,二十二歲,她的世界乘載了太多太多,多到她幾乎忘了自己還是個女孩,但短短幾個禮拜,她卻已經站在道德的彼岸,和整個世界對抗。她對不起誰她不知道,太多太多的社會法則,是學校教科書本裡不曾教過,太多太多的仁義禮教,現在在不斷跳躍而出的評論裡,叫她學會幫乾爹們漱懶覺。
一瞬間,這個世界變得好陌生,她到底是誰?她又為何而生?如果人出生就註定要死亡,那來到世界的意義又是什麼?如果人一出生,就注定要背負原罪,那為什麼又要給人們那些如永夜閃爍微光般的希望?
楊思敏深吸了一口氣,撥去了外衣,粉紅色的胸罩包覆著渾圓的胸脯,她說過,她不喜歡自己的胸部,那個吸引繼父犯罪,和破壞家庭和諧的凶器。當母親被酒醉的繼父施暴過後,母親會給她一記耳光,因為她的胴體勾引著繼父,而她的出生,耽誤了母親邁向大好人生,因為母親常說,如果沒有她,她會嫁得更好,不是嗎?
一個正義的魔人說,楊思敏,是在為往後的全裸寫真鋪路,是在沉寂過後,想靠著少女初脫,脫出一條演藝之路。
往後?自從李心惠死後,她從來不知道有沒有明天,這個世界太苦、太苦了。
她解開了後背的排扣,將自己毫無保留的暴露在螢幕前面,酥胸無瑕,如皚皚白雪,沒有任何一粒污點。
她以為這樣一來,就得以解脫,可是圍觀的人數戲劇性地攀升,已經沒有人記得她為什麼解開自己的胸罩,沒有人記得誰爆料她在東區夜店和男人亂搞,更沒有人記得誰殺死了李心惠,沒有人記得欠了這女孩一句道歉,而女孩應該為了自己沒有褪去內褲,愛撫自己的敏感帶,用來取悅這些高高在上的審判長,而感到深深地抱歉。
她憤怒、她羞愧、她傷心、她癲狂,這時候她腦中閃過了一個禮拜前的新聞,《水果周刊》的記者,採訪了她的母親,她知道,母親是愛錢的,儘管在楊思敏所剩不多的理智裡,她想相信,想相信母親愛她,想相信這個辛苦懷胎十月的女人,愛她更勝過鈔票,但新聞,卻狠狠擊碎了她最後的信念。
她突然開始大笑,抓起鍵盤,狠狠地朝自己的額頭瘋狂地砸去,然後對著螢幕咆嘯道:「我只是,想要有人愛我!」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聽說,聽誰說?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 158 |
Books |
$ 158 |
大眾文學 |
$ 176 |
中文書 |
$ 176 |
小說 |
$ 180 |
現代小說 |
$ 18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聽說,聽誰說?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聳動的新聞標題像一把利刃,割開了早餐店老闆娘王麗雅的平凡生活。
那些我們以為風馬牛不相及的新聞報導,讓每一個讀者成了嗜血的道德審判長,在網路的彼端定下萬劫不復的罪刑。
知名網紅的假面閨蜜情殺、議員黑幫勾結謀財、堯姓女學生遭集體霸凌案……,一篇又一篇的獨家,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熱浪席捲了整個社會,而麗雅竟然成了故事主角,被充滿正氣與道德的網友在法律無法制裁的地帶,宣判了她社會性死亡。
什麼是真相?
我們都只是聽說──聽說,到底是聽誰說呢?
作者簡介:
我說你聽/
我特別喜歡一個觀念,叫做「作者已死」,是由羅蘭巴特所提出的。
簡單來說,當作者完成一部作品,作品本身就已經脫離作者,這樣一個獨立的文本交到讀者手中,經過每一個人閱讀後,都能產生不同的觀點和想法,去詮釋作品本身。
當你拿起了我的作品,形同於茫茫人海裡遇見了我,如果你不趕時間,我將為你娓娓道來一段故事。
這裡容我鄭重地向你自我介紹,我是——我說你聽。
章節試閱
第五章 渴望被愛的女人(上)
男孩接過麗雅手中的三明治,說了句謝謝。
小男孩是三天前溜進來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廚房裡翻箱倒櫃,麗雅正從堆疊的早餐桌下,摀著腫脹的腦袋爬了起來,正巧撞倒一旁的酒瓶和安眠藥罐。
他發出了驚呼,一隻手緊緊地握住美工刀,麗雅只在手機的微光中瞟了他一眼,他的手在發抖,比起傷人,他更有可能不小心傷害了自己。她只是逕自打開了斷電的冰箱,翻了翻幾個還不算發霉太嚴重的冷凍麵包,然後從櫃子裡撈出鮪魚罐頭,胡亂就想打發一餐。
她遞給了男孩一片,男還沒敢接過,她就擱在了桌...
男孩接過麗雅手中的三明治,說了句謝謝。
小男孩是三天前溜進來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廚房裡翻箱倒櫃,麗雅正從堆疊的早餐桌下,摀著腫脹的腦袋爬了起來,正巧撞倒一旁的酒瓶和安眠藥罐。
他發出了驚呼,一隻手緊緊地握住美工刀,麗雅只在手機的微光中瞟了他一眼,他的手在發抖,比起傷人,他更有可能不小心傷害了自己。她只是逕自打開了斷電的冰箱,翻了翻幾個還不算發霉太嚴重的冷凍麵包,然後從櫃子裡撈出鮪魚罐頭,胡亂就想打發一餐。
她遞給了男孩一片,男還沒敢接過,她就擱在了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 次
第一章 楔子
第二章 說故事
第三章 誰是楊思敏?
第四章 故事主角
第五章 渴望被愛的女人(上)
第六章 渴望被愛的女人(下)
第七章 不一樣的家庭
第八章 大火
第九章 失格
第十章 信仰
第十一章 國民男友
第十二章 獨家新聞
第十三章 十年
第十四章 終章
第一章 楔子
第二章 說故事
第三章 誰是楊思敏?
第四章 故事主角
第五章 渴望被愛的女人(上)
第六章 渴望被愛的女人(下)
第七章 不一樣的家庭
第八章 大火
第九章 失格
第十章 信仰
第十一章 國民男友
第十二章 獨家新聞
第十三章 十年
第十四章 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