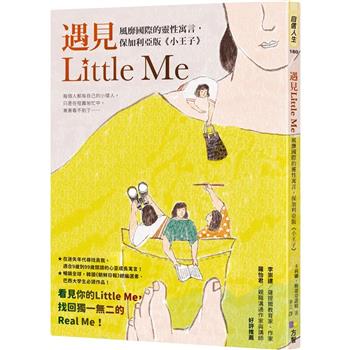【第一章 蟄】
小便斗裡的黑色小蟲扭動著。一共三隻,兩左一右在尿漬上蠕動,磁磚內側上方凹槽結著蜘蛛網,網裡黏上幾隻小灰蚊,八腳生物蠢蠢欲動,喀拉喀拉甩動細瘦前肢,連這裡也有蜘蛛網,多久沒有人進來這裡了?
我想也是,時間在這裡倒是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小蟲大概不到泡麵碎屑的一半大,可能是蛾的幼蟲吧我猜,門口地上有隻死的,差點被鞋底不經意踩碎,這裡的蛾太多了,有大有小,也有那種會爬在馬桶坐墊下趕也趕不走的怪異小蟲,又或許是某種沒有人知道名字的突變新種,我不知道,城市生態系複雜,每天都在發生各種難以理解的事情,小蟲們在通往水孔的壁邊扭動身軀,怎麼會生在這種注定長不大的地方呢?還是故意出現在這裡的?
陰謀論作祟,拉開褲檔拉鍊,尿液傾瀉,沒有要刻意避開的意思,我不想管它們死活。
從來不參加外邊過來的什麼假清高的動保團體,對那種組織沒興趣,既然做出選擇,就必須承擔後果,對吧?雖然小蟲們也沒有腦袋能理解這個概念就是了。
今天喝的水還不夠,尿有些濁,從邊壁流淌而下,漫過其中兩隻掙扎扭動的蟲體,牠們是在掙扎嗎?掙扎必須帶著痛苦的色彩,牠們是本來就痛苦,還是我的自我意識投射,過度解釋成牠們感到痛苦?
蟲的神經系統還什麼的大到足夠理解什麼是痛苦嗎?
咬文嚼字。
我搖搖頭,不應該撿奇怪的哲學書回家看的,問題還在膨脹,自體繁殖像變形蟲,噗啦,為什麼會選擇在這裡產卵呢?母蟲的腦袋裡內建物競天擇的意識嗎?物競天擇是本能嗎?還是牠們是靠人的尿液維生嗎?有可能牠們真正的巢穴是在水孔下,這幾隻只是湊巧爬出來被我看見?牠們有選擇嗎?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說不定又只是──
停,完畢,我逼自己停止,整理好褲頭,伸手準備按壓沖水鈕,這裡還是舊式的按鈕,碰。
鳥撞在窗玻璃上,不偏不倚,正中紅心。
灰黑綠繡眼,和平時一樣,介於幼鳥與成鳥之間,鳥兒終究是長不大,無論身處都市範圍還是空白地帶,窗戶沒有破,留下幾條污漬,但那鳥應該也差不多了,沒關係,手邊有工具,一起處理。
打了個冷顫,從不高的氣窗望出去,我這時才注意到視線範圍的更後面是隻離地漂浮的巨大鯽魚,自樹叢裡露出半顆頭,頭吻部幾乎和輛公車差不多大小,從廁所窗戶的角度看出去特別顯眼,天明明還沒暗啊,嘖。按壓按鈕,嘩啦啦啦,沒想到這裡的水管竟然還有水源接通,愈來愈搞不懂空白地帶管線配置跟區域繁榮度的關係了。
水流孱弱,但足以致命,左邊那兩隻小黑蟲正好在髒水行進的路徑上,迅速被沖下水孔,剩下右邊那隻盡力想爬離水孔,可惜成效不彰,最終卡在排水口邊角,動彈不得。
願牠們安息,或是得以長生。
無所謂,沒有人會在意。
走向洗手台,鏡子整個碎掉了,水龍頭的出水極細,沒有比我的尿清澈多少,公園裡的公共廁所,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隨便將水珠抹在褲子上,點了眼藥水,戴手套和豬鼻口罩,回到窗戶邊踮腳,手指嵌進窗溝,啊,生鏽卡死了。
好吧,只好繞到外面。裝屍體的袋子擺在廁所門口,黑色防水材質,內袋分左右共三格,提起揹帶往另一頭走,廁所後還有條堆滿落葉雜草的小水溝,幾百年沒人清理了,抬腿跨過,我盡量裝作不知道遠處那隻鯽魚的存在,牠們的眼睛像某種會將人類靈魂吸進去的黑洞,分不出善惡,洞察不出好惡,我不怎麼喜歡。
有種東西叫魚類恐懼症,Ichthyophobia,當初湊巧看到覺得這單字很酷特意背了起來,算是唯一擁有的外語能力吧,書店就算沒營業很久了,裡面果然還是有派得上用場的東西,我猜我大概有一點那種症,也有可能只是單純看牠們不爽,精神疾病這種東西是給城市那裡的有錢人得的,我們這種被病症歧視的階級,只配感染肺炎啊登革熱啊之類的底層疾病。
還是得踩東西才能攀上窗戶外緣,我的鞋尖抵牆,踩水溝邊堤起跳,勉強勾著了鳥身的一部分,多試了兩次,先是尾翼,再來是爪子,最後終於整隻抓入掌中。
手套布料隔絕溫度,應該還是溫熱的,牠雙目緊閉,和其他動物不同,鳥在死亡的時候眼睛是閉起來的,羽毛雖雜亂但相較之下安詳許多,我稍微翻動牠的身體,顏色完全不像是圖鑑上的配色與模樣,整體是灰階漸層,胸腹部最淺,而尾翅像墨汁一般,甚至比手套還要深上一層。
什麼都不能相信,連圖鑑也是。
拉開袋子,其中一格較小的專門給這種小鳥,和麻雀的屍體層層堆疊,回去再統一整理,另一邊給較大一點的八哥,今天也收穫不少,有時候會撿到逃出來的白文或是鸚鵡,大多是城市那邊飛過來餓死的,一樣放這格,最大那一格給鷺鷥之類的,不過我也只遇過一次,在水溝旁,全身顆粒黑點遍布,像從泥沼裡剛挖出來。
至於三不五時會遇到的貓狗屍體,那個需要用另外的防水布包起來,再用繩結綁在背包外側,雖然養分多,但時常晚一步便被其他生物給啃得稀巴爛,時機很重要,無論是死亡還是恰好遇見,鳥類都好處理許多,也難怪許多做這行的都只收鳥類,其他一概不理。
公共廁所位在公園邊陲一角,避開那隻鯽魚躲藏的樹叢,我知道這個距離牠碰不到我,但感覺不舒服,就像食物裡面出現蟑螂鬚這種狀況一樣,噁心,無法接受,無法預知牠們下一步會有什麼動作的情況最讓人感到不安,牠仍然縮在那一動也不動,不知道在等些什麼,我討厭跟牠們打交道,溼溼滑滑黏答答,沒有半點溫度。
我決定提早回家,今天這樣的量夠了。往反方向走,樹叢另一側忽然有動靜吸引我的注意,唰唰唰唰唰,轉頭,樹叢底部竄出隻小黑狗,還活著,但明顯營養不良,太過去可是會被那隻笨魚給吃掉啊阿呆!我邊想邊繼續走,沒有打算靠過去,但牠眼睛發亮,迅速衝至我腳邊再退回一段距離,雙腳拍地,翹著屁股狂搖尾巴,還是隻小狗,對這世界還抱持熱情的小生物。
忽然想起自己戴著豬鼻外觀的防毒面具,對豬鼻有興趣嗎?真難得,我傾身蹲了下來,慢慢伸出右手,牠在手掌周遭蹦蹦跳跳,踩起一小團沙塵,忽前忽後,除了左眼有圈淺棕色細毛,全身上下黑不溜丟的,牠對著我的手套張嘴撲咬,一副終於找到玩伴的樣子,媽媽呢?你媽媽呢?流浪動物的附近總是有母親,生物本能展現,純天然內建。
牠還是異常興奮,有沒有媽媽似乎也無所謂。
天然不天然,人工不自然,天生或後生,本性與偽裝,所有事情似乎都比愚蠢至極的人類想得還複雜,我想起側袋有肉條,前幾天賣場旁巷子垃圾桶撿的,「欸!等我一下,小黑你等我一下。」
胡亂取了個沒創意的綽號,反正牠也聽不太懂人話,口水亂噴,牠發出興奮低鳴,狗可以吃人吃的東西嗎?應該沒關係,反正都不是天然的,活得長跟活得短也只是相對概念,宇宙洪荒與電光石火都只是時間作祟。
嗷嗚,肉條被一口咬走,虎牙差點劃到手指,沒家教的死小孩,我縮手,袋裡還有一條半,全部給牠吃會不會太多?這種空氣拔面罩應該沒事吧?抬頭看了破舊路燈之後的紫色天空,沒有半朵雲,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脫掉面罩,就這麼辦。
吧喳吧喳亂啃一通,小黑前掌壓著肉條,吃得津津有味,我將另一條放在腳邊,拉下豬鼻,牙齒撕開斷成兩截的剩下半條,有股奇怪的冰箱冷凍味,跟空氣無關,肉上沾染到生魚的氣息了,難怪專賣過期食品的超市扔了一堆在巷子裡頭。
不舒服,我憋氣嚥下,將剩下的肉條一併推過去給小黑,那家裡面那堆要怎麼處理勒?之後都帶來給小黑吃好了。
「小黑你慢慢吃。」
站起身子,那小傢伙迅速看了我一眼,尾巴搖啊搖,但沒有心力顧及我的動作,滿腦子只有吃,小狗就是這樣,一點危機意識也沒有,要帶去給狗王養嗎?算了,麻煩,我掛回豬鼻,放輕腳步後退離開。
今日善事的扣打已用罄,有事擇期再約。
那隻鯽魚還是懸浮在那,嘴巴一開一闔的,我抬起頭,有群烏賊從包圍公園的建築物後方游出,鰻魚躲在陰影處探頭探腦,鐵甲擾動城市霧霾,夕陽從高樓夾縫刺入,這時間點正好是所有生物出動的時間,螃蟹迅速爬動,海葵伸展觸手,海鯰、毛鱗、狗母、鼬魚、青頭仔、水針、學仔、紅大目仔……
這是座海底城,沒有水的海底城。
魚在空中飛,聽起來有夠荒謬,可荒謬久了自然成習慣,習慣成自然,感覺荒謬或許才是真的荒謬。
又在咬文嚼字。
轉過彎後就不見小黑身影了,有緣會再相見的,公園入口處的ㄇ形欄杆不曉得被什麼鈍器給痛砸一頓,中間整個凹下碰觸地面,抬腳跨過,左右各一排圍繞公園的枯萎矮仙丹,人行道一片狼藉,垃圾滿地,路旁燈柱破損歪斜,好幾輛故障生鏽的汽車停在路旁,擋風玻璃整片碎裂,彎曲藤蔓竄升攀附車身,像被拋棄了上百年之久。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這裡是墳場,曾是烏托邦的墳場。
這樣說其實不太準確,將城市規劃成烏托邦並不代表它就會變成烏托邦,原本設計成天橋的各式柱狀鋼材石材裸露,從地上或是建築物的側邊牆面一根根長出,有些蓋得較早,幾十年前工程單位已放上了可行走的橋面,但橋是否能夠通往目的地,還是懸在半空讓不注意腳邊的人摔死或重傷不得而知,這種事在這裡稀鬆平常且繁瑣,大家都是習以為常。
我踩著滿布裂痕的柏油馬路,跨過早就稱不上是封鎖線的黃色塑膠長帶,走上公園旁足足有三層樓高的灰黑天橋,背包只有半滿再多一點點,回家前去吊人樹那邊看看,說不定會有所收穫。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水泥碎塊在鞋底膠面下崩解,連續三周繞來這裡,也算是熟悉了不少,每一條走過的路徑都是微薄貢獻,生鏽鐵桶擋在階梯盡頭,側著身通過,掃落幾隻欄杆上跳躍的草蝦,牠們會飛會游,摔不死,緩緩飄落至下方的另一團混亂之中,這部分的天橋設計成四條直線圍繞的正方形,我記得要到斜對角去,拐彎,夕陽正好直射眼珠,刺痛角膜,這大概是日光少數能辦得到的事情之一,早就喪失網路辭典裡說的熱度以及殺菌效果了,如果真能殺菌,那這座城市大概會直接消失在地表上吧我猜。
九十度直角後方延伸三個新選擇,左邊往下繞進二樓的大樓夾縫中,順著一直走會有間酒吧開在盡頭,這時間點應該還沒開門;中間向上穿進曾是辦公室的多功能中心,常有人在裡面舉辦宗教儀式之類的,無可厚非,這裡需要救贖與大量心靈寄託,再過去有個懸空的廣場,上萬噸可回收垃圾的暫時處理場地,有一些攤販會在那裡補給回收垃圾的居民們;右邊一樣向下,但是是通往地面,純粹是天橋入口,再走一段是地下道入口,那個方向時常有幫派分子出沒,遇到他們被找麻煩的機率大概三成,浪費時間也浪費尊嚴,還是走中間比較符合經濟效益。
說到經濟效益這個詞,當初還是從組織裡其他人那裡聽來的,忘記是白白還是妮娜說的,他們比較聰明,有的沒的鬼點子也比較多,總之我們負責的任務不同,該在期限內完成的事也不太一樣。
總之先走中間,等等再繞個路就好了。
到達四樓前遠遠便看到牆上的聖母迎接我的前來,她雙手自骨盆處微微張開,呈現接受擁抱的姿勢,溫柔和善,素色長袍被抹得髒兮兮,外頭披著另一件布料,低垂著頭俯視到臨的每一個過客,花圈漂浮頭頂,背後聖光根根突刺而出,像牆上重新噴漆過的鐵欄杆尖刺,可惜我看不見她的雙眼是否慈愛,鼻翼之上額頭之下被黑色噴漆抹去,像試圖用拙劣手法遮去不願被人知道的天大祕密。
腦中除了閃過記憶中媽媽模糊的身影,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所謂神的感召或奇異體驗從來沒有發生在我身上過,那些從痛苦中尋求真理的人也是些邏輯不通的怪胎吧我猜,不過怪胎歸怪胎,別妨礙到我就是了。
轉彎進到室內,到處都是被濃煙燻黑的痕跡,下午還沒開始舉辦儀式或祭典,但已經有一些人在裡頭走動布置蠟燭和柴火,男女老少都有,蒙著臉披著破布爛衫,我不想和他們對到眼,這不是我的場域,低頭左拐右彎,穿越另一座空中步道。
時不時有大魚小魚游過半空,把廢棄大樓當作珊瑚礁安居覓食,破窗、欄杆、曾是門柱之處,全都有機會遇上,或是單隻或是一群,而那些身型巨大的只能在外頭窺看,等待時機。
相較之下,步道盡頭的空中廣場卻不見貼近游過的大小魚蹤,那裡沒有什麼掩體遮蔽,反而成為海底生物避而遠之的地方,廣場上人群雜沓,一大半邊堆滿嚴謹分類的垃圾,滿身大汗、忙碌奔走的城市居民和捧著防塵罩裡甜點熱食的小販們來回穿梭,叫賣呼喊聲隔著口罩豬鼻模糊不清,時間尚早,夜晚還沒降臨。
該吃些點心嗎?手指在長褲口袋裡數著還剩多少零錢,鈔票擺在胸口的口袋裡頭,非必要時不會輕易示人,五、六、七、八……八十,花十塊買個紅豆餅來吃,還在可接受的範圍。
側身閃避迎面而來的服飾攤販,衣架上掛滿垃圾場裡撿來、重新整理過的衣褲,沒有賣鞋子,差不多該把腳下這雙換掉了,為了更精確的定位地圖,每天走來走去也差不多要把鞋底給磨平了,另一邊有賣蔥油餅和袋裝奶茶的,肚子雖然還沒有很餓,可嘴巴饞,迅速買個東西,必須趁太陽下山之前去吊人樹那裡看看,加緊腳步,太晚回去可就不好了。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空白地帶的圖書 |
| |
空白地帶【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22-03-09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Books |
$ 221 |
Books |
$ 221 |
科幻/奇幻小說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科幻小說 |
$ 252 |
華文奇幻/科幻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空白地帶
「願光芒照耀『空白地帶』的每個角落……
我們可以接納一切,但請不要奪走我們生存的權利。」
實力派作家陳建佐Chazel繼《恩索夫》後,再次挑戰賽博龐克(Cyberpunk)的題材;
一本充滿人性考驗、善惡之辯與階級鬥爭的原創故事重磅登場!
在遙遠的未來,人類進入高度資訊科技發展的新時代,在看似光鮮亮麗的城市背後,有一塊從來不被關心的區域,那裡的居民住在沒水沒電的廢墟之中,隨時可能被搶被殺。他們有永遠處理不完的垃圾、無法跨越的地區管制線、新興宗教團體「聖母之愛」、一棵吊滿屍體的「吊人樹」,還有在天空不斷出現的「黑色鯨魚」……人們稱這個地方為「空白地帶」。
「荒」是「空白地帶」的收屍人,平常的工作是尋找野外的動物屍體,用它們來餵養「樹」,還有完成「組織」交派的各種任務。某日荒遭遇不曾見過的武裝團體「黑斗篷」,被迫處理來自於城市的人類屍體。為了查明黑斗篷與政府的關係,荒拜託熟知各種眉角的「賣情報的」與勢力不容小覷的「狗王」一起協助調查。沒想到整起事情的背後,有著超乎想像的利益糾葛與歷史黑幕……「空白地帶」到底是如何形成?又為什麼會有「組織」聘用收屍人?在各方勢力衝突的最後,這個社會的殘酷真相猛烈襲捲城市裡的每一個人!
作者簡介:
陳建佐Chazel
27歲,喜歡音樂與玩具,對許多創作題材皆感興趣。
曾出版奇幻小說《莉莉絲》、《恩索夫》,科幻小說《鯨滅》。
皇冠雜誌《明日與那些幽微之時》專欄作家。
得獎紀錄:
103年高雄青年文學獎大專成人組短篇小說首獎
108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師組短篇小說項佳作
2020城邦集團「書寫1960歲月台灣」短篇小說組佳作。
個人網站
https://www.instagram.com/chazel315/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蟄】
小便斗裡的黑色小蟲扭動著。一共三隻,兩左一右在尿漬上蠕動,磁磚內側上方凹槽結著蜘蛛網,網裡黏上幾隻小灰蚊,八腳生物蠢蠢欲動,喀拉喀拉甩動細瘦前肢,連這裡也有蜘蛛網,多久沒有人進來這裡了?
我想也是,時間在這裡倒是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小蟲大概不到泡麵碎屑的一半大,可能是蛾的幼蟲吧我猜,門口地上有隻死的,差點被鞋底不經意踩碎,這裡的蛾太多了,有大有小,也有那種會爬在馬桶坐墊下趕也趕不走的怪異小蟲,又或許是某種沒有人知道名字的突變新種,我不知道,城市生態系複雜,每天都...
小便斗裡的黑色小蟲扭動著。一共三隻,兩左一右在尿漬上蠕動,磁磚內側上方凹槽結著蜘蛛網,網裡黏上幾隻小灰蚊,八腳生物蠢蠢欲動,喀拉喀拉甩動細瘦前肢,連這裡也有蜘蛛網,多久沒有人進來這裡了?
我想也是,時間在這裡倒是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小蟲大概不到泡麵碎屑的一半大,可能是蛾的幼蟲吧我猜,門口地上有隻死的,差點被鞋底不經意踩碎,這裡的蛾太多了,有大有小,也有那種會爬在馬桶坐墊下趕也趕不走的怪異小蟲,又或許是某種沒有人知道名字的突變新種,我不知道,城市生態系複雜,每天都...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後記】
嚴格說起來,這次聚焦在《鯨滅》之後,但也難以稱作是續集,頂多是借用許多相似概念,延續一些喃喃自語和莫名其妙的突發奇想,東拉西扯,造就了這個故事的完成。
前陣子在達米恩(Damien Rudo)的《悲傷地形考》裡看見他提到了馬克歐傑(Marc Augé)的超現代性和非地方(non-places),指稱汽車旅館、機場休息區、加油站、超市之類通行和消費的過渡空間,缺乏歷史和記憶,空間中的人只是某個正好身處其中的旅客,忽然覺得一直以來有興趣的部分事物聯結在一起,馬克歐傑的那本《非地方:超現代性人類學導論》既薄且...
嚴格說起來,這次聚焦在《鯨滅》之後,但也難以稱作是續集,頂多是借用許多相似概念,延續一些喃喃自語和莫名其妙的突發奇想,東拉西扯,造就了這個故事的完成。
前陣子在達米恩(Damien Rudo)的《悲傷地形考》裡看見他提到了馬克歐傑(Marc Augé)的超現代性和非地方(non-places),指稱汽車旅館、機場休息區、加油站、超市之類通行和消費的過渡空間,缺乏歷史和記憶,空間中的人只是某個正好身處其中的旅客,忽然覺得一直以來有興趣的部分事物聯結在一起,馬克歐傑的那本《非地方:超現代性人類學導論》既薄且...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蟄】
【第二章 破土】
【第三章 藤騷亂】
【第四章 繁花盛開】
【後記】
【第二章 破土】
【第三章 藤騷亂】
【第四章 繁花盛開】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