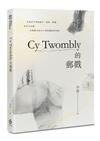〈迪耶普〉
不知何時起了雲,海灘變得清冷。我合上斯皮瓦克譯的《論文字學》,疊好毛巾,抖抖身上不多的沙子,往停車場走去。
四個男人在用地鑽搗碎水泥地面。他們邊幹活,邊聊天,慢悠悠地,但絲毫不給人磨洋工的感覺。個子最高的是黑人,下巴寬平,如一把鏟刀。兩個矮小的看著像阿爾及利亞人,捲髮,眼窩深陷。我興致勃勃聽他們談論球賽和姑娘,差點忘了他們站立的地方,我上午在那裡停了一輛福特。
「先生們,打擾一下。我好像在這裡停了一輛車,能不能麻煩告訴我,它現在去了哪裡?」
他們停下手中的活兒,詫異地相互看看,然後才轉向我。那位黑人用印度式英語慢條斯理地說:「兄弟,這不是停車場,你看看這把椅子。」他指著旁邊固定在地上的長椅。
「歡迎大家來到敦克爾克!」此時,後面來了一群印度遊客。敦克爾克?我不是在迪耶普?其中一個小夥子突然走過來:「爸爸,你怎麼在這裡?」我一輩子單身,不過,他確實長得太像我了。
〈索維拉〉
她一臉倦容,從我手中接過那瓶白瞪羚。從繃緊卻又不帶絲毫警覺的狀態,我有九分把握她一生優渥,童年有充足的水分,家庭財富一直滋育著她,不像那些我熟悉的瞪羚,健美優雅的身體裡面,無處不充滿躲避危險的基因。
「多麼美!」她的英文發音脆亮,像靴子踩在乾爽的積雪上。我在一部北歐電影裡聽見過類似的聲音。我知道她在讚美眼前大風捲起的浪花和水汽。她的生活太平靜了。
「夫人,這是我們當地最好的,產自阿爾甘莊園。阿爾甘就是──」我看見她嘴角輕微一動,即刻恢復到原來的樣子,我把後半句話收了回去,改口道:「當然,和勃根地還是不能──」
「不錯。」她明顯意識到了自己的傲慢有點粗魯。「多麼豐富,大海、山脈、沙漠,原始、古老、神祕,一個人還要什麼?」她知道自己靠近了矯情的邊緣,我注意到她眼睛有些濕潤。
「風真大!」我回頭,望著海灘上奔跑的孩子。我和她如此遙遠,卻彼此吸引,如同月亮和潮汐。
〈興隆鎮〉
我未來的父親將因為他的創建進入歷史。
他是色盲,只能辨識三種顏色:白色、灰色和深灰色。他熱愛閱讀,雖然字跡淺淡。他迷戀幾何和哲學,認為那是人類純粹的家園。他籌款買下海邊的一塊空地,開始建造他的理想國。他把每一粒沙子塗成白色,將那些棕櫚樹壓彎成二十度角,向上生長。他說,無法衝浪的日子,人們可以在樹幹上玩滑板。雖然樹幹和樹葉在他眼裡分別是灰色和深灰色,但依照真實不虛的想法,他希望它們真正是灰色和深灰色的。人們說起它們,不會再用棕色和綠色之類的詞語。他不知從哪裡得知,廣西石林有一位神人會施法,讓東西變顏色。神人小時候非常頑皮,到處破壞東西。神人的父母每天給別人賠禮道歉,苦不堪言。他們最後不得不把他鎖在一間空屋子裡。他一邊撕心裂肺地哭叫,一邊撓牆。他的手指破了,血跡在牆上變成一條蜥蜴,鑽進他的體內。他從此獲得了神力。我父親說,他夢見過這位神人。他要去請他,不惜一切代價。
〈北滘〉
純粹的抄襲需要純粹的感受力,否則難以徹底。我在抄襲過程中,一半是心慌,一半是無知,遺漏和弄錯了不少。原作的作者,一個包工頭,以無比豪邁的手勢,像趕蒼蠅那樣,把我放過。但一顆煎熬的心不放過自己,命令我一一更正。
1. 「原材料」被省略了。那個來自比哈爾邦的記憶非常原始,如同暴力和貧窮,五花八門,填充了日子凹陷的部分。
2. 金屬的行為表現,不是反應。物質的自身感受,超越人們對它的擠壓、打造和扭曲。我坐在涼茶鋪門口,無法解開自己。
3. 裝置充滿張力,極富戲劇化。我從未進過劇場,也討厭他們誇張的方式(這只是我的猜測),於是我就用了「精美」一詞,來形容一臺幾百噸的衝壓機。
4. 神蹟在屎尿中,看著它,即可見證。任何動作都是多餘的。「以」比「以為」還重,我用力過猛。
5. 那些沒有敲響的聲音迴蕩。我耳鳴,因此背離了原文的玄妙,加了俗氣的「清脆」一詞。
〈斯喬爾登〉
第一封信裡面是空的,信封上沒寫收信人的名字,而是寫著三天後的日期,信是從英國劍橋寄出的,地址字跡潦草,寫字人心不在焉。我在信封背面看到一些痕跡,印證了我的猜測。這個寄信人想破解密碼,卻把自己變成了密碼。
第二封是他在船上寫的,抱怨天氣和自己的怯懦。「工作艱難,卻是值得的。我知道,只要我不開始,一切都無從開始。」我記得他寫過這樣的話,但我最近經常失眠,容易把牧師說的話和他信裡的內容搞混。我需要喝點阿夸維特,活躍一下記憶。
等等,我聽見木匠的咳嗽聲。婆娘死後,他心情一直不好。我怎麼講笑話給他聽,他都愁眉不展。「笑話不夠嚴肅時,本身就是個笑話。」他冷不防冒出這一句,差點嗆到我。我想他並沒有搞懂他的雇主在說什麼。當然,我也只明白大概六成。有一次,他拿著圖紙,讓我找人幫他在山坡上建一座房子。「英國太熱了,也太熱鬧了。」這個是他和我說的,但我敢打賭,他不會對木匠說同樣的話。
〈馬德里〉
我終於回到了馬德里,用輕喜劇的方式。房東隔著門縫打量我,卷髮中間露出巴掌大的頭皮。他幹嘛不看我的臉,非要盯著我鬆鬆垮垮的褲子和擦不乾淨的皮鞋?對了,他居然記得,我離開時匆忙,把他的褲子連同皮鞋穿走了,現在物歸原主。
我路過不少林子,樹木在裡面生長,外圍的一圈矮一些。我跑累了,一隻鹿突然停下,愣在那裡。狼狽不堪的人不是話多就是無語。牠哀怨的眼神告訴我,獵人生前都是逃兵。反之亦然。
出去喝一杯吧?我抖了抖嶄新的二十歐元。
「我不酗酒,而且按時繳房租,是誰說的?」他露出狡黠的笑容問我,感覺就像失意多年的律師,打輸官司卻贏得被告的芳心。沒錯,我這位老房東曾經有一位漂亮的太太,雲遊四海,他思念時杳無音訊,他快忘記時總是會收到她寄來的明信片。他在客廳正中間放一張桌子,上面一本厚厚的世界地圖冊,旁邊是伽內特翻譯的英文版《罪與罰》。他把明信片和記錄我們談話的紙條夾在裡面。
〈餘姚〉
在我開竅之前,他已決定徹底剷除自己的思想,彷彿產生各種想法的大腦是一個可以隨時清空的文件夾。郊外,月亮出奇地蒼白,心事重重。「這是一個比喻,不牢靠的,如果你問我的話。」我當然不予理會,眼睛盯著那幅中堂裡的模糊人物,寥寥幾筆,像佚名作者試圖挽回局面的努力。我比較過事情在猶豫不決時的不同質地,房檐的空渺如何讓他心緒不寧。
至於影子的聲音,我相信是有的,存在於某個特殊的時刻:當內心隨著空間一起展開,江面上正好有兩艘駁船停在那裡,而他像其中一艘的纜繩泡在渾濁的水中。天色漸晚,我不得不放下簾子,打開燈。屋子裡,溽熱的空氣抱住他留下的那些殘念,非常混亂。當初他一定是在一片黑暗中左衝右突。
我們沒有商量過哪天一起進四明山,了結一樁無頭公案,但真是巧,一場雨的尾聲淅淅瀝瀝,結束在烏黑的瓦片上。我竟然跳了起來,抽出一塊。他迎面走來,接過,看都沒看,就拋向山谷。我們就這樣彼此錯過。
〈開羅〉
我在尼羅河邊喝著咖啡,他們在談論歷史,像在談論一條死蛇,具有隱祕的威脅力和醜陋的殺傷力,但現在已無用,雖然樣子還是可怕的。我的老闆是一位韓國人,深情嚴峻,肌肉緊張,每天雙眼充滿血絲,比法老還憤怒。
有一次,他帶我去酒吧(阿拉,請寬恕我!),自己喝掉一瓶。他深情地望著酒吧舞臺上的獅身人面像,然後轉過頭去,彷彿什麼也沒發生。我用蹩腳的英語說道:「獅子是熱帶動物,這裡以前溫度更高。」他每次聽我說英文,都遲疑片刻,隨即立刻若無其事地說,是的,是的,事情就是這樣。他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能力。
事情要往前追溯。在機場附近的總統官邸修建前,我們村子裡經常有陌生人路過。一些穿著羽毛做的裙子,臉上畫著蛇和花朵。他們在村口把蘆葦點燃,匍匐在地。真是奇蹟,一隻書裡的神鳥不知從何處飛來,在他們頭上盤旋,而月亮躲進了雲層,不願聽神鳥難聽的尖叫聲。一切都過去了,此刻我在咖啡杯的杯底看著當年的一切。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Cy Twombly的郵戳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Cy Twombly的郵戳
【塞.湯伯利(Cy Twombly,1928-2011)──生於美國維吉尼亞州,曾被《紐約時報》譽為「20世紀最偉大當代藝術家之一」。
作品結合了繪畫和素描的技巧,將素描的重複線條和塗鴉、潦草的書寫詞彙和油畫相結合,是為創舉而著稱。集抽象表現主義、極簡和普普藝術於一身,更影響了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1960-1988)等當代藝術家,不僅將抽象表現主義提升到新高度,更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藝術史。】
作者少況是中國翻譯家與詩人,本著作以Cy Twombly為名,呼應其抽象藝術,透過一段段的文字,詩意地、拼貼式地堆疊出各種意象。更以諸多景點、地標為名,透過行文的意境,宛如郵戳般,用文字在各地留下印記。
全書散文詩作共三百餘篇,囊括亞洲、歐洲、美洲各處地景,主題包含人事物的紀實、心靈性的思辨、超越想像的荒誕……,讓讀者宛如透過句句詩文,進入一個個嶄新的異世界,意猶未盡。
『我跑累了,一隻鹿突然停下,愣在那裡。狼狽不堪的人不是話多就是無語。/牠哀怨的眼神告訴我,獵人生前都是逃兵。反之亦然。』──節錄〈馬德里〉
作者簡介:
少況
翻譯家、詩人。
1964年生於中國上海,1982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1989年獲得該校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入職外國文學研究所。
翻譯有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艾希伯里(John Lawrence Ashbery)等詩人的作品,上世紀九十年代,翻譯出版了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的《白雪公主》和布羅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在西瓜糖裡》。2020年出版詩集《次要的雪》。《新九葉集》詩人之一。
章節試閱
〈迪耶普〉
不知何時起了雲,海灘變得清冷。我合上斯皮瓦克譯的《論文字學》,疊好毛巾,抖抖身上不多的沙子,往停車場走去。
四個男人在用地鑽搗碎水泥地面。他們邊幹活,邊聊天,慢悠悠地,但絲毫不給人磨洋工的感覺。個子最高的是黑人,下巴寬平,如一把鏟刀。兩個矮小的看著像阿爾及利亞人,捲髮,眼窩深陷。我興致勃勃聽他們談論球賽和姑娘,差點忘了他們站立的地方,我上午在那裡停了一輛福特。
「先生們,打擾一下。我好像在這裡停了一輛車,能不能麻煩告訴我,它現在去了哪裡?」
他們停下手中的活兒,詫異地相互看看,...
不知何時起了雲,海灘變得清冷。我合上斯皮瓦克譯的《論文字學》,疊好毛巾,抖抖身上不多的沙子,往停車場走去。
四個男人在用地鑽搗碎水泥地面。他們邊幹活,邊聊天,慢悠悠地,但絲毫不給人磨洋工的感覺。個子最高的是黑人,下巴寬平,如一把鏟刀。兩個矮小的看著像阿爾及利亞人,捲髮,眼窩深陷。我興致勃勃聽他們談論球賽和姑娘,差點忘了他們站立的地方,我上午在那裡停了一輛福特。
「先生們,打擾一下。我好像在這裡停了一輛車,能不能麻煩告訴我,它現在去了哪裡?」
他們停下手中的活兒,詫異地相互看看,...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輯 穿行是這裡唯一的主題】
拿坡里
布爾津
卑爾根
高州
箱根
阿布奎基
葫蘆島
戶縣
香港
綿陽
斯利那加
建德
托雷多
葉里溫
右玉
吉林
德勒斯登
自貢
哈爾濱
蒲甘
銀座
聊城
哥里
泰安
蘇州
瓦房店
靖西
無為
萊比錫
大慶
大同
洞庭
雷克雅維克
內鄉
怡保
開封
日照
福州
古丈
迪耶普
井陘
芝加哥
富爾希爾
多佛
黃瓜園
蘭州
奇馬約
伊爾富德
雅典
漢中
金邊
虹橋
【第二輯 純粹的抄襲需要純粹的感受力】
康卡勒
景洪
輪台
合肥
左岸
項城
党家村
新街口
塔林
...
拿坡里
布爾津
卑爾根
高州
箱根
阿布奎基
葫蘆島
戶縣
香港
綿陽
斯利那加
建德
托雷多
葉里溫
右玉
吉林
德勒斯登
自貢
哈爾濱
蒲甘
銀座
聊城
哥里
泰安
蘇州
瓦房店
靖西
無為
萊比錫
大慶
大同
洞庭
雷克雅維克
內鄉
怡保
開封
日照
福州
古丈
迪耶普
井陘
芝加哥
富爾希爾
多佛
黃瓜園
蘭州
奇馬約
伊爾富德
雅典
漢中
金邊
虹橋
【第二輯 純粹的抄襲需要純粹的感受力】
康卡勒
景洪
輪台
合肥
左岸
項城
党家村
新街口
塔林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