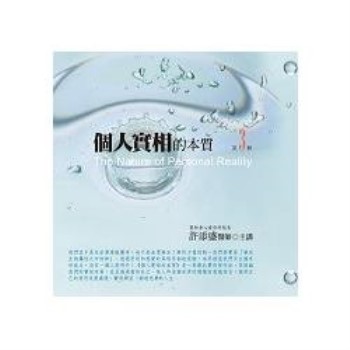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渣,是這個時代最本質也最具普遍性的人類狀態,
是刻在墓碑上的字,是風中的斷裂聲,
是紛亂的影子與世界的尖叫,是靈魂深處的怪力亂神……」
從看守所出來的豪發現,即便身體獲得了自由,自己卻依然在一個接一個噩夢中飄浮,每個夜晚都彷彿在一團渦流中掙扎,水嗆進他的氣管和肺部,讓他隨時都可能爆裂,同時也被無數無名的水草糾纏──那些黑色、褐色、深藍色、翠綠色、粉紅色的水草纏住他,使他像一頭捆得結結實實的怪物,於是他決定終結與這座城市的關係,成為一個自行失聯的人。
隨著豪的出走,也引發了好友們、妻子、女兒等身邊的相關人物,各自展開一連串對豪的追憶,從年輕時的肆意暢快,到現實相處中種種不曾被言說的不滿、嫉恨與醜陋。
當文明的假面被剝下,剩下的只有汙濁、骯髒的殘破心靈,和那些被輾碎了的歲月……
「我相信任何一種希望都將經由碎裂與消亡並在混亂與不確定性中產生。」藝術家唐寅九以長篇小說《渣》,對當代社會提出了最糾結、最沉痛的觀察與詰問。
本書特色
★「希望將經由碎裂與消亡並在混亂與不確定性中產生」──藝術家唐寅九最新長篇力作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渣 (電子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11 |
中文現代文學 |
$ 442 |
小說/文學 |
$ 457 |
中文書 |
$ 458 |
小說 |
$ 468 |
現代小說 |
$ 46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渣 (電子書)
內容簡介
目錄
│上部│
我曾經是一個醫生
豪
毅
慶
豪,出走
莫尼卡,我們來說說星空吧
我是一個死人
慶的兩篇日記
公司
姍
婕
三兄弟最後的晚饗
豪的自選詩
我想再去公司看看
小桃紅
噩夢與春夢交織的夜晚
我是一塊疤、一棵樹、一片流雲
我對你們唯有愛
姍,一個夢
斷指
│下部│
小婷和小莉
豪,囈語
豪和姍
你也認識一下我的朋友吧
莉莉
駒爸爸的下午茶
時間
少年與老人
紅頭髮的夜孩子
我曾經是一個醫生
連儂牆
豪,斷句
看看我呀,我才十五歲半
我不想做一個活死人
豪,斷句
死刑犯權最後的願望
該死的死,該亡的亡
不知不覺,我們已被某種東西毀滅
一片海灘
後記
我曾經是一個醫生
豪
毅
慶
豪,出走
莫尼卡,我們來說說星空吧
我是一個死人
慶的兩篇日記
公司
姍
婕
三兄弟最後的晚饗
豪的自選詩
我想再去公司看看
小桃紅
噩夢與春夢交織的夜晚
我是一塊疤、一棵樹、一片流雲
我對你們唯有愛
姍,一個夢
斷指
│下部│
小婷和小莉
豪,囈語
豪和姍
你也認識一下我的朋友吧
莉莉
駒爸爸的下午茶
時間
少年與老人
紅頭髮的夜孩子
我曾經是一個醫生
連儂牆
豪,斷句
看看我呀,我才十五歲半
我不想做一個活死人
豪,斷句
死刑犯權最後的願望
該死的死,該亡的亡
不知不覺,我們已被某種東西毀滅
一片海灘
後記
序
後記
這是我寫得最糾結的一部小說,從二○一七年開始,斷斷續續寫了五年。二○一九、二○二○年幾乎不敢動筆。我曾一度以為寫不下去了,因為害怕,因為遲疑,也因為好多東西還看不明白;可它幾乎已經是一本我必須每天面對且無法趕走的書。害怕且猶豫要不要寫下去的根本原因在於我不斷在問:人,人性怎麼就變成這樣了?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寫道:「渣是這個時代最本質也最具普遍性與代表性的人類狀態。整個人類都碎了,遍地成渣,撿都撿不起來!……」我並不是最早更不是唯一發出這種警示的人,類似的句子在艾略特的詩中俯拾皆是。但問題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過,也沒人把渣當作一本書的書名,當作是最具普遍性與代表性的人類狀態。
寫這本書幾同於把自己的心剖開、切片然後觀察、自嘲、分析……,正如批評家唐明先生在評論我的另一篇小說時說的話:「它充滿了絞刑架下的詰責與拷問。」通過一顆小小的卻又無比複雜和滄桑的心,我試圖想完整地看一看人性到底有多黑暗、多骯髒,又有多變態、多分裂;我想要看清楚,看它到底碎到了怎樣的程度!渣,從來就不是一個形容詞,它不是一種比喻,不是我們在打比方、舉例子;它也不是一個名詞,雖然它是,首先是一種物理狀態,但顯然不止於此,它甚至不僅僅是一種精神與心理狀態。是的,它是一個動詞!放眼望去,滿世界都是它的動作與聲音。可怕的是,作為一個動詞,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讓它停下來的方法;因為它的主語已經喪失,高貴的主語令人痛心和絕望地不在了、缺失了。這個主語不只是你、我、他,也不只是我們、你們、他們。它不是某個個體、組織與國家,而是人,是人類!人不在了,人類正在空缺,這正是問題普遍存在和日益嚴重的原因。喪失主語的動詞是可怕的,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任何主體性力量可以管控它、制止它。所以,我怎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內心的恐懼,毅然決然地堅持寫下去呢?直到寫這篇後記時,我的身體變得如此僵硬,思緒卻又如此澎湃。
《渣》最早的出發點是猥瑣。我曾藉其中的一句話表達過我的初衷:「我所寫的那本書,它唯一的主題乃是猥瑣,我要寫盡一代知識分子的墮落。」猥瑣當然是渣最基本的構成因索。猥瑣,在我看來,乃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普遍、最深刻,也最致命的根性,它比阿Q精神要更廣泛也更深入地影響了我們的民族心理。阿Q精神不過是自欺與麻木,可有時候它甚至還勉強算得上是一種臨時的、局部的、管點小用的精神療法。可猥瑣卻徹底侵蝕了我們的人格與心靈。這個世界沒有哪個民族像我們這樣遍地猥瑣,它既是我們的近現代史,也是我們的當代史。如果不承認或者不敢面對這一點,我們的人格就將永遠也不會健全,我們的心靈也將永遠不會健康,我們將永遠走不出來,更不用說以善良、美好的步伐進入人類文明的殿堂。毫不誇張地說,只要猥瑣的人格還如此普遍地存在,則無論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斷無和諧與幸福可言,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文明世界的信任與尊重。
在近五年的寫作過程中,這個世界發生了太多的事情,渣在我心裡隨之也突破了猥瑣的主題邊界,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範疇。它當然還是一部寫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書,也是一部幾乎是萬箭穿心的、寫盡猥褻心靈的書。但是它的主題及指向已經令人悲傷地擴大到了整個人類。遍地成渣是人類的現狀,是人類最大的現實與危機。改變組織、社會乃至於國家容易,改變人格、人性與人心尤為困難。連接人心的各種主題、工具、價值觀和方法論幾乎全都斷裂了;我們藉此獲得榮耀、自信、團結與信任的力量幾乎全都瓦解了,那些曾經那麼強大的宗教力量、道德力量、美的力量、家族的力量、社會乃至於國家的力量正在全面瓦解。國家行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變得像小丑似的弱智、愚蠢、不美好、不可靠及不可信任。渣不僅遍及所有領域,也在否定、嘲笑乃至於消滅數千年業已形成的文明,它每天都在以各種方式嘲笑我們──看看吧,整個人類文明,包括令人驕傲的印度文明、古羅馬古希臘文明、華夏文明……,全都如此不堪。從某種意義上講,渣正在成為我們每天都身陷其中的咒語與厄運。如果沒有更大的勇氣與智慧,沒有更廣闊的視野與胸懷,沒有更多的愛、更徹底的改變,那麼我們的文明就真將不堪一擊。
從《赤腳狂奔》、《一小片浮雲》到《懸空的椅子》,從《一片海灘》、《時間的傻姑娘》到《渣》,我通過詩歌、小說、電影劇本,也通過繪畫、影像和裝置,用將近八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階段的創作。正如唐明在〈時態悖論中的一副手銬──關於唐寅九自選詩的芻議和思辨〉一文所說──
「它們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創作體系,上述出版物所呈現的主題,可用癢、疼、渣、花園概言之;它們既是心靈的體驗也是一系列動作。其精神上的關聯甚至可以用一串連貫的動作來描述──癢,然後撓,然後引發疼痛,然後撕開、碎裂乃至於遍地成渣,然後重構,以花園安身立命。癢是長篇小說《一小片浮雲》的核心主題,也是唐寅九創作的出發點及初始概念,所對應的詞包括疏離、無端、荒謬、難受、叛逆、反抗。在唐寅九的文本中,撓與撕開乃是掙扎與反抗,癢有多深入,抗爭與疼痛也就有多深入。有意思的是撓與撕開都是自己與自己發生的事情,帶有明顯的自省性、自虐性與唯一性。這是唐寅九式的內省與批判,他將刀尖從社會、政治、歷史的外在層面指向了複雜而內省的自身,且刀刀見血,直見性命。」
在〈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文明週期〉一文中,我曾闡述過我對人類未來的基本判斷。我一直在觀察也一直在思考,但未能找到解決之道;《渣》當然也承擔不了指點迷津的重責。正如我在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
「他在某個夜晚寫下了這本新書的書名──《渣》,這個詞是這麼些年他和許多人生活的本質,是刻在墓碑上的字,是風中的斷裂聲,是紛亂的影子與世界的尖叫,是靈魂深處的怪力亂象……。他將繼續沿用具有宿命性質的毛文體,以斑剝牆壁上滿是漿糊味的大字報的文風,揭露黑暗世界的陰森與猥褻。」
至此我的寫作將暫停一段時間,我所關注的另一個重大主題──《花園》,將通過更多元、更具實驗性的視覺語言來呈現,它關乎我們是否能夠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安身立命。
我相信任何一種希望都將經由碎裂與消亡並在混亂與不確定性中產生。
唐寅九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寫於臺北
這是我寫得最糾結的一部小說,從二○一七年開始,斷斷續續寫了五年。二○一九、二○二○年幾乎不敢動筆。我曾一度以為寫不下去了,因為害怕,因為遲疑,也因為好多東西還看不明白;可它幾乎已經是一本我必須每天面對且無法趕走的書。害怕且猶豫要不要寫下去的根本原因在於我不斷在問:人,人性怎麼就變成這樣了?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寫道:「渣是這個時代最本質也最具普遍性與代表性的人類狀態。整個人類都碎了,遍地成渣,撿都撿不起來!……」我並不是最早更不是唯一發出這種警示的人,類似的句子在艾略特的詩中俯拾皆是。但問題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過,也沒人把渣當作一本書的書名,當作是最具普遍性與代表性的人類狀態。
寫這本書幾同於把自己的心剖開、切片然後觀察、自嘲、分析……,正如批評家唐明先生在評論我的另一篇小說時說的話:「它充滿了絞刑架下的詰責與拷問。」通過一顆小小的卻又無比複雜和滄桑的心,我試圖想完整地看一看人性到底有多黑暗、多骯髒,又有多變態、多分裂;我想要看清楚,看它到底碎到了怎樣的程度!渣,從來就不是一個形容詞,它不是一種比喻,不是我們在打比方、舉例子;它也不是一個名詞,雖然它是,首先是一種物理狀態,但顯然不止於此,它甚至不僅僅是一種精神與心理狀態。是的,它是一個動詞!放眼望去,滿世界都是它的動作與聲音。可怕的是,作為一個動詞,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讓它停下來的方法;因為它的主語已經喪失,高貴的主語令人痛心和絕望地不在了、缺失了。這個主語不只是你、我、他,也不只是我們、你們、他們。它不是某個個體、組織與國家,而是人,是人類!人不在了,人類正在空缺,這正是問題普遍存在和日益嚴重的原因。喪失主語的動詞是可怕的,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任何主體性力量可以管控它、制止它。所以,我怎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內心的恐懼,毅然決然地堅持寫下去呢?直到寫這篇後記時,我的身體變得如此僵硬,思緒卻又如此澎湃。
《渣》最早的出發點是猥瑣。我曾藉其中的一句話表達過我的初衷:「我所寫的那本書,它唯一的主題乃是猥瑣,我要寫盡一代知識分子的墮落。」猥瑣當然是渣最基本的構成因索。猥瑣,在我看來,乃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普遍、最深刻,也最致命的根性,它比阿Q精神要更廣泛也更深入地影響了我們的民族心理。阿Q精神不過是自欺與麻木,可有時候它甚至還勉強算得上是一種臨時的、局部的、管點小用的精神療法。可猥瑣卻徹底侵蝕了我們的人格與心靈。這個世界沒有哪個民族像我們這樣遍地猥瑣,它既是我們的近現代史,也是我們的當代史。如果不承認或者不敢面對這一點,我們的人格就將永遠也不會健全,我們的心靈也將永遠不會健康,我們將永遠走不出來,更不用說以善良、美好的步伐進入人類文明的殿堂。毫不誇張地說,只要猥瑣的人格還如此普遍地存在,則無論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斷無和諧與幸福可言,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文明世界的信任與尊重。
在近五年的寫作過程中,這個世界發生了太多的事情,渣在我心裡隨之也突破了猥瑣的主題邊界,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範疇。它當然還是一部寫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書,也是一部幾乎是萬箭穿心的、寫盡猥褻心靈的書。但是它的主題及指向已經令人悲傷地擴大到了整個人類。遍地成渣是人類的現狀,是人類最大的現實與危機。改變組織、社會乃至於國家容易,改變人格、人性與人心尤為困難。連接人心的各種主題、工具、價值觀和方法論幾乎全都斷裂了;我們藉此獲得榮耀、自信、團結與信任的力量幾乎全都瓦解了,那些曾經那麼強大的宗教力量、道德力量、美的力量、家族的力量、社會乃至於國家的力量正在全面瓦解。國家行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變得像小丑似的弱智、愚蠢、不美好、不可靠及不可信任。渣不僅遍及所有領域,也在否定、嘲笑乃至於消滅數千年業已形成的文明,它每天都在以各種方式嘲笑我們──看看吧,整個人類文明,包括令人驕傲的印度文明、古羅馬古希臘文明、華夏文明……,全都如此不堪。從某種意義上講,渣正在成為我們每天都身陷其中的咒語與厄運。如果沒有更大的勇氣與智慧,沒有更廣闊的視野與胸懷,沒有更多的愛、更徹底的改變,那麼我們的文明就真將不堪一擊。
從《赤腳狂奔》、《一小片浮雲》到《懸空的椅子》,從《一片海灘》、《時間的傻姑娘》到《渣》,我通過詩歌、小說、電影劇本,也通過繪畫、影像和裝置,用將近八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階段的創作。正如唐明在〈時態悖論中的一副手銬──關於唐寅九自選詩的芻議和思辨〉一文所說──
「它們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創作體系,上述出版物所呈現的主題,可用癢、疼、渣、花園概言之;它們既是心靈的體驗也是一系列動作。其精神上的關聯甚至可以用一串連貫的動作來描述──癢,然後撓,然後引發疼痛,然後撕開、碎裂乃至於遍地成渣,然後重構,以花園安身立命。癢是長篇小說《一小片浮雲》的核心主題,也是唐寅九創作的出發點及初始概念,所對應的詞包括疏離、無端、荒謬、難受、叛逆、反抗。在唐寅九的文本中,撓與撕開乃是掙扎與反抗,癢有多深入,抗爭與疼痛也就有多深入。有意思的是撓與撕開都是自己與自己發生的事情,帶有明顯的自省性、自虐性與唯一性。這是唐寅九式的內省與批判,他將刀尖從社會、政治、歷史的外在層面指向了複雜而內省的自身,且刀刀見血,直見性命。」
在〈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文明週期〉一文中,我曾闡述過我對人類未來的基本判斷。我一直在觀察也一直在思考,但未能找到解決之道;《渣》當然也承擔不了指點迷津的重責。正如我在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
「他在某個夜晚寫下了這本新書的書名──《渣》,這個詞是這麼些年他和許多人生活的本質,是刻在墓碑上的字,是風中的斷裂聲,是紛亂的影子與世界的尖叫,是靈魂深處的怪力亂象……。他將繼續沿用具有宿命性質的毛文體,以斑剝牆壁上滿是漿糊味的大字報的文風,揭露黑暗世界的陰森與猥褻。」
至此我的寫作將暫停一段時間,我所關注的另一個重大主題──《花園》,將通過更多元、更具實驗性的視覺語言來呈現,它關乎我們是否能夠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安身立命。
我相信任何一種希望都將經由碎裂與消亡並在混亂與不確定性中產生。
唐寅九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寫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