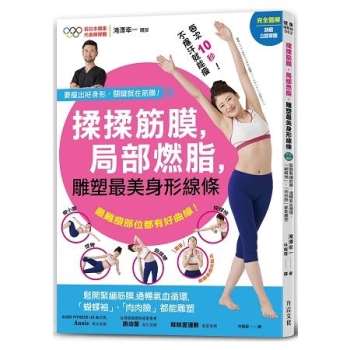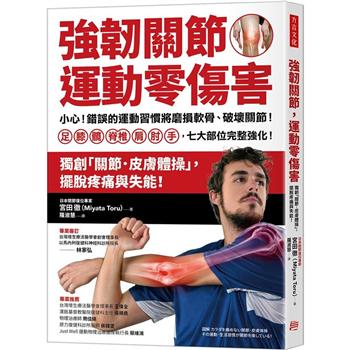§ 看交響樂的女人(節選)
人民大會堂。
馬麗直直地仰望著,舞臺上那個背對著她的小個子指揮,兩隻胳膊一夾一夾,同時用力一蹲。馬麗實在領略不出交響樂的妙處,雖然來時的路上,老房告訴她,票價六百,舞臺上的那個指揮,也是重金請過來,有國際外交的面子。「這場交響樂的門票,不是誰拿錢都可以買到的。」老房鄭重地說。
馬麗動了一下,這種直直的身姿,真的是很累。在她的正前方,還有一面一米見方的柱子,遮擋了馬麗的視線。馬麗只能左右地引頸著。
剛剛春天,這麼高穹頂的大會堂裡,還是讓人感到了燠熱。馬麗同時感到她的右臉,有老房目光的烘烤,更熱。老房在對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進行考察,她知道。
「你怎麼不看臺上?」馬麗放下脖子,問老房。老房是部隊的師級幹部,喪了妻。今天晚上,他和馬麗是第二次見面。總看我,不白瞎了門票,我臉上也沒長花。馬麗的內心分明是不滿。
「我喜歡多看看妳,臺上聽聽就行了。」師級幹部是南方人,他的帽簷兒壓得比平日低,臉黑頭小,這使他的腦袋看起來像一罐廣東小菜兒。「音樂會帶個耳朵就夠了,用不著看。」房師長說。今天他穿的是便服,便服的他沒有馬麗第一次見軍裝的師長威儀。穿便服,壓帽簷兒,拿自己當地下黨呢。馬麗又仰起了脖子。
舞臺上,指揮變化了一個姿勢,兩隻胳膊的用力改成一隻手的輕揚了,樂隊前,多了一位拉小提琴的男士。小提琴馬麗同樣不懂,但是她能聽出好聽,是那首耳熟能詳的〈梁祝〉,讓馬麗眼睛一亮的,是拉琴這個人,三七開式的自然鬈髮,黑白相間得體的禮服,適中的個子,不胖不瘦的身材,特別是男子拿弓的無名指上,戴著一枚亮晶晶的白金戒。白金戒本不稀奇,滿天下的男女,只要有倆錢兒,誰都可以戴。可是出現在這隻手上,這隻拉琴的手上,真是巧奪天工啊。指甲乾淨,手指勻稱,配合著那張抵琴的臉,美!美不勝收!這是誰家的兒子?哪個女人的丈夫?怎樣厚福的孩子的父親?馬麗的迷醉裡,帶著幾分豔羨和心酸。
馬麗的兒子也有這麼高了,也有這麼端正的五官,可是兒子跟他爸一樣,才過十八歲,吃喝嫖賭,坑蒙拐騙,放蕩的生活成了他的享樂。
馬麗左腿搭上了右腿,鱷魚嘴式的前鞋尖兒,抵在了前座椅的橫樑上,想到了自己灰心的生活,馬麗禁不住打了個疲憊的哈欠,意識到了旁邊有房師長,在考察她的房師長,她馬上伸手遮住了嘴,同時把哈欠變成了無聲的嘆息。
不看演出,總看我幹什麼呢。你是師長,你就有權力這麼看人吶。馬麗心裡非常不滿,也不舒服,可她還沒有勇氣糾正師長的放肆,索性不管他,再次仰起了臉,全神貫注看臺上。
「顴骨高,殺人不用刀」,馬麗和丈夫初識時,婆婆看她第一面,就給過兒子這樣的忠告。其實馬麗的正面還是挺好看的,高顴骨,顯出眼睛的凹陷,長睫毛,又密又彎,鼻子、嘴巴也都恰到好外,像有歐洲人的血統。「妳不是二毛兒吧?」很多人這樣問過她,馬麗是東北人,黑河,和俄羅斯接壤。在她們老家,二毛、三毛確實很多。
咦,你怎麼還不看演出呢?馬麗的表情似乎很天真,眼睛也睜得很明亮,她真希望通過她的問,友好的問,師級幹部能把臉端正過去,而不是行家相看幾歲牙口的牲口一樣死盯著她看。
不耽誤,不耽誤。老房衝馬麗擺擺手,看妳的吧,看妳的吧,哪兒都不耽誤。
馬麗的右腿已經麻了,又把左腿當成了支架,鱷魚嘴鞋尖兒太長了,無法不抵到前椅的橫樑上。看吧,喜歡看你就看吧,老東西,真是把自己當皇上了,選妃呢,滿天下的女人不夠你挑挑揀揀的了,挑吧,選吧,別搞花了眼。老娘也不是十八歲的小姑娘,還怕你看嘛。馬麗昂起了頭,昂得很有技巧,現在的馬麗側面也不怕看了,她做了美容。馬麗心目中的美人形象是那個姓靳的華裔女商人,在這一點上,小艾跟她正相反。小艾說,那個整容整得一隻眼珠兒都要掉下來的老女人,那麼醜,說話那麼做作,她還成了美的代言人,真是笑話。她哪兒美呀,我看她就像個老妖精。
小艾反對是反對,這並不影響她跟馬麗的交情。馬麗屬兔,小艾屬羊,她倆都信命,命裡說,屬羊的跟屬兔的在一起,吉祥,小艾就不厭其煩地找馬麗,馬麗呢,更相信都是食草動物,羊對兔沒有一點危害,馬麗幾乎只要有空兒就跟小艾摽在一起。讓馬麗疑惑的是,同樣是食草的,人家小艾的命怎麼那麼好呢,丈夫是副師級,長相也不錯,把小艾從東北農村,一步一步,帶到了北京。北京,首都啊。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土豆也叫馬鈴薯︰曹明霞短篇小說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中文書 |
$ 299 |
小說 |
$ 306 |
現代小說 |
$ 306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土豆也叫馬鈴薯︰曹明霞短篇小說集
「棋盤上已蜘蛛網一樣一圈圈占滿了,五分之四的棋子進去了,她也沒能致勝。」
中國女性文學獎得主.曹明霞爽利的筆下,讓我們看見潛進電影院的二胖如何和看門人躲藏捉拿;看交響樂的馬麗如何與相親對象交鋒;四枝兒看著一起離鄉進城工作的兔唇兒為了男人與自己漸行漸遠;還有李校長家裡,冬梅手上永遠削不完的馬鈴薯皮……
或許人生就像一盤五子棋,機關算盡也未必能贏。在各人翻來覆去的盤算中,曹明霞還是帶給我們一線希望──為愛情蹚過了千山萬水的漢族爺爺、滿族奶奶,在沒邊沒沿的黑土地上經營起粉房,粉房開張那天爆竹聲聲,同一天晚上點起了花燭,然後,就有了父親,有了你我。生生不息。
作者簡介:
曹明霞
中國大陸當代女作家。
祖籍雲南,生於黑龍江鐵驪,九○年代中期到河北工作。職業戲曲編劇,業餘文學創作。
著有長篇小說《日落呼蘭》、《青山不墨千秋畫》(與人合著)、《看烟花燦爛》等,中短篇作品集《這個女人不尋常》、《婚姻往事》。曾獲梁斌長篇小說一等獎、中國女性文學獎、河北文藝振興獎等。另有中短篇小說〈士別三日〉、〈夜晚的咖啡〉、〈花開兩朵〉、〈一夕漁樵話〉等被多種選本選載。小劇本《晚餐》、《金剛》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第六頻道(電影頻道)播出。
章節試閱
§ 看交響樂的女人(節選)
人民大會堂。
馬麗直直地仰望著,舞臺上那個背對著她的小個子指揮,兩隻胳膊一夾一夾,同時用力一蹲。馬麗實在領略不出交響樂的妙處,雖然來時的路上,老房告訴她,票價六百,舞臺上的那個指揮,也是重金請過來,有國際外交的面子。「這場交響樂的門票,不是誰拿錢都可以買到的。」老房鄭重地說。
馬麗動了一下,這種直直的身姿,真的是很累。在她的正前方,還有一面一米見方的柱子,遮擋了馬麗的視線。馬麗只能左右地引頸著。
剛剛春天,這麼高穹頂的大會堂裡,還是讓人感到了燠熱。馬麗同時感到她...
人民大會堂。
馬麗直直地仰望著,舞臺上那個背對著她的小個子指揮,兩隻胳膊一夾一夾,同時用力一蹲。馬麗實在領略不出交響樂的妙處,雖然來時的路上,老房告訴她,票價六百,舞臺上的那個指揮,也是重金請過來,有國際外交的面子。「這場交響樂的門票,不是誰拿錢都可以買到的。」老房鄭重地說。
馬麗動了一下,這種直直的身姿,真的是很累。在她的正前方,還有一面一米見方的柱子,遮擋了馬麗的視線。馬麗只能左右地引頸著。
剛剛春天,這麼高穹頂的大會堂裡,還是讓人感到了燠熱。馬麗同時感到她...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臺灣版自序.這個世界會好嗎?
很小的時候,鄰居華家男人鷹鼻深目,嗜酒。酒後不是掂菜刀就是拎斧頭,要劈女人。記憶中他家男孩光著腳衝進我家,有時是早晨有時是半夜,冰天雪地,嗓音沙啞劈裂:「我爸要殺我媽了!」
──那份驚恐,也一次次嚇裂了我的心臟。長大後極怕驚嚇,極度膽小,應是那時養成的。
有一天,大家還沒吃晚飯,街上傳來呼叫──他媽媽在前面跑,他爸拎著劈柴的大斧後面追。一街人都跑出來看,拉架,勸說,那男人見女人加速了,竟輪圓胳膊投標槍一樣把斧頭擲了出去,好在沒剁著人。再後來的有一天,中午放學時...
很小的時候,鄰居華家男人鷹鼻深目,嗜酒。酒後不是掂菜刀就是拎斧頭,要劈女人。記憶中他家男孩光著腳衝進我家,有時是早晨有時是半夜,冰天雪地,嗓音沙啞劈裂:「我爸要殺我媽了!」
──那份驚恐,也一次次嚇裂了我的心臟。長大後極怕驚嚇,極度膽小,應是那時養成的。
有一天,大家還沒吃晚飯,街上傳來呼叫──他媽媽在前面跑,他爸拎著劈柴的大斧後面追。一街人都跑出來看,拉架,勸說,那男人見女人加速了,竟輪圓胳膊投標槍一樣把斧頭擲了出去,好在沒剁著人。再後來的有一天,中午放學時...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貓空─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出版緣起
臺灣版自序.這個世界會好嗎?/曹明霞
看交響樂的女人
事業單位
老孫又去讀博士
電影院
花燭
一盤五子棋
兩個鄉下姑娘
情人是個保潔工
母親和牆角的聖誕老頭兒
土豆也叫馬鈴薯
邊界
寂寞沙洲冷
臺灣版自序.這個世界會好嗎?/曹明霞
看交響樂的女人
事業單位
老孫又去讀博士
電影院
花燭
一盤五子棋
兩個鄉下姑娘
情人是個保潔工
母親和牆角的聖誕老頭兒
土豆也叫馬鈴薯
邊界
寂寞沙洲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