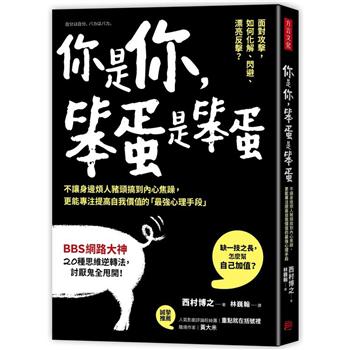推薦序
花甲少女魔時說
文字創作者 妍音
「我來自何方,像一顆塵土,有誰看出我的脆弱?
我來自何方,我情歸何處,誰在下一刻呼喚我?」(感恩的心)──詞:陳樂融 曲:陳志遠
《魔時少年》讀罷掩卷瞬間,這首歌的旋律自然跳進腦門,我來自何處?何時來到?浩瀚宇宙之下微不足道,一粒塵一粒沙一顆土一道煙,最終又會如何流轉?流轉途中曾經或將會遇見什麼人,看到什麼景,發生什麼事?
時間流水一般,或輕淺或湍急或奔流或激越,打小一路走來,彷彿仍在路途中瀏覽目不暇給的風光,不曾想回眸卻是倏忽已過萬重山。可腳下仍持續踩踏的步履,究竟會迎向怎樣的風景?能否回頭再去尋某一段美麗?或是牢牢安放心間便是了。
隨著《魔時少年》潘克羅的路徑,走了大半座島嶼,這座島嶼的東部,始自蘭陽平原,一路推展往南而去,迷宮森林、深邃洋流、斯米拉望少年少女出現又消失。走在如夢如幻未可知之境,彷彿走在是神話是傳說是歷史的路上,路上會不會也有我的前生?
潘克羅告訴機器人,我們要去未來,未來是很久以前的過去(本書第二十一章)。而過去的世界應當是很美好的(本書第二十九章),我深深相信潘克羅這個想法,過去超過半世紀我的記憶,童年生活再困頓,社會氛圍再壓抑,總體經濟再不活絡;生活仍然充滿希望,社會也朝前轉動進化,小日子裡有小確幸,美好人事物無需巨大。
我的這一世,生長在島嶼西部的盆地,盆地上有河川,河川最後流入黑水溝。多少年總在鐵公路上由著火車汽車競逐,彼時窗外景象跑馬一般快速,我曾巴巴望著那一片閃電飛過的遼闊山林,猜測著大肚王國在哪裡?
臺灣中部曾經由拍瀑拉族、巴則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與巴布薩族所建立的跨部落王國,鼎盛時期領域範圍還往南大約推至鹿港,北則可延伸至桃園以南,幾經更迭融合兼併,後來範圍縮至大肚溪上中下游流域。
這些是陳年歷史,是人們早已遺忘殆盡的族群融合,而我也和許多島上住民一樣,只是落籍島上一隅食用島上物產翻讀有限資料,卻不曾深入書冊之後的綿長源流。
曾經的中部跨部落王國各族從何而來?後來又如何了?一無所知。
我哪裡有過見識?生長在西部鄙陋無知,竟以管窺天,以為天地就所知的這麼大。但其實天地無限大,尤其我所在的這座島嶼東部,緊鄰著世界第一大洋,大洋深處有海溝,海嘯湧起,潮來潮去,湧上岩石羅列的海岸,夾帶來什麼消息,或夾帶了什麼人?
潘克羅一路懷想著太祖輩的日記紀錄,第二十四章兩人相遇時,身為太叔公祖的潘德諾真吃驚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的過去來到我的現在,或是現在的我撞進過去你的世界?
誰說得清。
什麼是先來後到?
先來後到,究竟以哪個時間點為基準?
「時間無時無刻變動著,每一天所遇見的人、看見的風景與遭遇的獵物,都在成為不一樣的人事物。」(本書第七章)
遠古時代,南島不同族群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遷徙,經過大洪水逃難,經過海上漂流種種歷險,來到了島嶼東部,經過一次又一次離散聚合,一次又一次或對立仇視或團結合作,語言飲食生活文化便也漸次融合而相似或相同了。無論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太魯閣族或阿美族、泰雅族各社,想來也和島嶼西部曾經的跨部落王國的族群一樣,在時間之流沖刷之下,存在空間被動的異動後,再分不清誰是誰了。
花甲之後,總感覺時間有咒語,那咒語直令時間轉動更加快速,明明才是春暖花開時候,一眨眼卻已然秋深。我也與烏帕一樣,心有餘而力不足(本書第十六章),可我又沒能像烏帕那樣擁有與天神溝通的法力,能清楚說出:「這裡不只有一個時間。」
或許,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可融合一處。
所以,夜寐夢裡,先人來訪友人同遊娃娃後輩也談笑風生了。
本書最後,潘克羅隨著他的太叔公祖潘德諾跟著彩虹光束走,想像著自己出生時祖父母懷抱他的情景。他也看見自己長大後發現由樹皮記錄的傳說資料,加以謄寫資料成為傳家之寶,只為能讓後代子孫真正瞭解祖先的故事。
潘克羅美好的記憶裡,有著和祖父划著帆船在太平洋上航行的畫面,他還記得祖父曾經對那時年幼的他說過:「我們在此相遇,總有一天也會在某個世界相逢。」
一顆塵土雖微脆,因有同伴而堅實,一路行來便是獨一無二的生命歷程,即使在光陰洪流裡,已沖刷至末流。
但,我願相信時間有魔力,輪轉再輪轉,花甲婦非少女,也能很少女。
必得感恩哪,因為這時這地那時那處,而長養了不斷流轉的你我他。他是誰或許無關緊要,但都是歷史長河裡的一個點,就因有了這個點,你我方能恰如其分演繹個人生命,在時間裡走著,悠然自得。
自序
關於時間消失的很久很久以後
時間是否曾經停止在什麼樣的地方,是否也曾快速轉動。
將近快十年前,拜訪蘭嶼和綠島,一路由宜蘭、花蓮至臺東,嘩啦啦的海浪聲不知不覺安靜了下來,站在島嶼的高處,聆聽波濤的聲響,廣漠的大海邊緣盡是小心翼翼迂迴曲折在岩岸間,浪一個一個躡手躡腳爬上了岩石,又悄悄落回海面。
那樣的大洋看起來像面鏡子,時間彷彿都慢下。
所有的動靜也都跟著慢下。
沒多久,傍晚的金光退去,先前墨黑下天色的遠方海面,開始閃爍一道道白光,像由雲朵往下竄出的樹根,充滿巨大能量的樹根,以極快的速度鑽動,消失在不遠處島嶼的地平線,卻什麼聲音也沒聽見。明明能清楚看見那不遠處的小嶼,閃電直直落下,無論耳朵怎麼仔細撐開去聽,那白色夾帶著紫色和藍色光束一同落下的閃電,怎麼也沒響起雷聲。
在遠離路燈下的注視者,那一方黑暗和那遠方無聲的閃電,都彷彿一同與遠處烤肉攤店的時空產生了隔斷。
烤肉店裡也該有人聲鼎沸的景象,注視者什麼也沒聽見,無論是雷還是人,時間在注視者的身旁慢下,或者快速轉動,以致於失去了重要細節的傳遞,聲音便是其中之一。
無聲平靜的海面就像是那樣的時空,被快速轉動著,或者過於慢速播放,以致於失去了海浪的變化,海水接觸陸地時所湧起的泡沫,泡沫下那些夾帶著無數微生物、原始生命體和古老有機與無機物體一同落下,再度竄回海裡的那諸多生態細節,都消失了,只剩下那海水與陸地邊緣,彼此戒慎恐懼的維持著一個寂靜的輕微接觸,旋即又爬回自己的地域,維護一個介面的平衡。
就那麼看著平靜卻近似停滯的海,感受著另一面驚濤駭浪卻似限制在一方土地面前的海,也經歷過滔天巨浪段差好幾公尺的海域駐足在海的某處,海慢下與快速流動間,分割起無數時空……也有那愈靠近陸地,海的腳步因受限於沙土或是岩石,而激起浪花的海。在那無數時空、海域與小島間生存的南島語族,以船為腳,大步邁向海洋的中心,彷彿穿越無數時間場域,使航行於其中的人,快速轉動著,或被慢速播放,前進著,也彷彿停滯著。
一次又一次,在無數回返的一生裡,離開原本生活的地方,前往捕魚的地區,去到彼此交易的地域,回返能夠駐足之地。反覆在那曾發生過、持續發生、即將發生的時間軸裡,穿越那些彼此相鄰,因為地形而有所差異的海域,去經歷起不知為何漂泊的命運。彷彿那大洋裡的島是船,從一艘船到另一艘船,由某處海域到達另一處海域,靜止在相同的命運——回返祖先居住過的島,去到另一座島,然後成為子孫所說的祖先地域。
那祖先曾走過的路,都遺留在原鄉傳說,試圖傳達給後裔,關於家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家曾經在何處,家對於祖先的情感,以及家的延續……洪水分隔遠古記憶,天梯能夠溝通母親般的神靈,原鄉究竟位於何方,神聖的樹維繫著聚落發展,植物具有神奇的驅邪祈福力量,千萬不能用手指著那天空中奇異的光,無論是日月星辰或是彩虹。傳說直跟著船漂,由一個家到另一個家。
海流在大洋裡,悄悄走過那些傳說成為一個圓,時間在海水裡,也慢慢畫成一個圓,那樣的圓重現再重現,生活裡每一分每一秒的記憶,無論是在何時何方,遇見什麼樣的故事,那感到心痛的片刻、心碎時分、幸福的瞬間、快樂的、悲傷的……終於明瞭的那一刻,都曾經已然在祖父母的床邊故事中被提起,在後來的人生所經驗,以至於在某天突然對某些畫面感到熟悉的那一瞬,安慰著,支持著,嘗試聯繫著,祖先想告訴孩子們的很久很久以前。
二○二二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