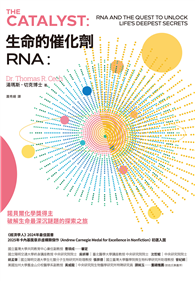傳說無臉的野篦坊能幻化人形,將模仿對象取而代之!
在一場獎金高達十萬美元的說故事大賽中,究竟誰是人?誰是妖?而誰又被取代了?所有線索,都藏在五則細思極恐的故事裡……
為了驅除身上的詛咒,秀姸打算跟隨姐姐的足跡,前赴高野山伊邪那神社,但就在出發前,收到一封匿名信函,邀請她參加一場五人夜話的遊戲,信中透漏尚有其他破除詛咒的方法;好友昕涵也是獲邀者之一,而邀請人竟是五年前突然失蹤的朋友孫楚琳。
另一方面,原本約了秀姸燭光晚餐的家彥,突然遭到沒有臉孔的女子襲擊,危急之際,被一名神祕少女救下,這位言行舉止優雅但飄忽的少女,告訴他秀姸與昕涵將遭遇險境,只要願意替她找一把玉造的梳子,就協助家彥救人。這名少女到底是敵還是友?
此刻,位在山頂名為「聽櫛亭」的大宅裡,聚集了五位參賽者──調查朋友死因的小宋、打算摧毀不祥之物的蔡老頭、計畫除掉野篦坊的秦陽虹、思念牽掛之人的韓慕湘與想救出姊姊的孫楚琳,他們各懷鬼胎,開始了說故事大賽。究竟這場比賽背後有什麼陰謀?秀姸透過詛咒能力,也看見了每個人的祕密,發現大家並不如表面上單純……更糟的是,野篦坊就混入其中!
繼《黑塚之絆》後,「詛咒少女秀姸」系列再起
香港怪奇小說家金亮,結合恐怖&推理元素,打造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
本書特色
★香港怪奇小說家金亮,結合恐怖&推理元素,打造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
★能夠幻化人形的妖怪野篦坊混入比賽中,秀姸能否透過詛咒能力揪出幕後黑手?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野篦坊之櫛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推理/驚悚小說 |
$ 334 |
驚悚/懸疑小說 |
$ 342 |
華文奇幻/科幻小說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野篦坊之櫛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金亮
香港作家、媒體工作者,工作就是寫寫寫,興趣也是寫寫寫,熱愛推理、奇幻及傳說故事,認為角色刻劃及劇情佈局是一本小說不可或缺的兩大元素,缺一不可,期望能將兩者結合,寫出角色鮮明、懸念巧設、佈局精妙的小說,令讀者每次翻開書頁都忍不住大喊一聲:one more page!
作家專頁
www.facebook.com/writerkris/
金亮
香港作家、媒體工作者,工作就是寫寫寫,興趣也是寫寫寫,熱愛推理、奇幻及傳說故事,認為角色刻劃及劇情佈局是一本小說不可或缺的兩大元素,缺一不可,期望能將兩者結合,寫出角色鮮明、懸念巧設、佈局精妙的小說,令讀者每次翻開書頁都忍不住大喊一聲:one more page!
作家專頁
www.facebook.com/writerkris/
序
序
我在前年開始執筆撰寫這個故事,本以為一年內便可完成,奈何中途身體再次不適,停筆大半年養病,待重新寫作已是一年後的事,之後再因公事和家事拖拖拉拉,結果一拖兩年,還好仍能如願出版,總算沒有白費工夫。
今次故事與之前相比,幻想性更強,世界觀更大,更加天馬行空,出場人物也是最多的,這是我第一次嘗試這類幻想與現實,真假交錯的題材,虛虛實實,夢裡夢外,我自己覺得挺好玩的,希望大家也喜歡。
《詛咒少女秀姸》系列至今已完成五部長篇小說,前後跨度五年,平均計算,也是每年一本吧!雖然這個系列故事尚未完結,腦海中仍有不少詭譎劇情和人物發展,想寫入這個特殊的世界觀中,不過回心一想,自己寫了五年,只寫了一個系列,作品類型似乎不夠多元化,趁這個機會停一停,嘗試一下其他類別的小說,或者寫些短篇作品,也不失為一個好嘗試。
再一次感謝秀威資訊,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信任,感謝責任編輯陳彥儒,幫我完成整個出版流程,亦感激每一位支持我的讀者,我會繼續努力,寫出更多作品。
金亮
二○二二年 冬
我在前年開始執筆撰寫這個故事,本以為一年內便可完成,奈何中途身體再次不適,停筆大半年養病,待重新寫作已是一年後的事,之後再因公事和家事拖拖拉拉,結果一拖兩年,還好仍能如願出版,總算沒有白費工夫。
今次故事與之前相比,幻想性更強,世界觀更大,更加天馬行空,出場人物也是最多的,這是我第一次嘗試這類幻想與現實,真假交錯的題材,虛虛實實,夢裡夢外,我自己覺得挺好玩的,希望大家也喜歡。
《詛咒少女秀姸》系列至今已完成五部長篇小說,前後跨度五年,平均計算,也是每年一本吧!雖然這個系列故事尚未完結,腦海中仍有不少詭譎劇情和人物發展,想寫入這個特殊的世界觀中,不過回心一想,自己寫了五年,只寫了一個系列,作品類型似乎不夠多元化,趁這個機會停一停,嘗試一下其他類別的小說,或者寫些短篇作品,也不失為一個好嘗試。
再一次感謝秀威資訊,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信任,感謝責任編輯陳彥儒,幫我完成整個出版流程,亦感激每一位支持我的讀者,我會繼續努力,寫出更多作品。
金亮
二○二二年 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