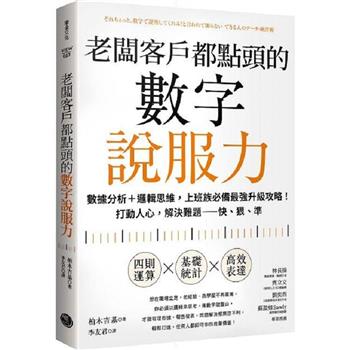〈序曲 初心〉
陽光普照的天氣,我端著熱咖啡行色匆匆走在醫院大廳。我是林唯樂,從大學畢業後,就進入這家醫學中心工作。經過五年的護理師臨床試煉,因緣際會下接受了專科護理師的訓練。到現在,已擔任專科護理師這份工作屆滿十年。
目前我在婦癌病房中工作,雖然介紹這麼多,想必你們對於專科護理師這個名詞還是有點陌生,就如同未曾到過醫院的民眾往往不解:專科護理師跟護理師有什麼不同?其實,說穿了,我們也是提供健康服務的一群人。醫院裡不只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還有很多的醫事人員一同為大家提供照顧,最終目的都是希望病人可以康復出院。然而,往往有時候事與願違。有些疾病與病患,總是令人頭痛不已。
一路走來遇到許多人與事,有時靜心坐下想想,即便人生中有許多起伏與大起大落,但它們只在有限的生命中占據極少的部分。
病人總說我是他們生命中的貴人,這句話似乎很輕,但卻沉重壓在我的心頭。當初決定進入護理這條路的時候,曾未想過能如此榮幸變成某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能持續秉持初心,盡全力照顧好每位病患,或許就是這份熱情感染了病人,也讓我有機會記錄下,她們人生中獨特的經歷。
準備好了嗎?讓我把這些美麗又滄桑的故事,向你們一一道來。
〈第二章 異鄉悲夢〉(節選)
外籍移工的引入大約開始於八○年代,從漁業、製造業、家庭幫傭到看護工,這群離鄉背井的人們,為台灣的就業市場投入許多勞力。雇用外籍移工必須提出相關文件申請,政府審核通過後才可雇用,並採取配額管制。而移工一次來台只有三年的居留時間,之後可以展延一次,至多六年為限。另外,這段居留期間無法自由轉換契約並更換雇主,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才能例外放行。
娃蒂卡是首度來台,而且剛剛滿四個月而已,尚未熟悉台灣這份新的工作,就因身體不適而無法繼續。
我大約猜到仲介想要說什麼,不外乎想問娃蒂卡到底是什麼疾病?治療過程會不會很麻煩?會不會花費很多錢?是否有需要自費的項目?
其實依照健保給付來治療疾病,已經綽綽有餘,絲毫不用擔心需要自費負擔其他項目。
但是,在我進入病室前的這些假設,都似乎太小看娃蒂卡的問題,我沒料到接踵而來是場不小的風暴。
我走入病室,望著床上的病患,娃蒂卡皮膚黝黑且身形瘦小,只見她躺臥在病床臉上還帶著兩行淚水。
「妳好,我是專科護理師林唯樂,妳可以叫我樂樂。」我對床旁坐著的一位中年女性自我介紹著,「請問是妳要找我嗎?」
「妳好。」中年女子抬頭望著我然後說道:「我是娃蒂卡的仲介,我姓歐。」
我聽出了仲介的華語中帶著點口音,讓人明顯感受到她應該不是台灣人。
「歐小姐,請問妳想了解些什麼?」我望著她好奇問道:「娃蒂卡沒有家人在台灣嗎?」
「來台灣工作的勞工怎麼可能會有家人跟著來,」歐小姐的話中帶著些許鄙視,「我是想問妳,如果我們要辦出院,是不是立刻就可以離開?」
「原則上來說,林醫師應該不會批准娃蒂卡辦理出院,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她的病是癌症,接下來需要積極治療。」
我的話讓歐小姐輕輕地挑了挑眉毛,跟著她就對著娃蒂卡說著我聽不懂的話,我猜那應該是印尼話或是當地的家鄉話。
只見她們妳一言我一語,我雖然聽不懂她們話裡的意思是什麼,但從歐小姐的語氣中,不難察覺出她正在責罵娃蒂卡。
娃蒂卡被罵得淚眼汪汪,跟著雙手合十地哀求她,但是歐小姐的態度卻變得更兇悍。
她們的話語讓我有點頭痛,但也好奇這位歐小姐到底想跟我說什麼?她又想知道什麼?
於是我開口打斷他們的談話,「歐小姐,妳請我過來到底想知道什麼?有我能幫上妳們的地方嗎?」
「哎,還真是麻煩。」歐小姐轉頭對我說:「娃蒂卡才剛來台灣四個月,正在熟悉環境跟學習怎麼好好照顧病人,偏偏就遇上這種事。如果她的雇主買張機票給她,讓她回去印尼,然後再重新申請一個新看護就沒事了。偏偏她的雇主不願意出這個錢。」
「送回印尼?」我驚訝地望著她,他們怎麼能把移工的命視如草芥呢?
我詫異道,「可是娃蒂卡需要接受治療,她得的病可不是小感冒,是癌症呀。癌症妳懂嗎?那是惡性腫瘤,如果不治療可是會死人的。」
「林小姐,我的華語沒有那麼爛,我當然知道癌症不治療會死,但我們是做生意的,可不是慈善事業。」歐小姐覺得我似乎看不起她,於是乎就對我說:「沒錯啦,我也是印尼人,可是我嫁給我老公已經十五年了,也拿到台灣身分證了。也因為這樣,我才能幫老公一起管理仲介印尼勞工公司。」
歐小姐一派輕鬆地說道:「況且我是印尼雅加達人,跟他們那些從鄉下來打工的人,那可是不一樣。」
這還真叫我大開眼界,原來印尼人歸化為台灣籍以後,就能把家鄉澈底忘記。
「歐小姐,如果娃蒂卡的雇主不出機票錢,基於同胞情誼上,妳來幫忙出這一份錢,應該不算過分吧。」我覺得如果今天我是歐小姐,在異鄉見了同胞有難,能幫多少就幫多少,於是乎我把難題丟回給她。
「什麼同胞?」歐小姐似乎在中文造詣上尚須多多研習,居然聽不懂同胞是什麼意思,不過她倒是聽懂建議出錢買機票這件事情,只見她不留情面且大聲地說道:「我為什麼要幫她買機票?她在台灣工作這幾個月都有薪水,只是她通通把錢匯回印尼,我叫她打電話給她老公,趕緊把錢匯回來給她買機票。」
我覺得無論哪國的生意人,算盤都打得很精。也是啦,說到底整件事情,花錢就可以搞定一切,但是唯一的麻煩就是娃蒂卡沒有錢。
「小姐,小姐。」娃蒂卡突然拉住我的手,然後用彆腳的中文說:「我沒有錢,我老公不會理我。我沒有錢。」
歐小姐生氣地拉開娃蒂卡的手,然後又開始用惡狠狠的語氣,對著娃蒂卡說起印尼話。只見娃蒂卡又開始眼淚掉個沒完。
我覺得眼下又是僵局,而且很難解決。仲介想了解的並不是娃蒂卡的病有多嚴重,只是想知道她們是否隨時可以出院。
「歐小姐,我會把妳的需要跟請求跟主治醫師說,至於她是否會同意讓妳們出院,我就不知道了。」這時候我還是先溜至上。
「沒關係。」歐小姐轉頭對我說:「反正我還要跟她印尼的家人談判,既然知道她是癌症就更好辦了,家人總不會冷眼看她死在異鄉吧。」
我的老天鵝啊,歐小姐還真是嚇到我了。她居然想好這般陰毒的招數,我看娃蒂卡的家人如果不聽話乖乖地把錢匯回來台灣買機票,那娃蒂卡未來的處境當真是堪慮。
走出病房後的我心裡很沉重,不知道為什麼,娃蒂卡哭泣的淚眼,讓我產生了同情心。我慢慢走回護理站,坐在電腦前面,一整個思緒陷入混亂。
移工們遠走他鄉,為的就是希望賺錢以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態,偏偏在剛剛抵達異鄉的時刻被診斷出癌症。
一般來說這些移工要申請到台灣賺錢,並沒有那麼容易。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印尼移工在家鄉要先經由仲介公司訓練及媒合,必須先行付出一筆不少的仲介費,這筆費用大約是十四到十六萬,他們多半必須在當地辦理貸款來支付這筆錢,所以第一年的薪水大都匯回家中還款。而一般會外出工作賺錢的,大都來自貧窮的鄉下。仲介公司也喜歡到窮一點的鄉鎮去招募移工,因為貧窮才有賺錢需求,而且鄉下大多純樸,普遍認為會比較聽話。
娃蒂卡應該是家裡經濟狀況不好,所以才來台灣工作,卻在此關鍵時刻被診斷出罹患癌症。
葉心走到我身邊,看我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好奇問道:「樂樂姊,妳在想什麼呀?」
「一張去印尼的機票,大概要多少錢?」
葉心不懂我的意思,「樂樂姊,妳要去印尼玩嗎?」
「沒有,我只是好奇買一張去印尼的機票會不會很貴?」我望著葉心,「應該一萬多就有了吧?」
「大概吧,這方面我不是很懂。因為我都跟團出國旅遊。」葉心吐吐舌頭,「我不像妳,買張機票後背著背包就出國去玩。」
如果是一萬多塊,是否可以找邱曉娟來幫忙?
眼下我又把主意打到社工師身上,畢竟我每次遇到病患沒錢,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她。
不過我怎麼也沒想到會在邱曉娟那邊碰了軟釘子。她告訴我,如果病患住院期間沒錢吃飯,或是缺點尿布衛生紙,她還可以幫忙用善心人士小額捐款協助來度過難關。但是買機票這件事就比較難辦了。
邱曉娟也很疑惑,娃蒂卡是合法移工又不是逃逸移工,正常來說如果要回印尼,必須由雇主或是仲介負責購買返國機票。怎麼會要她自行負責?
那接下來又該怎麼辦?趁著林怡津查房的時候,我跟她提起這件事情,沒想到林怡津的反應讓我感到意外。
「不買機票就留下來治療。」林怡津一臉泰然對我笑著說:「樂樂,如果娃蒂卡留下來,我們不是可以好好治療疾病,總好過她回印尼等死吧。」
對耶,我怎麼沒有想到,如果沒人出機票錢,娃蒂卡就得留下來治療,這樣對她來說反而是比較好的選項。
「通常這種外籍移工,在家鄉屬於比較低下階層,如果回印尼治療癌症必定要花很多錢。」林怡津一派輕鬆說道:「她留下來用台灣的健保治療疾病,癌症可以申請重大傷病,無論是手術、化學治療等等,通通健保來負擔。」她拍拍我的肩膀說:「樂樂,我們就好好幫娃蒂卡治病,仲介那邊就不用想太多。」
「說起那位仲介,我還真是生氣。」我忍不住跟林怡津抱怨起來,「她告訴我她是印尼人,只是運氣好嫁給台灣人,還拿到台灣身分證。那天我去病房解釋病情的時候,她對娃蒂卡凶狠的樣子,真把自己當成是台灣人,忘記自己當初也是從印尼出來的。」
「在商言商,她眼底只有賺錢一事而已。眼下娃蒂卡對她來說,是個燙手山芋。因為她占著移工的缺,卻無法工作賺錢。雇主那邊也不願意支付這筆機票錢,她們自然認為娃蒂卡要自己出錢買機票回去。」林怡津笑著說:「沒關係,既然沒人願意送她走,我們就好好安排後續的治療計畫。」
林怡津這麼有自信,我也覺得這樣處理很好,於是我們預備到病房裡告知她們目前的情況。
剛剛走進娃蒂卡的病房,就聽見有人大聲責罵的聲音,嘰哩咕嚕一大串讓人聽不懂的話語又伴隨哭泣聲,歐小姐正在責罵娃蒂卡。
「樂樂,我應該沒走錯吧?」林怡津有點疑惑地望著我,「這是什麼情況……」
「印尼話。」我壓低聲音說:「仲介又在威脅病人了。」
林怡津臉上閃過一抹不悅之色,可能我剛剛說的事情影響了她。讓她跟我一樣,對這位惡狠狠的仲介沒有好印象。只見她刻意咳了一聲又清清喉嚨,我在一旁偷偷忍著笑,心想不知道林怡津又要出什麼怪招?
林怡津伸手把床簾拉開後走了過去,她對著床上的娃蒂卡說道:「妳就是娃蒂卡嗎?」
娃蒂卡點點頭,臉上依舊掛著兩行清淚。
我站在林怡津身旁,憐憫之感自心底油然而生,怎麼每次見到娃蒂卡,她都可憐兮兮地正在被仲介逼著吐錢出來。
「我是林醫師,是妳的主治醫師。」
「林醫師,妳好。」一旁的歐小姐主動站起來,笑吟吟地說道:「我是她的仲介,我姓歐。」
哇賽,歐小姐的嘴臉變得還真快,剛剛還惡狠狠地開罵,現在見到主治醫師,立刻就變了張臉。想必她先生的老家在四川,她居然學會變臉這項技藝。
「歐小姐妳好。」林怡津笑臉迎人:「我聽樂樂說,妳們不想治療,想要辦理出院?」
「是的,林醫師,首先我得先表明我的立場,娃蒂卡來台灣是要工作,既然現在她生病沒辦法繼續工作賺錢,自然就得回印尼去。」歐小姐望著林怡津說道:「現在比較麻煩的是雇主不願意出這筆機票錢,所以我得跟她印尼的家人溝通,讓他們把錢匯回來買張機票給娃蒂卡,然後讓她回家。」
「歐小姐,妳確定娃蒂卡不接受治療嗎?」林怡津轉頭望著病人說:「妳不治療會死掉,我建議妳留在台灣好好接受治療。」
娃蒂卡沒有聽懂林怡津的話,只見她又開始哭著說:「我沒有錢,我的家人沒有錢,我不知道怎麼辦。」
林怡津大約猜到娃蒂卡的中文沒有很好,所以不懂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於是轉頭對歐小姐說:「來來來,妳來幫忙翻譯一下。」
歐小姐帶著警戒心望著我們,「妳們到底想要跟娃蒂卡說什麼?妳們要搞清楚,她沒有權力決定任何事情,有任何問題就告訴我,她的事情都由我決定。」
林怡津幾乎爆炸地說道:「得癌症的又不是妳,況且妳不是娃蒂卡的家人,妳憑什麼做決定?我告訴妳,台灣是講人權的地方。我是她的主治醫師,自然只跟她解釋病情,至於要不要治療都由病人自己決定,並不是妳這個仲介說了算。」
林怡津的話讓歐小姐七竅生煙,她悻悻然地說道:「好呀,那妳自己想辦法跟她說清楚,我幹嘛幫妳們翻譯,我告訴妳,娃蒂卡沒有錢治病,若不是我先生可憐她,接她到公司宿舍住,她早就流落街頭了。」
「如果真流落街頭,我們還比較好辦一些。」我見歐小姐囂張的態度感到有點惱火,「妳言下之意,就是不願意幫我們翻譯了?」
「幫什麼幫,娃蒂卡不可能留在台灣治病,現在她就只缺一張回印尼的機票而已。」歐小姐態度極其惡劣:「她在台灣沒有半個朋友親人,如果要開刀,沒有我的簽名,妳們敢幫她開刀嗎?」
「她可以自己簽名。」歐小姐的囂張態度令林怡津氣惱難耐,所以下定決心跟她槓上,「如果妳不幫忙翻譯也沒有關係,我可以去找移民署幫忙。」
「好呀。」歐小姐氣急敗壞地盯著我們,跟著轉頭對著娃蒂卡說了一連串的印尼話,我跟林怡津聽不懂,但是話中的語氣急促,加上娃蒂卡臉上充滿恐懼,不難想見,這位歐小姐又在恐嚇她。
語畢,歐小姐轉頭望著我們說:「好吧,妳們既然不需要我翻譯,那我要先回去公司處理事情,如果有需要幫忙再打電話給我吧。」然後她提起包包就走了出去。
我沒料到這仲介會來這招,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揚長而去,留下我跟林怡津面面相覷。
林怡津拉拉我的手臂說:「樂樂,這下子怎麼辦?我們是不是把場面弄僵了?」
(……)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那些年,在婦癌科病房發生的「鳥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66 |
生死醫病 |
$ 300 |
中文書 |
$ 323 |
小說/文學 |
$ 342 |
醫病分享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那些年,在婦癌科病房發生的「鳥事」
改編自婦癌專科護理師那緹的親身經歷,每一個生命故事都仿若在身旁發生,每一滴淚水都像是滴落在你心底……
----
醫院是個屬於生、離、死、別的地方。作為專科護理師,那緹見證了人性的美麗與醜惡、生命的圓滿與遺憾。一路走來,那緹與許多病患及家屬分享歡聲,也分享熱淚。現在,她將生活化為故事,以專科護理師「林唯樂」的主角,娓娓道來婦癌病房那些乍看之下令人傷透腦筋、帶點荒謬,但其實發人省思且溫暖感人的「鳥事」──
玉蘭因遭受家暴逃家,臨終前希望和兒子團聚,但多年離家心結讓兒子遲遲無法開口喊一聲媽;外籍移工娃蒂卡的病況嚴重,在仲介壓榨下沒錢就醫也無法歸鄉;正值花樣年華的沛涵才剛新婚,就因卵巢癌復發而必須裝上人工肛門;腦部、腹部都被診斷出腫瘤、在化療期間被兒子互踢皮球的阿致婆婆,心中掛念的卻是老家那畝種給子女的菜園;不時缺席治療計畫、經常搞得醫療團隊雞飛狗跳的陳喜妹,懷著對父親難解的恨意,在生命最後倒數時刻有機會和解嗎……
面對這些複雜的生命課題,「林唯樂」並非一個人,她與病患、家屬、醫護團隊、社工師、癌友會,甚至安寧照護師,都參與了一個又一個生命故事──
「護理師是一份很美的職業,我們在生命循環中從未缺席。
我的堅韌與柔軟,都來自於我所見證的美好與缺憾。」
作者簡介:
那緹
來自北台灣,畢業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研究所,平日在護理界打滾,看盡人生百態,始終相信人性本善,持續以筆記錄雙眼所見與心中所感。另為UDN聯合新聞網之琅琅專欄簽約作家,鏡文學網路簽約作家,《我們,長期抗戰中:第一線護理人員的疫情觀察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共同作者。
章節試閱
〈序曲 初心〉
陽光普照的天氣,我端著熱咖啡行色匆匆走在醫院大廳。我是林唯樂,從大學畢業後,就進入這家醫學中心工作。經過五年的護理師臨床試煉,因緣際會下接受了專科護理師的訓練。到現在,已擔任專科護理師這份工作屆滿十年。
目前我在婦癌病房中工作,雖然介紹這麼多,想必你們對於專科護理師這個名詞還是有點陌生,就如同未曾到過醫院的民眾往往不解:專科護理師跟護理師有什麼不同?其實,說穿了,我們也是提供健康服務的一群人。醫院裡不只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還有很多的醫事人員一同為大家提供照顧,最終目的...
陽光普照的天氣,我端著熱咖啡行色匆匆走在醫院大廳。我是林唯樂,從大學畢業後,就進入這家醫學中心工作。經過五年的護理師臨床試煉,因緣際會下接受了專科護理師的訓練。到現在,已擔任專科護理師這份工作屆滿十年。
目前我在婦癌病房中工作,雖然介紹這麼多,想必你們對於專科護理師這個名詞還是有點陌生,就如同未曾到過醫院的民眾往往不解:專科護理師跟護理師有什麼不同?其實,說穿了,我們也是提供健康服務的一群人。醫院裡不只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還有很多的醫事人員一同為大家提供照顧,最終目的...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清晨時分,空氣瀰漫一絲冷冽氣息,穿上外套拿著車鑰匙緩步往地下停車場移動。日復一日,無論春夏秋冬,都在同一時間醒來,預備好一切後出門,猶如公務員般精準打卡上班,而面對的挑戰,在抵達醫院後,日日都不相同。
當遇到舉目無親的街友病患,除了與她身上癌患戰鬥外,後續的安置問題也需同時面對與處理;在病房上演了團圓戲碼卻不是美好結局,她與兒子之間未解的心結令人感到唏噓。幫助外籍勞工順利返家,除了熱心的病友們募款買機票,還有醫護人員慷慨解囊,讓她在返鄉後不會阮囊羞澀度日,但我心中仍懷抱無法醫治她的些許遺...
當遇到舉目無親的街友病患,除了與她身上癌患戰鬥外,後續的安置問題也需同時面對與處理;在病房上演了團圓戲碼卻不是美好結局,她與兒子之間未解的心結令人感到唏噓。幫助外籍勞工順利返家,除了熱心的病友們募款買機票,還有醫護人員慷慨解囊,讓她在返鄉後不會阮囊羞澀度日,但我心中仍懷抱無法醫治她的些許遺...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 序
序 曲 初心
第一章 哈囉,無家可歸的人
第二章 異鄉悲夢
第三章 渴望愛的女孩
第四章 蘭因絮果
第五章 好死不如賴活著……嗎?
第六章 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第七章 何處是我家?
第八章 媽,我愛你
第九章 道別之後的悲傷
尾 聲 始終會再相見
序 曲 初心
第一章 哈囉,無家可歸的人
第二章 異鄉悲夢
第三章 渴望愛的女孩
第四章 蘭因絮果
第五章 好死不如賴活著……嗎?
第六章 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第七章 何處是我家?
第八章 媽,我愛你
第九章 道別之後的悲傷
尾 聲 始終會再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