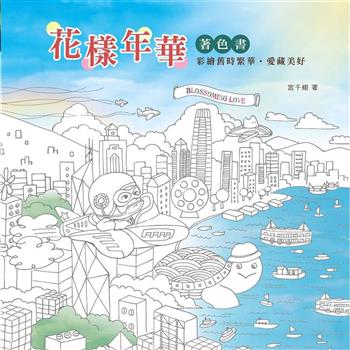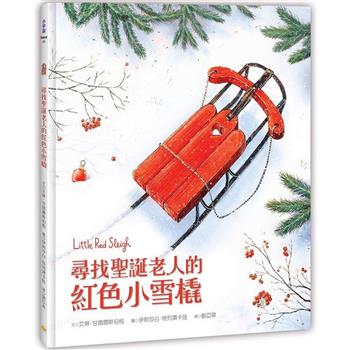第 一 回 屠村
血紅殘陽,像隻蹲踞在西山頂上的巨大火龍,灼灼目光,緊箍著沿滇池西岸南奔的一飆鐵騎,彷彿要伺機予以吞沒,好融入它亙古長照的烈焰之中。
這飆鐵騎約莫五、六十乘,個個盔甲齊整,刀槍森森,胯下所騎,皆為適於平原馳騁的高頭大馬,與矮小但具長力的滇馬顯然不同。每一騎的馬鞍上,都繫有十來綹或墨黑或花白的長髮,長髮盡處,赫然是撒上石灰的人頭,顆顆隨著鐵蹄的翻騰起落,不住地滾動蹦躍,但見石灰與塵土齊飛,鮮血共殘陽一色,端的是驚悚萬狀,駭人無比。
為首騎者,是個從五品的武略將軍,生得虎背熊腰,豹眼獅鼻,肌肉墳起,膚色黑亮,渾似鐵鑄銅澆出來的一般。他一手執韁策馬,另一手擎著巨大鮮麗的錦旗,旗面正中,恭恭整整繡著個斗大的「傅」字。這黑將軍嘴裡不斷爆出架架的嘶吼聲,混雜著大旗獵獵的凌風聲,攪和進鐵蹄隆隆的踏地聲,結合成一根無堅不摧的大鐵錘,狠狠敲碎了雲南大地素有的美麗與靜謐。
滇池的西南角,一個依山傍水的村落裡,稀稀疏疏散布著十來戶人家。雖已是臘月時節, 但雲南因西、北、東面皆有高山屏障,是以冰雪罕見,風霜少至,可說是四季和穆,景致宜人, 人間若有仙鄉,這兒或許要算上一處,而中原漢人自古因雲南地處偏遠,竟視之為瘴癘蠻荒之境哩!直至明朝初年,有個官員吳履所作的〈送雲南教授劉復耕〉詩仍云:
見說思陵過五溪,熱雲蒸火瘴天低;星聯南極窮朱鳥,山抱中流界碧雞。
苜蓿照盤官況冷,芭蕉夾道驛程迷;巍巍堯德元無外,未必文風阻遠黎。
倒是清朝乾隆間名士孫髯翁既寫景亦敘史的〈大觀樓長聯〉,形容得較為真切: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 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 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孫髯翁作此膾炙人口的長聯,已是三百多年後的俊賞雅事了,且按下不表。此時,大明洪武十四年的臘月間,在滇池西南這座小小村落裡,既無熱雲蒸火,亦乏香稻芙蓉,唯見炊煙嬝嬝,上融於雲霞,但聞雞犬聲聲,遠傳入湖山,男人漁牧農獵歸來,婦女倚在柴扉上,高喚玩耍中的孩童返家。一個少年於斜陽晚照裡,望見其父頎長威猛的身影,連忙撇下玩伴,快步奔去,邊跑邊喊:「爹爹,爹爹,您回來了!」語音爽脆,仍顯稚嫩。
其父年歲在四旬上下,劍眉星目,鼻梁高聳,滿臉虯髯,顯非漢家兒郎,而他身穿白色長衫,外罩坎肩,頭戴白色無簷圓帽,一望可知他是個穆斯林。那穆斯林大漢停步待少年奔至,伸出蒲扇似的大手,握住少年的小手,含笑道:「是呀,三保,爹爹回來了。告訴爹爹,你今日乖嗎?有沒有再把姊姊妹妹們逗哭?」「沒呢,三保今日很乖,沒逗哭姊姊妹妹們。爹爹,您再跟三保講述您去天方(即今阿拉伯)朝聖的故事好不好,好不好啦?」他滿臉求懇神色,邊說邊用小手搖晃父親的大手。
「你已聽過幾十遍了,怎還不膩?」「不膩,不膩,爹爹再跟三保講嘛,尤其是您在大海遇上颶風的那段。」「呵呵,若不跟你講,依你的性子,定要緊纏不休。等吃過晚膳,咱爺倆邊喝奶茶,邊望星空,邊說故事,如此可好?」三保得到父親應允,雀躍不已,連連道好。父子倆嘻嘻哈哈進門,才入內,察覺有異,立時止住腳步。那大漢閉目深吸口氣,張眼緩緩吐出,旋即露出驚喜神色。這時,一絕色女子趨來,為那大漢奉上一方手巾與一杯咖啡。
咖啡在當時的伊斯蘭國度裡相當普及,算是日常之飲,甚至在鄂圖曼帝國轄下,倘若丈夫未能持續供應咖啡給妻子喝,妻子可因此休夫,但在中土,此物極其稀有難得。那大漢出身不凡,年少時常有咖啡可喝,原不甚珍視,如今景況大不相同了,除了去到天方的那段時日外,已多年未享其味,日前不惜以祖傳寶物,輾轉從一支西域商隊換得些許豆子,暝目嗅聞再三,年少回憶與朝聖榮光油然而生,然後珍而重之地收藏起來。他妻子溫氏倒看得開,也知此物不宜久存,問明用法,今日心血來潮,烹煮了給夫婿飲用,平時為避人耳目,家居十分簡樸,為了此飲,刻意翻箱倒篋,找出封存已久的玉壺瓷杯來盛裝。
那大漢先用方巾抹臉淨手,再接過鑲金瓷杯,嗅了嗅黑黝黝的杯中物,輕啜一口,發出「啊」的一長聲,心曠神怡地朝妻子咧咧嘴,露出滿口齊整的白牙。溫氏用明眸回睇他,嫣然一笑,狀極嫵媚。二人結褵近二十載,恩愛彌篤。三個女娃兒湊過來向父親請安,年紀居中的妹妹朝三保扮了個鬼臉,三保為了晚上能聽故事,佯作未見。他們不似中原漢人拘謹而緊守禮法,父女又抱又親,甚是熱絡,一家人沉浸於親情與咖啡的甜香之中。
那大漢單手抱起年僅兩歲的幼女,對溫氏說道:「孩子的娘啊,我今兒忽然想到,年關將近,不如過完年,咱們去把大兒子文銘給接回來,好一家團聚,妳看如何?」溫氏回道:「說來也巧,我原也是這般打算,正想跟你商量,你倒先提出來了。」那大漢笑道:「妳我這叫心有靈犀一點通嘛!」溫氏白了他一眼,正容道:「咱們讓文銘到晉寧縣城裡幫傭,立了五年合同,你去天方,一別兩年,回來後又匆匆過了三個寒暑,算來五年期約將滿,等開春後你去將他帶回。過完年文銘便是十八了,咱們可琢磨著幫他討房媳婦兒,你看鄰村穆家的大女兒如何,他們也是回族。」
「哥要回來了,哥要回來了。」三保跟長兄最親愛,對他思念甚殷切,沒等父親回答,已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呼小叫,幾個女孩子自也歡喜。他們這些年未見長兄,但畢竟手足情深,難得將要一家團聚,是以全都喜不自勝,才兩歲的小女娃兒也跟著興奮莫名,直喊著「哥哥,哥哥」。
「三保,別胡鬧了。孩子的爹,飯菜已然備好,你跟三保先去禮拜。」溫氏悠緩說道,滿腔柔情中隱含三分威嚴。那大漢生得膀闊胸厚,軒昂魁偉,卻對嬌弱的溫氏千依百順,平常雖會跟她調笑,一旦愛妻下達指示,從不敢不遵。他此刻急急仰頭,一口喝完杯中萬分難得的咖啡,連原本要說的「選媳婦兒的話,哪一族都無所謂,人品最重要」,也隨汁液吞落肚,將杯子遞給長女,放下懷中幼女,帶著兒子三保先行小淨,整肅衣衫,進入齋堂,面對聖城默加(即麥 加)的方向恭敬而立,沉靜心思,然後舉手、誦經、鞠躬、叩首、跪坐在地,如此數次。他妻子溫氏乃是漢人,並非穆斯林,反倒自幼吃齋禮佛,不過他甚知變通,未曾強逼妻子皈依伊斯蘭教。溫氏也頗能體恤夫婿,像他前往默加朝聖之事,便得到她全力支持,雖然丈夫離去九個月後所產之女夭折,卻毫無怨言,苦苦獨力養兒育女,等待夫婿歸來,更加贏得他的敬重。
那大漢伏地禮拜時,隱隱感受到風雷湧滾,飛快逼近,仍沉住氣,不動聲色,虔誠完成儀式,方才起身與三保走出齋堂。溫氏這時也已察覺有異,與那大漢同往窗外窺探,望見蒼茫暮色裡煙塵滾滾,一條灰紅毒龍直往這村落襲來。那大漢急道:「孩子的娘,快帶孩子們躲起來,無論發生何事,切勿出屋。」溫氏尚未應允,三保已發問:「爹爹,怎麼了?」那大漢回道:「爹爹也不知道。」他將雙手按在三保肩頭上,肅然道:「兒子啊,爹爹問你,你可還記得爹爹為何將你的小名取為三保?」「孩兒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姊,而且爹爹要孩兒自保、保家與保衛聖教,是以叫孩兒三保。」那大漢愛妻及女,女兒們也計入排行,未單重兒子。
「甚好,爹爹的話你都一直牢記在心。此時此刻爹爹要你善為自保,並須保護好娘跟姊姊妹妹們,不管爹爹發生甚麼事,你都千萬不可強出頭,留得有用之身,以便長大後保衛聖教,知道嗎?」三保點頭道:「爹爹放心,三保知道了。」那大漢有不祥之感,輕「嗯」了聲,抱抱三個女兒,深情款款望了妻子一眼,隨即開門而出,關上荊扉,走出十餘丈外挺立不動,身形如淵停嶽峙,氣勢直衝牛斗,真個是不怒自威。鄰人全都躲在屋內,猶自瑟縮不安,連家犬也牢牢約束住,不使吠叫奔竄,唯恐招惹喪星上門。
那飆鐵騎旋風般掃到,為首的黑將軍看見前頭一條回族大漢垂手而立,三分從容中透著十分威風,其形容樣貌與自己前來捉拿的匪酋一般無二,不禁心下一凜,連忙止住馬隊,馬嘶聲中,原本迎風招展的傅字旗面垂了下來。黑將軍喝道:「兀那漢子,可是回回馬哈只?」回民中凡是去過聖城默加朝聖者,一向被尊稱為「哈只」,意思是「巡禮人」,因在當時極難能可貴,屬無上榮耀,本人多會隱去原名,從此以「哈只」為號。這回族大漢本名米里金,漢文名懷聖,與其父米的納都去過默加朝聖,故皆稱馬哈只,只是馬懷聖在父親去世數年後才動身,通常不致搞混,而他尊重先人,無意把眼前事端推卸給亡父,因此昂然回道:「草民正是馬哈只,不知將爺找草民何事?」
黑將軍揮了揮傅字錦旗,道:「我等奉大明征南大將軍傅友德之命,前來抓拿元粱王巴匝拉瓦爾密餘黨馬哈只,你既已自承為正犯,那就快快束手納命,若牙迸個不字,我等定殺得你全家雞犬不留,燒得舉村草木無存。」馬懷聖道:「草民世居此地,務農放牧為生,未曾入軍旅,亦從無一官半職,怎會是元梁王的餘黨呢?將爺定是弄錯了。」「哈哈,對也好,錯也罷,你到了陰曹地府,再跟閻王爺爭辯去吧,休誤我事,我等還有好些人頭要砍,許多功勞須掙。」黑將軍一說完,將傅字錦旗插於鞍旁,抽出長刀,便要拍馬上前。
「且慢!」馬懷聖瞥見混在馬隊中的一個黑衣人,朗聲道:「將爺,切莫受奸人挑撥。納西族與我回族原本井水不犯河水,各拜各的神,各吃各的糧,然而納西族的阿甲阿得跟草民年輕時,都中意漢族溫家大小姐,二人相爭不下,溫家老爺要草民與阿甲阿得以辨識蟲魚鳥獸之名決勝負,草民託天之幸勝出,娶得溫家大小姐。這件事到現在已近二十年,不意阿甲阿得仍然懷恨在心,趁機搆陷草民,草民絕非元梁王餘黨,懇請將爺明察。」
黑衣人阿甲阿得從馬隊中竄出,厲聲罵道:「馬懷聖,你滿口胡言,甚麼『世居此地,務農放牧為生』,又說甚麼『從無一官半職』,其實全是放屁!我問你,賽典赤瞻思丁是你的甚麼人?『賽典赤』的封號何來?他是否當過元狗的高官,還受忽必烈諡封為咸陽王?你爺爺拜顏的官做得可也不小,還晉封為淮王,而你爹跟你本人也分別襲封為鎮陽侯與滇陽侯,這些難道都是我栽贓捏造的嗎?說穿了,勢利極了的溫老頭,看重的其實是你的家世,哪裡是你的學識!」
馬懷聖聞言大驚,阿甲阿得所說的賽典赤瞻思丁,正是自己的五代先祖,「賽典赤」是成吉思汗賜封,天方語「聖裔」之意,元初從西域來到雲南,曾任平章政事,子孫承其庇蔭,任高官,享厚祿,世襲王侯。迨元朝氣數將盡,天下英雄競起逐鹿,馬懷聖的父親米的納便隨妻子之姓而改姓馬,捨了侯府不住,舉家遷來滇池西南畔匿居。此事殊為隱密,馬懷聖對外人絕口不提,不意阿甲阿得竟然知曉,馬懷聖更沒料到,正是他以祖傳寶物交換咖啡豆之舉,讓其身分之祕洩漏了出去。
……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不全劍(壹):少年鄭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332 |
武俠/歷史小說 |
$ 370 |
中文書 |
$ 370 |
武俠小說 |
$ 378 |
其他武俠小說 |
$ 378 |
其他武俠小說 |
$ 37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不全劍(壹):少年鄭和
☆ 鄭和甫滿十歲之際,雙親與三姊妹慘遭明軍屠戮,危急之時被明教四大法王的戴天仇所救。為了修練明教絕頂神功,鄭和揮刀自宮,竟換得無從解讀的武學祕笈……千迴百轉的人生際遇,是否能讓鄭和百鍊成鋼?一雪血海深仇?
☆ 歷史與武俠完美結合,重新定義明代「鄭和下西洋」;作者傅羽精心打造《不全劍》,系列首部曲隆重登場!
家破日將暮,劍殘人更殘;江湖多夜雨,血熱丹心寒!
鄭和本姓馬,小名三保,回族人,家族世代為尊貴顯赫的穆斯林,祖先獲成吉思汗賜封為「聖裔」,父祖皆襲封為侯。鄭和甫滿十歲之際,雙親與三姊妹慘遭明軍屠戮,危急之時被明教四大法王的光明金剛——戴天仇所救。戴天仇性格乖戾,喜飲人血,自斫十根手指裝上鋼爪,以一套「透骨鬼爪功」獨步武林。為了復仇,鄭和下定決心修練明教絕頂神功,與戴天仇一同前往明教總壇。
兩人一路走來凶險萬分,明太祖朱元璋為鞏固大權,不惜與昔日戰友決裂,成立錦衣衛組織,延攬江湖豪傑意圖剷除明教餘眾。鄭和拚死抵達總壇,不惜自宮,竟換得無從解讀的武學祕笈,他與小明王之女、明教龍鳳姑婆——韓待雪隨馬幫避走西藏,藏匿於大唐金城公主後人宅中,卻遭一位老喇嘛擄走……千迴百轉的人生際遇,是否能讓鄭和百鍊成鋼?一雪血海深仇?
作者簡介:
傅羽
臺灣大學政治系學士,美國雪城大學政治學暨經濟學碩士、經濟學博士候選人。歷任資訊公司行銷副總、總編輯,發表過數本著作與譯作。
章節試閱
第 一 回 屠村
血紅殘陽,像隻蹲踞在西山頂上的巨大火龍,灼灼目光,緊箍著沿滇池西岸南奔的一飆鐵騎,彷彿要伺機予以吞沒,好融入它亙古長照的烈焰之中。
這飆鐵騎約莫五、六十乘,個個盔甲齊整,刀槍森森,胯下所騎,皆為適於平原馳騁的高頭大馬,與矮小但具長力的滇馬顯然不同。每一騎的馬鞍上,都繫有十來綹或墨黑或花白的長髮,長髮盡處,赫然是撒上石灰的人頭,顆顆隨著鐵蹄的翻騰起落,不住地滾動蹦躍,但見石灰與塵土齊飛,鮮血共殘陽一色,端的是驚悚萬狀,駭人無比。
為首騎者,是個從五品的武略將軍,生...
血紅殘陽,像隻蹲踞在西山頂上的巨大火龍,灼灼目光,緊箍著沿滇池西岸南奔的一飆鐵騎,彷彿要伺機予以吞沒,好融入它亙古長照的烈焰之中。
這飆鐵騎約莫五、六十乘,個個盔甲齊整,刀槍森森,胯下所騎,皆為適於平原馳騁的高頭大馬,與矮小但具長力的滇馬顯然不同。每一騎的馬鞍上,都繫有十來綹或墨黑或花白的長髮,長髮盡處,赫然是撒上石灰的人頭,顆顆隨著鐵蹄的翻騰起落,不住地滾動蹦躍,但見石灰與塵土齊飛,鮮血共殘陽一色,端的是驚悚萬狀,駭人無比。
為首騎者,是個從五品的武略將軍,生...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 一 回 屠村
第 二 回 林戰
第 三 回 烽火
第 四 回 神醫
第 五 回 明教
第 六 回 自宮
第 七 回 青樓
第 八 回 死別
第 九 回 走馬
第 十 回 雪域
第十一回 江城
第十二回 劍法
第 二 回 林戰
第 三 回 烽火
第 四 回 神醫
第 五 回 明教
第 六 回 自宮
第 七 回 青樓
第 八 回 死別
第 九 回 走馬
第 十 回 雪域
第十一回 江城
第十二回 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