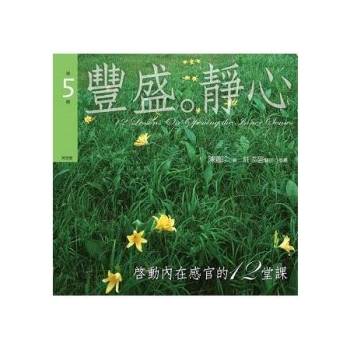推薦序
眼押韻眼神〉
洪春峰(《霧之虎》、《酒神賦》作者)
是愛讓你有了光暈。
是眼神中的愛,讓你認出我。
是思念的時間河流,我在那裡划槳。
是回味的瞬間,我變成了海明威。
是書店那一日與巷口的夜晚,讓我看見你的愛。
原本這本書的書名考量,就在上述幾行字句裡,但書名來自於內容的濃縮與意象,是愛,讓這本書有了光。靜靜地閃亮在書海裡,彷彿一個岸邊沙灘上的貝殼。一本書是這樣的,飄洋過海來看你,是書寫者的心海,是你的掌心與指頭,以及你朗讀的聲響,敲打,還能說什麼,彈奏,還想聽什麼,於是就往前往後,往南往北追尋孟樵的語言,她經歷的故事,她看見的看見,她的聽覺與觸摸,她的感受與行走,她的安靜與她的夢,這就是匯聚了無數個自我與他人的眼神,釀造出來的一杯書般造型的酒。
在書店那一日,泱和對方有著纏綿不斷,若有似無的情緒,那種情感動態,完整地被作者寫了下來,有如河流拍岸。人與人的相處,猶如借閱彼此腦海中書櫃上的書,讀到乏了,日子無味,有獨到之祕,則愛不釋手,恨不能居留在彼此心上,成為永遠居住的人,主人就是客人,就是多麼令人期待的完美的愛。而陌生感,有時成為調味劑、五香粉、十三味,在心情的巷口飄盪。
沙林傑(J. D. Salinger)在寫出《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之前曾經從軍,經歷砲火生死,炸裂了靈魂的戰爭在作者與世界上其他人一樣,造成傷痕。那樣的文學給予我們信念、失落、溫暖、被人懂得的感覺。在孟樵的這本書《眼神說了什麼》有著她以往在《《歸鄉》的親子關係與俄羅斯文化:這位導演,讓我想起我爸媽》那本書類似的口吻,只是觀察的對象與速度不一樣了,那是凝望的差異,也是書寫的差異,如果能創造故事,那就是世界上最至高無上的事情之一,或者,有如發明了一個科學理論,一則數學公式,一種審美的距離,獨有的故事。能把握這樣的語言,能夠經歷這樣的時刻,那便是許多作家心中的共同追求。
當愛不見了,回頭尋找內心的聲音,低首凝望書頁的文字。《麥田捕手》的核心是愛,愛著世界,不免失望,但依然去愛。書寫者從凡人成為英雄,是歷經千面,走過千山的。孟樵寫過「如果說,腦海的記憶是最佳的相機。那麼我們還需要相機?」我只是認為,文字就是底片,顯影一切,包括黑暗,包括光。
孟樵在〈是眼神,讓你我走入光暈〉寫出:「這回,換我呼喚你,以眼神告訴你,這世界不會黑暗、不會只有月亮,永遠有晶亮的光彩伴隨,那是你也是我。」作者的意志流淌於文字,關注的意念布滿了篇章。她又在〈月亮冷不冷,眼睛熱不熱〉中寫道:「對於美麗的悸動,停留在不知幾歲時的記憶,就是喜歡抬頭看月,就是喜歡看到月亮裡的兔子。從沒想過月亮怕黑嗎?會冷嗎?」書寫者是聆聽者、觀看者、記錄者,因此吳孟樵不得不被美麗的事物迷住。旅行、愛情、閱讀,是三把創作的聖火,她如此心懷柔思地欣賞各種美好事物,正好應證了自己的一顆心。
我們愛著同一部電影,比爾‧莫瑞(Bill Murray)的電影《今天暫時停止》(Groundhog Day)是一個關於愛和時間的故事,在那個故事中有春光,我相信孟樵也深刻體會了其中滋味,並有所感,發而為文。這本書是許多文字的珍珠落在玉盤上。
每一次書寫,就是一次分裂,一次成長。也像孟樵之前的書《歸鄉》,書寫是一種回歸內心的飛翔。《眼神說了什麼》是一本飛行之書,任語句乘載故事,讓心情印成墨跡。這本書也是一本水之書,記憶似水,愛念蒸發如淚,漂流在讀者心情的海洋。
二○二三‧二‧二八
推薦序
恰似一道道輕觸過這個世界的眼神……
涂書瑋(詩人、詩評家、大學教授)
吳孟樵的影評文字向來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不論是阿巴斯(عباس کیارستمی)、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還是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Тарко́вский),孟樵總是能夠將影像的局部/整體,與自身的生命體驗嵌合,不斷地在「影」與「文」之間,上演著一次次華麗而優雅的心思迴旋。這個文類跨界迴旋舞不只自限於靜態的事物關照,而是迴旋出種種源於自身身世中亟待陳述、梳理方得以放下的記憶與夢境,更能夠迴旋出一幅幅受塑於恆常變動、蒼涼與憂患的人間情境。
這就是孟樵,如同其人,她的文字旋身在都市寬垠的蜃景與疏離的人際網絡之間,仍是那樣仙氣而靈動。與孟樵的晤面,每每感於其心智的真純與透明,然而於塵世的惘惘間,也屢屢憂於其心地的敏感而易碎,以及如何能夠以這樣純透的心智,抵禦人間種種不可測度的風暴。直到我讀到她在《鞋跟的祕密》中一篇〈復活記〉,她寫到《我的心留在布達佩斯》的玉芸:「她的一雙眼似乎化為攝影鏡頭,環視。隨著她的視線,我一直是在起/終點專注地對應她……」,這段文字讓我反身式地意會到孟樵「眼神」的穿透力與預示感,原來,早在我們濁淌於塵世之時,她早已悠緩地站立在塵世的起/終點,以「眼神」為我們一眾好友預告著生命前路/來世的圓銳或分合。
細讀《眼神說了什麼》,其顯著的特色,除了是影/音評論文體與敘說自身故事的文體交織互文,以達到某種生命情境的釋懷與通透之外,另一項比較潛隱的寫作取向,就是孟樵既愛造夢、寫夢也解夢。夢境,當然在「精神分析」的發達年代,已然成為撬開人類意識底層或內在幽暗世界的主要入口。而孟樵尤愛對自己或他者的夢境進行「解析」,例如:「夢境,讓我以參與者,也是畫外者進入『訴說』與『告別』的情境」(〈道歉啟事〉);又或是「我倒堅信,夢跑得比你心底對自己的認識還快,且深入。只是,你敢認識你自己多少」(〈在夢裡‧旅行〉),等等。此等置身「其中」卻又「超我」式的釋夢,體現出孟樵在感官與情感的沉浸之外,亦有知性的深刻與鋒利。
孟樵的文字向來隨興拈來,段落的收束之間渾成般的自由、靈動。她往往排拒刻意的結構,或情意的布局,我也無意將孟樵刻意歸類於當代「女性」散文的某種知識框架,或是「像是XXX」的某種偏執認識之中。她的文字內裡,從未深陷於隱喻的修辭迷陣,也從未不經意流露出情思、感覺或情緒上的專斷。孟樵的「眼神」既是可以「記憶、記述、回顧、展望」,也是關乎生命記述在時間摺痕裡盛開的悲喜瞬間。於是,孟樵的每一個字恰似一道道輕觸過這個世界的「眼神」,它既能讀出月的暈臉、風的唇語、心的構成,也能在那一次張弛開闔之間,捕捉到我/們遺落在這個時代的集體感覺。
推薦序
跌出時間之外
歐銀釧(作家、星洲媒體集團駐臺灣特派員)
多年來,經過象山附近一家咖啡館,常會放慢腳步。
那咖啡館有扇大玻璃窗,偶爾,有一人或兩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向窗外。有時那位子是空的。我總是好奇,停下來,看著那窗、那人和那杯咖啡。
沒想到,今年春天,我和作家吳孟樵坐在那個位置。我們成為那扇大玻璃窗裡的兩個人。
那天,我們在象山捷運站見面,穿過公園,一起步行去咖啡館。
這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面。之前,我是她的讀者,常在《人間福報》拜讀她的作品。有一次她寫:「幾乎日日有夢,一睡就陷入夢境。」我停留在這句話許久。後來,陸續讀到她的文章,夢在她的文字之間轉折,「夢跑得比你心底對自己的認識還快,且深入。只是,你敢認識你自己多少。」
我跟著她的文字旋轉。
身兼影評人的她,曾提到關注失智症的紀錄片《以遺忘為詩》想傳達的內容在對白裡:「人生不過是場夢,而夢本身只是做夢的一部分。」她接續寫道:「不想遺忘的是『愛』──愛與被愛的記憶與能力。」我被這段透澈的文字觸動,思索了好幾天。
兩年前,她計畫出版新書《當音樂響起,你想起誰》,透過《人間福報》和我聯絡,收錄了一篇我追念音樂才子史擷詠先生的文章:〈在城市裡聽見海濤〉。出書之後,她寄書來,還送了一張她畫的畫,色彩斑斕。我想起她曾經寫的這段話:「我趴在地板作畫,畫紙畫筆所成就的圖,讓我意外發現現實生活裡的我喜歡黑白灰色調、個性內向,在畫紙上卻看到繽紛與愉悅的世界。」
初次和她見面是在一個新書發表會和展覽會上。那回匆忙,我趕著要去另一個會議,只打了招呼,和七、八個友人合影之後,跑去搭捷運,她和友人追上來,說要一起搭。我們比鄰而座,才說了幾句話,她已到站離去。傍晚,朋友傳來合影,我看見她美麗的身影,長髮綁著幾束辮子,像芭蕾舞者般,舞進相框。
那天晚上,我想起她曾提到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說:「時間與記憶彼此融合,彷彿是一枚勳章的兩面。記憶是精神概念……一旦失去記憶,人就成為虛幻存在的囚徒,因為他跌出時間之外,無法理解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係……。」
她寫道:「我在心底模擬著『跌出時間之外』的畫面。那是黑洞般無法聚焦的世界,也或許會帶來驚奇的魔幻之旅?」
窗外,月光灑落。夜裡,我又想起她的另一篇文章:「我堅信記憶會存放在月亮裡,只等待可以展現光芒時,就像是貓們燦亮亮的眼睛。」心有所感,我在那張舊報紙上寫了一段文字;「月光是記憶的絲線,收藏無數透明的心靈,照亮幽暗。」
那段日子,她寫電子郵件來,和我分享一些生活小故事。每封郵件都好像在奔馳的捷運上,聽她輕聲說故事。
直到今年春日,我們來到象山附近的咖啡館,坐在面向路口的位置。從玻璃窗望出去,是一條小路,附近有幾棵不知名的樹。我們追念共同的朋友史擷詠,設想他在天上創作樂曲。偶爾有路人經過,停下來望著我們,就像多年來,我在窗外看著咖啡館裡的人們。
她提起伊森‧霍克(Ethan Hawke)主演的電影《超時空攔截》(Predestination)裡的一句話:「時間一直在改變我們,而我們在時空裡穿梭。」
那個下午時間過得飛快。傍晚,我送她去搭捷運,再次步行經過公園。她說:「聽講這時候有一位愛讀書的男子會來到公園。」是的,就在前方的長椅上,他正捧讀一本厚厚的書,專注地閱讀。書名是《《歸鄉》的親子關係與俄羅斯文化:這位導演,讓我想起我爸媽》。
那不就是她的作品?我們在時間裡?或是跌出時間之外?
她沒有上捷運,說要走回家。深夜,她傳來一封信:「很抱歉,今天送妳的玫瑰不夠好。」我看著藍瓶子裡的玫瑰,它呼吸著月光,好像正在夢裡,等待綻放。
推薦序
目光後面的生命迴盪
蔡翔任(詩人、哲學教師、雜文作家)
或許是長年浸潤在電影裡,吳孟樵的文字有如善於觀看的鏡頭。那是一種帶著影像論的眼神,孟樵其人其文都是如此,她能夠將人的言語、動作、神情、習慣、背影、心思意念等種種騷動繽紛的內在風景以及外在事物與時空場景,固定在一個欲言又止的戲劇性瞬間,那是法國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所說的「我把暈眩固定住」(Je fixais des vertiges)的文字煉金術,也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numen──神祕的指示力量,即經由神的注目而被捕捉、凍結、抑制住的歇斯底里,暗示著由神明靜默的手勢所宣判的重要時刻,或甚至是命運。這種書寫型態能夠把我們帶回到一幕又一幕的寓意,它們是命運交織的線團,也是看與被看的交會、穿透與纏繞。
確實,讀孟樵《眼神說了什麼》這本書的文字,我腦中總會不斷浮現法國導演布烈松(Robert Bresson)的話:「兩人四目交投,看到的不是對方的眼睛,而是對方的目光。」(Deux personnes qui se regardent dans les yeux ne voient pas leurs yeux mais leurs regards)。當然,對她而言,穿透到他人的、以及自己的目光後面不是別的,而是一個個有重量、有溫度的生命故事。不妨說,孟樵的書寫之所以動能強大、之所以細膩深刻,乃源自於情深義重。不論結緣是深是淺、充實還是缺憾,她都會珍惜並演繹之。家人、親人、友人,或是讓她感動的陌生人……,是其文字運轉的樞紐,環繞、展開的是其博雅的素養──電影、文學、知識、音樂、作畫、古典詩詞等,再加上其獨特的靈魂力量──比方說夢境書寫與童年書寫彼此迴腸盪氣的交錯,這些都讓孟樵的每一則書寫背後盡是生命的迴盪。
作者序‧敘
眼神的魅力,展演故事(節選)
覆地翻天猶如大地的演化,俯視與仰望,可以掀起什麼樣的印記?
從前的從前,我就像個軟骨動物,沒有太多支撐的力量,兩手插在口袋裡頹唐地垂眼地走路,那是因為懶得理人,也是因為害羞。直至仰起頭抬起眼觀看,我體會到眼睛具有心的力量。
看著地面的石頭、路面的隙縫,下雨時水花的濺起,像是刻畫的眉眼觀看世間人。少年時期希望自己是顆石頭,卻忽略石頭或許也有許多的想像力與感官能力。
看過《魔戒》(Lord of the Rings)後,除了最愛亞拉岡之外,樹真是吸引我,樹可以牽動樹,彼此呼喚彼此團結,無私地與大地連結。
於是,我更愛看樹木更愛看天空了。遠望雲湧動的舞姿(如果可以假想著是雲的心情),那是誘引的舞姿,千變萬化。就像是記憶與心情可以如此地包覆,又如此地融合與離散,彷如舞臺劇布幕,要不要換幕由劇作家決定。如果太陽星月與雷電雨一起來,那麼就是唱起搖滾樂或奏起交響樂。雲朵與雲朵間的隙縫,就是「眼睛」。
雲快速地變化著,如同世界的運作法則,記憶更迭記憶,遺忘丟失遺忘。但是,你會記得打動你的眼神或是干擾你困擾你的眼神。那麼,眼神可以記憶、記述、回顧、展望,甚至是重建嗎?
在我思考中,回顧也是創造的一環,重新賦予可期的生命。布洛茨基(Иосиф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родский)的生命歷程經過離散也嘗試回顧,他認為記憶與藝術的共通之道是偏愛選擇和嗜好細節,記憶包含細節,而不是整個畫面。他也提到:「你不能用它來重建任何人,哪怕是在紙上……。」乍看這段文字,很令人傷感;繼之我想,他的意思是所有的記憶都需要更多更多的細節,而我們能做到多少細節不被疏略。
所有人的記憶與細節就像是碎片,是不是也就像是雲,漂流飄動,沒人可以準備好所有的細節去做記憶記述。記憶需要空間,安排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牽掛。但是,我的思緒經常是一瞬在此一瞬在彼,甚至經常串結起來,心的空間被撐得超大也超小,於是擠壓了心。把記憶拋開,給出更好的空間,或許就是記述,從記述中建構情感,而不讓某些記憶被自己不小心壓(壓輾/壓抑)碎了。
那麼把範圍縮小在眼神,眼神能具有什麼樣的力量?我們可以輕易地舉例眼神:快樂歡欣喜悅高興大笑微笑興奮期待、焦慮緊張恐慌恐懼驚嚇、質疑驚詫疑惑挑釁、不屑不滿不安、憤怒憤慨暴怒怨懟剽悍、憂鬱鬱悶傷心悲哀怯弱、藏淚落淚或是歡喜的淚、內斂防衛攻擊侵略、調皮體貼憐愛鎮定穩健和氣、堅毅勇敢坦然不退縮……等等充滿情緒的眼神,眼神就是符號。眼神也可以變成一把劍,將思維以最簡潔的方式傳遞,不以字眼傷人、不以肢體或物件傷人,而是以最穩實的力量傳輸自己正在想什麼,以及能做到什麼,甚至是化險為夷。
我們都有許多與陌生人,與熟識親友間對視的經驗,瞬間接收到情感或情緒的時刻,尤其疫情以來戴著口罩,無論相識或不相識者的眼,形成臉部的重點,能以眼睛辨識他人或自己的當下情緒,無形中加深了眼的接收能力以及心的感知能力(視力不好或是眼盲者,或更具有強大的感知能力)。疫情間,我更愛看植物,每一天都有植物對人間訴說的語言。
《眼神說了什麼》共收錄五十八篇文章,其中有十一篇曾收錄在二○二○年五月出版的《《歸鄉》的親子關係與俄羅斯文化:這位導演,讓我想起我爸媽》、一篇收錄在《當音樂響起,你想起誰》,對已看過上述那兩本書的讀者致歉,也藉機解釋會堅持如此收錄,是為了我很珍惜《人間福報》副刊散文專欄,每至交稿期,視當時生活或新聞所產生的情狀而書寫,有我個人的心緒。主體在於《人間福報》「心之所念」專欄(一篇)再至「樵言悄語」三年(三十六篇),當時還沒有疫情,希望能使這些篇章完整收錄於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