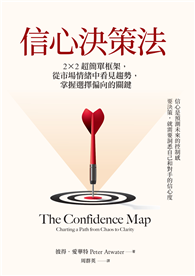「文學是對自由的渴望──而待寫作深入下來,我才開始意識到,寫作其實遠不只是一片浪漫的雲彩,它也許是一種超脫,但它更是一種對世俗生活的回望;只有回望了,那雲彩才可能閃爍出靈光異彩。」──何玉茹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小城文化館辦報紙的葉建華來到師範學院文學班進修,她沉迷在褚威格、弗洛姆、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細緻又開闊的世界,與同學藍音的交流,也讓她在短時間內重新經歷了前半生的精神跋涉──幼時對閱讀的渴望、文革時與學長偷偷躲在充滿老鼠的圖書館讀《簡愛》,為了脫離農村來到城市擔任臨時雇員,卻發現所謂「城市」、「農村」的分野彷彿只存在於戶口名簿上,人們的口音、行事作風早已沒有了界線,但人與人之間實質的不平等卻依然存在。
於是她試著在書裡、在愛情裡、在工作裡、在寫作裡思索關於「平等」的答案,來到文學班就像是陽光裡有了樹蔭,雨天裡有了雨傘,那沒著沒落、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竟是不知不覺地消失了。只是兩年的時間轉瞬即過,這些思考、迷惘、渴望、愛戀是否能昇華成永恆?
本書特色
★中國女作家何玉茹從城鄉、智愚、理想現實等對比性探討「平等」議題的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