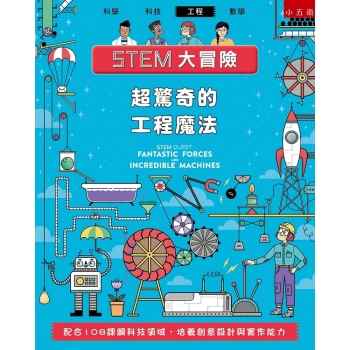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百萬小說獎得主.凌煙.刻劃台灣半世紀崢嶸的時代三部曲★
★描繪日治時期以降,時代變局下的聚散悲歡──一名借腹子的誕生,無形中牽引著雲林北港四個家族的命運。從青春的熱戀、兄弟的情義、愛國的情操到家庭日常的包容,牛車緩緩走過半世紀的歲月,見證歷史硝煙中,淬煉出的人性至善與至美。
同樣孕育自她的體內,
農家子與富家子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丈夫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阿春揪著胸口的衣領拉著兒子永隆跪在他身邊,淚水無聲地落下,想著他最後的交代:要買一頭牛,好好栽培永隆讀書,不能讓孩子和我們一樣做一輩子的青瞑牛……
此時地主陳進丁向阿春提出一個意外的請求──獨子博文受到朋友牽連,即將前往南洋擔任戰地實習醫生,但是博文的妻子婚後遲遲未能生育,因此想向阿春借腹生子,藉以延續血脈。
他需要一個孩子,陳家的未來才能延續。
她需要一頭耕牛,蔡家才有翻身的機會!
阿春最後同意以一頭母牛交換這個孩子,只是懷胎十月、從身上掉下的骨肉,又豈能如此輕易地割捨呢?這場交易將如何改變兩家的命運?太平洋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隨著政權交替、各方觀念衝突越來越深──歷史的齒輪又將帶領他們走向什麼樣的未來?
本書特色
★「世間種種的仇恨、誤解與遺憾,唯有愛能化解與彌補。」──百萬小說獎得主.凌煙,刻劃台灣半世紀崢嶸的時代三部曲!
★一名借腹子的誕生,無形中牽引著雲林北港四個家族的命運。從青春的熱戀、兄弟的情義、愛國的情操到家庭日常的包容,牛車緩緩走過半世紀的歲月,見證歷史硝煙中,淬煉出的人性至善與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