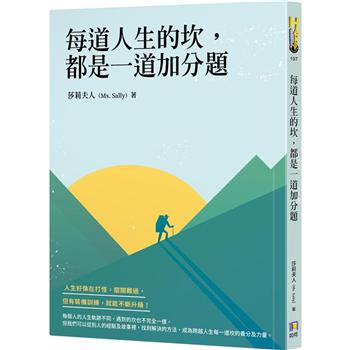著名文學評論家、專欄作家司徒衛於2003年辭世,距今(2023)已二十載。
司徒衛(1921-2003),本名祝豐,字茂如,原籍江蘇如皋,1947年來臺,曾任教成功中學、文化大學,著述甚豐,為臺灣著名書評家、專欄作家。
他長期從事教育與編輯工作,為臺灣文壇培育出眾多文學大家;主編《幼獅月刊》、《文藝論壇》、《自立晚報‧副刊》等刊物;編著《五十年代文學論評》、《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時代》等書刊;並於1980年代中期以降持續在聯合報和中華日報副刊的專欄寫作。正如李瑞騰先生所言:「……作為一位教師,他讓學生懷念;而為文壇做過的事、出版過的書,文藝界不應把他遺忘。」
本書由李瑞騰先生與歐宗智先生主編,收錄鄭培凱、渡也、蕭國和、向陽、趙衛民、毛瓊英、李宗慈、范銘如、歐宗智、周昭翡等人的懷念文章,並收錄訪談及司徒衛個人詳細資料。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司徒衛的人格與文風的圖書 |
 |
司徒衛的人格與文風 出版社:釀出版 出版日期:2024-03-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03 |
作家傳記 |
$ 255 |
中文書 |
$ 255 |
華文文學人物傳記 |
$ 261 |
作家傳紀 |
$ 261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司徒衛的人格與文風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李瑞騰
1952年出生於南投草屯,在臺中一中讀初、高中,在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完成學士、碩士、博士學業,曾專任教職於德明商專、淡江大學中文系、中央大學中文系,前後40年。在中大31年,曾任中文系系主任、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長、人文藝術中心主任等,2010年2月1日起借調臺灣文學館館長4年。著有詩集、散文集、文學論述二十餘種,主編圖書七十餘種。
歐宗智
1954年生於臺北,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新北市清傳高商校長,現為連清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出版《仰望自己的天星》、《春衫猶濕》等二十餘種。近年以論述為主,著有《臺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村上春樹長篇小說析論》等多種,兼具論文之理與小說之趣,素有「校長評論家」之譽。
李瑞騰
1952年出生於南投草屯,在臺中一中讀初、高中,在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完成學士、碩士、博士學業,曾專任教職於德明商專、淡江大學中文系、中央大學中文系,前後40年。在中大31年,曾任中文系系主任、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長、人文藝術中心主任等,2010年2月1日起借調臺灣文學館館長4年。著有詩集、散文集、文學論述二十餘種,主編圖書七十餘種。
歐宗智
1954年生於臺北,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新北市清傳高商校長,現為連清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出版《仰望自己的天星》、《春衫猶濕》等二十餘種。近年以論述為主,著有《臺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村上春樹長篇小說析論》等多種,兼具論文之理與小說之趣,素有「校長評論家」之譽。
目錄
編序/李瑞騰
【輯一】司徒衛基本資料
司徒衛小傳
司徒衛年表
司徒衛著作書目及提要
報導及評論司徒衛篇目
司徒衛關於文藝書評之理念(摘要)
【輯二】訪談與評論
走不盡的文學路──訪司徒衛兼談《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王寬之
珍貴的文學史料與文學批評的典範──我看《五十年代文學論評》/歐宗智
專欄文章的新境──談司徒衛《靜觀散記》/歐宗智
盡一個大我的責任──祝豐的求學與創作/周昭翡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訪司徒衛先生/劉叔慧
提燈者──司徒衛老師與我/歐宗智
文學與人生的導師──記司徒衛老師/歐宗智
我的師專生活:懷念祝豐老師/謝瓊玉
【輯三】他依然閃著光
祝豐老師/鄭培凱
彷彿又看見老師看著我──懷念祝豐老師/渡也
我所有的一切/蕭國和
做一個持平且謙和的人──追思祝豐(司徒衛)老師/向陽
詩的尋求──夸父追日/趙衛民
他依然閃著光──懷念祝豐老師/毛瓊英
再當一次老師的學生/李宗慈
畢業後開始的師生情誼/范銘如
記祝豐老師/周昭翡
【附錄】
鄉情無限話如皋/司徒衛
大學生活瑣憶/祝豐
【輯一】司徒衛基本資料
司徒衛小傳
司徒衛年表
司徒衛著作書目及提要
報導及評論司徒衛篇目
司徒衛關於文藝書評之理念(摘要)
【輯二】訪談與評論
走不盡的文學路──訪司徒衛兼談《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王寬之
珍貴的文學史料與文學批評的典範──我看《五十年代文學論評》/歐宗智
專欄文章的新境──談司徒衛《靜觀散記》/歐宗智
盡一個大我的責任──祝豐的求學與創作/周昭翡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訪司徒衛先生/劉叔慧
提燈者──司徒衛老師與我/歐宗智
文學與人生的導師──記司徒衛老師/歐宗智
我的師專生活:懷念祝豐老師/謝瓊玉
【輯三】他依然閃著光
祝豐老師/鄭培凱
彷彿又看見老師看著我──懷念祝豐老師/渡也
我所有的一切/蕭國和
做一個持平且謙和的人──追思祝豐(司徒衛)老師/向陽
詩的尋求──夸父追日/趙衛民
他依然閃著光──懷念祝豐老師/毛瓊英
再當一次老師的學生/李宗慈
畢業後開始的師生情誼/范銘如
記祝豐老師/周昭翡
【附錄】
鄉情無限話如皋/司徒衛
大學生活瑣憶/祝豐
序
編序
李瑞騰
一九七二年秋天,我來到陽明山華岡的中國文化學院,就讀中文系文學組。我原來的文學想像,除了浩瀚的古代文史典籍,還有現代詩文創作,但文學組完全不提供新的東西,因此,我在大學四年有關現代新文學的學習,基本上是自學,到圖書館閱讀書報,胡亂摸索創作,結交一些對寫作有興趣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大一教書法的史紫忱老師,像傳統的師父帶徒弟一樣,領我進入一個有情有義的文藝江湖。
我就在史府認識在中文系文藝創作組任教的祝豐老師。我大一學習寫鄭板橋的字,一邊臨帖,一邊讀鄭板橋詩文字畫,有點體會,試寫了一篇小論文,當作學期報告,史老師建議我改寫成〈鄭板橋的文藝觀〉,也幫我擬了一個題綱,我大感興趣,努力寫完後呈閱,沒多久,它竟然在《自立晚報‧副刊》的「星期文藝」幾乎整版刊出,史老師說他把我的文章拿給祝老師看,祝老師時亦兼《自立晚報》副刊主編,他覺得很好,就發了。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開啟我往後漫長歲月以評論為主的寫作生涯。史老師於我恩同再造,祝老師則引我上了文壇,在他耕耘的文藝園圃,我開始大量發表作品,甚至包含小說,在我那段三餐不繼、困知勉行的日子,《自立晚報》的稿費真是天降之甘霖啊!
史老師不良於行,我從大三開始陪他去學校上課,從住所到學校很近,但必須搭計程車,然後讓他扶肩上樓,一直到我讀完碩士班。我因此在史府的時間很多,彷彿那便是自己的家。祝老師有時會來,我和他談話不多,簡單的交談主要和寫作有關,有一回他說副刊改版,要我多寫一些稿子給他,那一段時間,我用了許多筆名;另有一次的記憶非常深刻,那是《聯合報》剛辦文學獎的時候,他可能看到了什麼,要我多關注,可以寫點觀感,我那時還不是很了解複雜的文學社會,沒什麼特別的想法,但從那時起,我真的一直關注文學獎,且認為那是文學發展的指標之一。
我沒上過祝老師的課,但文藝組的朋友對他評價很高,特別是對古今詩歌的解讀。華岡有一個文壇,有教授、畢業校友、在學學生,都亮眼;校園詩社、書評社的活動頻繁,執事的同學常獲得祝老師的協助,看樣子,書評社的成立很可能和他有關(祝老師以筆名司徒衛寫書評,在一九五四年出版《書評集》、一九六○年出版《書評續集》)。一九八○年代之初,相應於由學院改制為大學,華岡曾有過一陣文學榮景,出版部辦了一本《文學時代》(雙月刊,一九八○至一九八三,共出十六期),由魏偉琦、李昂前後主編,華岡出版部更企劃出版「華岡文叢」,第一輯有田原《青色年代》、吳東權《離巢燕》、朱西甯《海燕》等人作品集,祝老師的《奔雲集》也在其中。第二輯是「七十年代作家創作選」,有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等各類作品精選集,分別由向陽、趙衛民、歐宗智、李昂編選。其背後的支撐力量來自祝老師。
祝老師的住家在臺北市濟南路自立晚報社的對面巷內,成功中學教職員宿舍(詩人紀弦也住那裡,他們是成功中學同事)。學生時代我住華岡,有時下山到自立晚報社代史老師、胡(品清)老師領稿費,曾到祝老師府上拜訪,多年以後,因為齊東詩舍,我在已消逝的自立晚報社周邊多次踏查,曾進到猶存在的成功中學宿舍區,望著祝老師的舊居,佇立良久,時祝老師已病逝美國紐約十年矣。
祝老師一九四八年來臺以後,一方面教書,先在成功中學教國文,後來到文化學院文藝組,其間也曾兼課於育達商職、省立臺北師專等校;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刊物有《幼獅月刊》、《文藝論壇》、《自立晚報‧副刊》等,也曾為驚聲文物供應公司主編「驚聲文藝叢書」,為天視出版公司策劃編印《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參與文化學院《文學時代》之創辦等;寫作方面,重要的當是一九五○年代的書評寫作,以及一九八○年代中期以降在《聯合報》和《中華日報》副刊持續八年的專欄寫作。
二○二三年是祝老師辭世二十週年,我聯繫曾受教受惠於祝老師的歐宗智校長,商量為祝老師編印一本紀念文集。歐校長曾為祝老師寫過多篇評介文章,也收集不少相關資料,我們一起研擬邀稿名單,獲得朋友們的響應,編成此集。大體來說,本書所收篇章觸及祝老師一生的教學、編輯和寫作,作為一位教師,他讓學生懷念;而為文壇做過的事、出版過的書,文藝界不應把他忘記。
本書得以問世,特別要感謝秀威資訊科技宋政坤總經理,當我向他提及,我想為祝老師編紀念文集時,他馬上答應出版,說他大一在文藝組上過祝老師的課,印象深刻。我們都念舊惜情,人間因緣總也千迴百轉,緣深緣淺而已,在相遇的那一刻,我們誠心掌握當下。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李瑞騰
一九七二年秋天,我來到陽明山華岡的中國文化學院,就讀中文系文學組。我原來的文學想像,除了浩瀚的古代文史典籍,還有現代詩文創作,但文學組完全不提供新的東西,因此,我在大學四年有關現代新文學的學習,基本上是自學,到圖書館閱讀書報,胡亂摸索創作,結交一些對寫作有興趣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大一教書法的史紫忱老師,像傳統的師父帶徒弟一樣,領我進入一個有情有義的文藝江湖。
我就在史府認識在中文系文藝創作組任教的祝豐老師。我大一學習寫鄭板橋的字,一邊臨帖,一邊讀鄭板橋詩文字畫,有點體會,試寫了一篇小論文,當作學期報告,史老師建議我改寫成〈鄭板橋的文藝觀〉,也幫我擬了一個題綱,我大感興趣,努力寫完後呈閱,沒多久,它竟然在《自立晚報‧副刊》的「星期文藝」幾乎整版刊出,史老師說他把我的文章拿給祝老師看,祝老師時亦兼《自立晚報》副刊主編,他覺得很好,就發了。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開啟我往後漫長歲月以評論為主的寫作生涯。史老師於我恩同再造,祝老師則引我上了文壇,在他耕耘的文藝園圃,我開始大量發表作品,甚至包含小說,在我那段三餐不繼、困知勉行的日子,《自立晚報》的稿費真是天降之甘霖啊!
史老師不良於行,我從大三開始陪他去學校上課,從住所到學校很近,但必須搭計程車,然後讓他扶肩上樓,一直到我讀完碩士班。我因此在史府的時間很多,彷彿那便是自己的家。祝老師有時會來,我和他談話不多,簡單的交談主要和寫作有關,有一回他說副刊改版,要我多寫一些稿子給他,那一段時間,我用了許多筆名;另有一次的記憶非常深刻,那是《聯合報》剛辦文學獎的時候,他可能看到了什麼,要我多關注,可以寫點觀感,我那時還不是很了解複雜的文學社會,沒什麼特別的想法,但從那時起,我真的一直關注文學獎,且認為那是文學發展的指標之一。
我沒上過祝老師的課,但文藝組的朋友對他評價很高,特別是對古今詩歌的解讀。華岡有一個文壇,有教授、畢業校友、在學學生,都亮眼;校園詩社、書評社的活動頻繁,執事的同學常獲得祝老師的協助,看樣子,書評社的成立很可能和他有關(祝老師以筆名司徒衛寫書評,在一九五四年出版《書評集》、一九六○年出版《書評續集》)。一九八○年代之初,相應於由學院改制為大學,華岡曾有過一陣文學榮景,出版部辦了一本《文學時代》(雙月刊,一九八○至一九八三,共出十六期),由魏偉琦、李昂前後主編,華岡出版部更企劃出版「華岡文叢」,第一輯有田原《青色年代》、吳東權《離巢燕》、朱西甯《海燕》等人作品集,祝老師的《奔雲集》也在其中。第二輯是「七十年代作家創作選」,有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等各類作品精選集,分別由向陽、趙衛民、歐宗智、李昂編選。其背後的支撐力量來自祝老師。
祝老師的住家在臺北市濟南路自立晚報社的對面巷內,成功中學教職員宿舍(詩人紀弦也住那裡,他們是成功中學同事)。學生時代我住華岡,有時下山到自立晚報社代史老師、胡(品清)老師領稿費,曾到祝老師府上拜訪,多年以後,因為齊東詩舍,我在已消逝的自立晚報社周邊多次踏查,曾進到猶存在的成功中學宿舍區,望著祝老師的舊居,佇立良久,時祝老師已病逝美國紐約十年矣。
祝老師一九四八年來臺以後,一方面教書,先在成功中學教國文,後來到文化學院文藝組,其間也曾兼課於育達商職、省立臺北師專等校;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刊物有《幼獅月刊》、《文藝論壇》、《自立晚報‧副刊》等,也曾為驚聲文物供應公司主編「驚聲文藝叢書」,為天視出版公司策劃編印《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參與文化學院《文學時代》之創辦等;寫作方面,重要的當是一九五○年代的書評寫作,以及一九八○年代中期以降在《聯合報》和《中華日報》副刊持續八年的專欄寫作。
二○二三年是祝老師辭世二十週年,我聯繫曾受教受惠於祝老師的歐宗智校長,商量為祝老師編印一本紀念文集。歐校長曾為祝老師寫過多篇評介文章,也收集不少相關資料,我們一起研擬邀稿名單,獲得朋友們的響應,編成此集。大體來說,本書所收篇章觸及祝老師一生的教學、編輯和寫作,作為一位教師,他讓學生懷念;而為文壇做過的事、出版過的書,文藝界不應把他忘記。
本書得以問世,特別要感謝秀威資訊科技宋政坤總經理,當我向他提及,我想為祝老師編紀念文集時,他馬上答應出版,說他大一在文藝組上過祝老師的課,印象深刻。我們都念舊惜情,人間因緣總也千迴百轉,緣深緣淺而已,在相遇的那一刻,我們誠心掌握當下。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