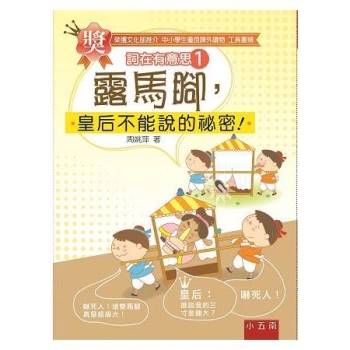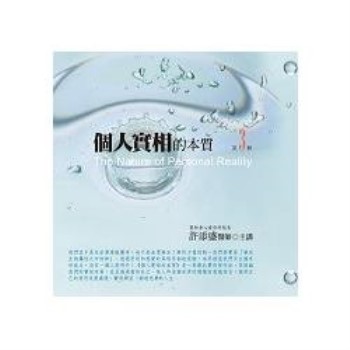廁所導航臺──
我的電影原型人物 金金金金
1
他生來面若桃花,甚至呼吐出的氣息都帶有一股奶與花蜜混合的香甜。年幼的時候,他是我的驕傲。那些年長的年少的三角城居民,都喜歡多看他幾眼,更貼近他一些,以便嗅食那種丁香花香味兒,並把它帶到夢裡。年長起來,他卻日漸腐壞,成了我的恥辱。他在三十歲的年紀上依舊面白脣紅、笑靨蕩漾,依舊渾身香氣,走起路來嫋嫋娜娜的樣子,只有說起話來聲音還算金屬。他的樣子如此顛覆,倒也不足為奇。對於民風淳樸的三角城來說,他畢竟是一朵土生土長的男性之花,除去早已進入傳說之外,還是有讓人司空見慣的一面。令我再不敢與他同行於街市的恥辱柱有兩根。一根是他得了冠軍,在全市首屆踢毽子比賽中。那次比賽報名參賽的一律是女性,只有他一名男性,結果他脫穎而出,技壓群芳。另一根是他終於如願以償,擠進了三角城棉紡織廠,當上了一名紡織男工。我身邊的朋友都在咿咿呀呀地說,這可破了紀錄,蓋了帽,絕了頂,因為金金金金是三角城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長把柄的蜘蛛女。
附注:金金金金是我舅舅的名字,他自己取的。我外婆金丁氏和外公金堡壘給他起的名字叫金鑫。他唱兒歌跳猴皮筋的時候把它打散,唱成了金金金金。上初中那一年,他決定以金金金金來註冊登記,負責登記的婦女老師被日本兵強姦過,反對他用日本式的四字名,削減掉一個,我舅舅覺得倒也差強人意,只是堅持讓我一定要叫他四字名金金金金。與他同時上初中的歐陽強大和淳于莫名,也都被女老師削去名字的慧尾,成為歐陽大和淳于莫。
再附注:蜘蛛女是我們這群惡少對紡織女工的惡稱。棉紡廠是三角城內唯一一片工業區,占據了三角城東南角的好大一片區域,廠區內沒有任何一個男性。老人們說,連飛進去的麻雀都全是雌性的,沒一個公的。每當下班的時候,女工們總是披散著飛瀑一般的長髮湧現在街上。她們都剛剛在工廠裡的浴池裡洗過澡,不無炫耀與自戀地把一天中緊束在頭頂、緊壓在帽底的秀髮嶄露給小城的夕陽與夕樹。在我們還不懂得尊崇秀髮之美的禿小子時代,她們的來勢、她們的陣容、她們的職業屬性,一度暈眩了我們的童年。把她們與蜘蛛聯想到一起,是我們狹窄的想像之渠中能夠通流的唯一一股淨水。於是,我們躲在樹後和牆頭,由其中膽子最大的喊「一」和喊「二」,然後由膽兒小的和膽兒大的一起喊:「蜘蛛女,不上班!」到現在為止,我也不知道,喊她們「不上班」是對她們怎樣的羞辱。
2
他的姊姊金燕子生下我的時候,他十五歲,她二十五歲。金燕子在鐵路醫院裡當護士,金金金金在鐵路一中讀初二。她沒時間帶孩子,他卻喜歡帶孩子,襁褓中的我便成了他課餘時間的主修課程。我跟隨母姓。他給我取名歸歸,怕我淘氣跑丟不歸家。
他做任何事都很細緻、很溫柔。聽我媽媽說,我的襁褓中一年三季充滿花香,春天是桃花梨花迎春花,秋天是玫瑰和野菊,冬天是乾茉莉,它們是金金金金從茉莉花茶中「採摘」出來的。通過媽媽的記憶和對比比我更小的寶寶,我把自己的嬰幼年想像為丁香花香、乳香和尿香和尿騷氣混合的味道。
我的最初記憶與媽媽爸爸無關。它棲落在舅舅的懷裡和背上,撲扇著毛茸茸的翅膀。舅舅有時抱著我,有時揹著我,清晨去看朝陽,用草尖上的露滴沾溼我的頭髮,說一些「我們都是草木,春天來秋天走」的話給我聽,晚上就是面朝西方,靜靜地站著,陪伴太陽西落,不錯過它的最後一線光輝。我是個調皮搗蛋的孩子,但是那些時刻,從來不鬧不吵。如有神力灌注於場景與血液之間。
他的姊姊是個粗枝大葉的人,連他在日漸成為三角城西北一帶的著名人物都一無所知。
他的名聲首先來自於揹我和抱我的方式。
他模仿當紅日本電視劇的女主角,為我親手縫製成三塊背巾,一塊橙黃鑲銀邊兒,一塊土紅繡鳳凰,一塊是墨藍色。他輪替著用它們包住我的腰身和屁股,揹著我去看豪雨過後的溝渠,去白樺樹林進而聽鳥唱歌,也去劇院看戲看電影。他長得細高䠷,我們走在街上,會有比他小比我大的小學生大聲喊他:「喂,男阿信!你從哪兒生的孩子呀!」另一些孩子就嘻笑著應答:「從屁眼兒!」我衝他們哭,衝那夥山歌賊,大聲地叫著嚎著哭。雖然我還不諳人事,但我是一頭幼獅,憑藉原生的敏銳就能嗅出欺凌的訊息。哭聲把他們嚇跑後,我發出了來此世界的第一聲呼喚。媽媽。他吃驚地轉過頭來,把我的脣緊貼在他的左頰上。
等我上了小學,他高中畢業沒有工作在家賦閒的時候,我問過他,為什麼要用日本女人的方式揹我。他說,那是他所看到的最輕鬆又最含辛茹苦的揹孩子方式。三角城人揹孩子,一般不借助工具,只是把孩子向背上一顛,要孩子雙臂環住脖頸或雙手攀住雙肩,疼孩子的人反背雙臂用雙肘和雙手夾孩子的雙腿,揹起或放下雖然較為便利,但背負的過程雙方都要付出努力,而且是雙方都要專注於「疼」這個姿勢,定型在這個動作上,不可稍有鬆懈,否則孩子就會從背上仰摔下去,造成腦震盪,或者成為二傻子。日式背法,既解放了背負者的雙臂雙手,又解放了孩子,不讓人生的負擔過早地攤派到小孩子的身上。「媽媽」只要使用負重的力就行了,負重的樣子卻最鄉土。而且,它還可以進行詮釋,娃娃小的時候,可以視為揹著一個布娃娃,娃娃個兒頭兒太大太沉的時候,又可以視為人生的重軛壓在脊背上。無論如何,都是詩意的。他補充說,女生比男生含辛茹苦,一生都是。
金金金金的數理化成績很差,外公外婆去世後,他的姊姊我的媽媽一直為此嘆息不止。只有語文課,算是他可以輕鬆過關的科目。他的作文每一篇都用陰性的第三人稱作主角。「她穿著一條蝴蝶般的裙子坐在馬車上,迎面而來的風吹開她心中的青春之花,臉龐是開放的花瓣。」他只有我一個朋友,悄悄告訴我,他寫的每一個「她」,都是他自己。他的每一任語文老師都是年輕帥氣的男老師,他們無一例外地喜歡他。但是,教務長很討厭他,一有機會就在全校課間操的時候點名兒或不點名兒地嘲諷他,說:鐵路一中出了一個會織毛衣的天才,還叫個日本名,只可惜數理化門門不及格,不能帶著他的手工藝品走遍天下。
金金金金初涉編織領域,是在外婆去世不久。外婆為我編織的毛衣肘部和袖部在我爬樹的時候刮了個稀巴爛,我怕媽媽訓斥,就向舅舅求助。他拿起剪刀,乾淨俐落地把肘部以下剪斷,然後理出一團顏色相近的毛線,找出外婆遺留下來的竹質織針,再從斷袖上找到一個又一個針眼兒,穿到針上,無師自通地編織起來。在媽媽值夜班回到家裡的早晨,我從睡夢中醒來,枕旁端端正正地擺放著左袖新織的毛衣。和衣躺在床上熟睡的舅舅,臉上微微蕩漾著笑意。晨光中,他的兩頰透泛著嬌妍的瑰紅,美麗得令蓬蓽生輝。當時我想,他也許是織女星下凡。
差不多是從那隻斷袖開始,金金金的數理化成績直線急下,而我的、媽媽的和爸爸的毛衣毛褲毛手套毛圍脖毛線滑冰帽還有毛襪子,一夜之間一應俱全起來。沒有人過問它們是怎麼來的,享用現成的東西比追詢其錯綜複雜的源頭要省力省時省心得多。我們一家三口選擇前者。
教務長是一個中年漢子,看上去還算五官端正,只是有那麼點兒糙。毫無疑問,美麗的舅舅像一切美麗的人兒一樣有些膽小。數理化老不及格,就有被開除的危險,而一心想開除他的,恰恰是這位一看到他的秀靨就皺眉頭的大男人。聰明的舅舅想出了一個極為世俗的辦法:送禮物給他,在過新年的時候。於是乎,堂堂漢子在新年前夜收到了一隻紅藍相間圖案的廚用手套。為了防熱,手套的作者還用麻布縫了一層厚厚的襯囊。手套的手背處,是紅色毛線所形成的三個字,「新年好」。對此,教務長著實義憤填膺了幾分鐘。多虧他的老婆把手套奪過去,高高興興地戴在左手上下了廚房。在此之前,他的老婆由於他的房事不濟,已經三年沒有下過廚房了。
新年之際同時收到毛織禮物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金金金金的同班同學,校草兼班級體育委員梅元華,他收到的是一條乳白色的長圍脖,另一個是大齡校草兼體育老師謝靜國,他收到的是一雙厚底兒毛襪子,顏色是藍黑色。教務長對此瞭若指掌。他沒有再動開除金金金金的念頭,但總用白眼看他,還在背後說,一聞到他身上的甜味兒腮幫子就泛酸水兒。
3
金金金金高中一畢業,就到棉紡廠去報名,還寫了一篇題為〈我的理想〉的附加材料,描述他對一幅幅鮮豔奪目的花布從自己的手中流水般淌過的人生境界之嚮往。他的申請理所當然被駁回了。駁回的理由簡明扼要:棉紡廠沒有男廁所、男浴池、男宿舍、男更衣間。於是,金金金金被安置進鐵路車輛段,負責提著小錘子在車廂與鋼軌之間走來走去,敲敲打打。檢查車廂的運轉部件是否受損,是否鬆動,是否會導致機車脫軌、人仰馬翻。
鮮豔欲滴的金金金金日漸喪失著水分。他手中的小錘子越磨越亮,常常被他抱在油汙制服的胸前,像我小時候被他抱在胸前一樣。有時候,他就那麼端莊地站在鋼軌之間發呆,懷抱著錘子,火車開過來都沒能在意。他的「故態復萌」,造就了八位捨身救人的英雄。他們不是他的年輕同事,就是車站上的工作人員。為此,他的另一個綽號又被從歷史的大霧中發揚出來。那個綽號是與「男阿信」同時誕生的,它叫「男瑪利亞」。沾他的光,我的名字也在這個時期,被同伴改唱成「龜龜」,他們隨口創編的前說唱體歌詞是:金金金金金,龜龜龜龜龜,龜是烏龜王八蛋的龜,龜是大龜頭的龜!
(……)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公廁電影院全年無休,日場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公廁電影院全年無休,日場
「對於之前讀過崔子虛構非虛構文學、看過他的影片的人來說,《公廁電影院全年無休》可能是本集大成作品。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部酷兒實驗媒介(包括文學、電影、廣播電臺)的現世神話文字呈現版。……超現實、『偽科幻』、萬花筒式的『排片』結構文體,或許令人眼花撩亂,但對愛與家的追尋和叩問,像一匹無軌火車頭,驅動著這本奇書穿越時空,奔向各種讀者。」──張真(紐約大學電影系教授、亞洲電影研究學者)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幽默與歡笑,是青春永駐、長生不死的祕訣;
尋求青春永駐、長生不死,精神上的輸入和肉體上的排泄同等重要!
我們有偉大的地下電影,同樣也有偉大的地下廁所!
你我鄰居男女老少同學老師愛人情人外星人孤兒混血兒活人死人,
人人都可能是公廁藝術家!
與那些熱愛公廁,在公廁中靈感大發的公廁藝術家們結為良伴,
在公廁電影院中把酒談論天下事,沖破/衝破各種邊界想像吧!
公廁電影院,全年無休!
日場凌晨五時起放映,想要入場,請在售票亭以紙巾付費──
----
旅美的中國獨立電影人、同志導演崔子恩跨越媒介形式的集大成之作,
與其獨立電影息息相關,以紙上電影院的形式把酷兒故事再說無數次!
作者簡介:
崔子恩
作家。獨立影人。
生於哈爾濱。曾長居北京。
現居北佛羅里達PVB。
章節試閱
廁所導航臺──
我的電影原型人物 金金金金
1
他生來面若桃花,甚至呼吐出的氣息都帶有一股奶與花蜜混合的香甜。年幼的時候,他是我的驕傲。那些年長的年少的三角城居民,都喜歡多看他幾眼,更貼近他一些,以便嗅食那種丁香花香味兒,並把它帶到夢裡。年長起來,他卻日漸腐壞,成了我的恥辱。他在三十歲的年紀上依舊面白脣紅、笑靨蕩漾,依舊渾身香氣,走起路來嫋嫋娜娜的樣子,只有說起話來聲音還算金屬。他的樣子如此顛覆,倒也不足為奇。對於民風淳樸的三角城來說,他畢竟是一朵土生土長的男性之花,除去早已進入傳說之外,...
我的電影原型人物 金金金金
1
他生來面若桃花,甚至呼吐出的氣息都帶有一股奶與花蜜混合的香甜。年幼的時候,他是我的驕傲。那些年長的年少的三角城居民,都喜歡多看他幾眼,更貼近他一些,以便嗅食那種丁香花香味兒,並把它帶到夢裡。年長起來,他卻日漸腐壞,成了我的恥辱。他在三十歲的年紀上依舊面白脣紅、笑靨蕩漾,依舊渾身香氣,走起路來嫋嫋娜娜的樣子,只有說起話來聲音還算金屬。他的樣子如此顛覆,倒也不足為奇。對於民風淳樸的三角城來說,他畢竟是一朵土生土長的男性之花,除去早已進入傳說之外,...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影像文學的馬拉松「放映」〉
文/張真
認識崔子恩有二十多年了吧。最早一次似乎是新世紀初,通過當時電影學系教學中心的工作人員江玫。江對跨太平洋華語酷兒社區比較熟悉,介紹崔子來紐約大學藝術學院放映。當年Tisch還沒有改建裝修,六樓布局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服裝工廠那磨損的黃漆細條地板。走道彎彎曲曲,黑乎乎的。二○○三年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崔子的專題馬拉松放映放了長短幾部,記得有《哎呀呀,去哺乳》、《丑角登場》、《舊約》和《霧語》。大教室裡基本坐滿了,討論也相當熱烈。活動後崔子還贈送了一套他的小說給...
文/張真
認識崔子恩有二十多年了吧。最早一次似乎是新世紀初,通過當時電影學系教學中心的工作人員江玫。江對跨太平洋華語酷兒社區比較熟悉,介紹崔子來紐約大學藝術學院放映。當年Tisch還沒有改建裝修,六樓布局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服裝工廠那磨損的黃漆細條地板。走道彎彎曲曲,黑乎乎的。二○○三年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崔子的專題馬拉松放映放了長短幾部,記得有《哎呀呀,去哺乳》、《丑角登場》、《舊約》和《霧語》。大教室裡基本坐滿了,討論也相當熱烈。活動後崔子還贈送了一套他的小說給...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影像文學的馬拉松放映/張真
廁位導航臺
05:00 am 燦爛公廁
06:30 am 四個外星人陷入劫匪圈
馬桶座裡
08:00 am 副歌
09:30 am 男妓萍生
咖啡座裡
11:00 am 公廁正方反方
12:00 pm 我如花似玉的兒子
午餐圓桌
01:45 pm 虛構
04:15 pm WC呼呼哈嘿
咖啡座裡
06:00 pm 哎呀呀,去哺乳
Q&A 自編自導自映自論的傲嬌里程I
廁位導航臺
05:00 am 燦爛公廁
06:30 am 四個外星人陷入劫匪圈
馬桶座裡
08:00 am 副歌
09:30 am 男妓萍生
咖啡座裡
11:00 am 公廁正方反方
12:00 pm 我如花似玉的兒子
午餐圓桌
01:45 pm 虛構
04:15 pm WC呼呼哈嘿
咖啡座裡
06:00 pm 哎呀呀,去哺乳
Q&A 自編自導自映自論的傲嬌里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