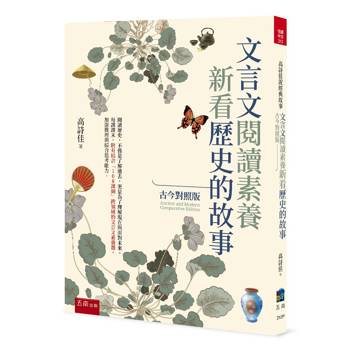第一章
掐死 按住喉部使窒息至死
那傢伙掐住我的脖子,拿我的頭撞地板,大概是決定不了,到底是要勒死我,還是想把我撞到腦袋開花。
若非如此,便是他厭煩了用一般的殺人方式。
我拚盡全力想甩掉他,但簡直自不量力。我,西羅‧麥克恩泰,人稱「電玩高手」,想撂倒這種大坦克?
想得美。
小蝦米鬥大鯨魚的勝算可能還大一些。老實跟你說,我能讓他眼球突瞠,已經很厲害了,至少表示我不是個澈底的廢物,他還是得花些力氣的。
若是換個時間,我頭側挨一記,八成就倒地不起了。這次本人死撐著不倒,唯一理由就是我太怒了。
我不是生他的氣,我是說,他多少在我的意料中,要不然他還能怎麼辦?這是我自找的。
我氣的是我老媽,都是她的錯,全得怪她。
她平常就那樣。
假若安德——那是我老娘的名字——不是那麼難相處,她十四歲時,便不會流落街頭了。
要不是她那麼——這麼說好了——漫不經心,就不會在十五歲時生下我。
要不是她那麼爭強好勝,也不必在二十五歲,硬要證明自己可以讀法律學院。
若不是她那麼吝嗇,也不會拖著我陪她去上所有夜間課程。(我是說,偶爾花十塊錢請保姆是會死嗎?她每天吃炸薯條都不只那個錢。)
如果她不是那麼杞人憂天,就不會逼我每晚陪她讀書了。
要不是她那個樣子,如果她只是個中規中矩的無聊媽媽,我就會對法律毫無所悉。
假如我一點都不懂法律,就什麼都不會說。
而我若什麼都沒說,這雙油兮兮的大手就不會掐在我的脖子上,我的腦子也不會在眼球後方彈跳,看見奇怪的白光,聽到男性天使呼喊著:「回家來吧,西羅!回來吧!」我應該在滑板場裡廝混,做一般十五歲小孩子會做的事:遊蕩閒晃。
老實說,我受夠安德打亂我的人生了,我不會再放過她了。我突然好想掐死她。
那大概正是我需要的吧。一個目標,一個能驅策我的東西。我突然橫勁一生,雖非超人的神力或類似的東西,但亦足矣。我把那傢伙的拇指扳開一兩公釐,我的氣管隨之一張,吸入一小股空氣,然後直盯住他的眼睛,說出我必須說的話。
「Res judicata.」(一罪不二審)
第二章
事實陳述書
事實的陳述以及相關法條,由申請、上訴、動議雙方各自提出。
五個月前。
我第一次看到道奇‧佛蓋爾跟安德在一起時,以為他要逮捕安德。
聽起來瘋狂,實則合理,我敢打包票,每個人都以為是那樣。我的意思是,誰不會那樣想?當你看見一名警察奔過大街,抓住某個穿著軍靴的瘦小女生時,自然會以為他要給她上手銬。
如果你是那個瘦小女生的孩子,自然覺得她一定是用手肘去撞警察的牙齒,在原本已有的罪狀上,再加一條「抗命拒捕」了。
你絕對沒有料到的是,警察竟用手臂圈住她的脖子,彎下他那顆碩大的頭,湊到她臉上,然後——我真沒有開玩笑——用鼻子去蹭她的耳朵。
假如安德抽身將那傢伙海扁一頓,那麼我還會覺得活在現實裡,可是她並沒有。
她也用鼻子蹭回去。
等我從震驚中回過神,我已經準備好去逮捕他們兩人了。刑事法中雖然沒有「蹭鼻子」罪,但應該列進去,畢竟裡頭有公然猥褻罪,更別提虐待兒童了。(如果看著兩名成人——其中一位是你老媽——在公共場所與人親暱,還不構成虐待兒童的話,我不懂還要怎樣。老實說,我懷疑那種情緒創傷會不會有癒合的一天。)
幸好安德抬頭換氣時,瞧見我站在那兒怒目瞪他們了。她就像被自己老爹活逮在門廊上跟人親熱似的,慌忙從那傢伙身邊跳開,然後努力眨眼裝萌,彷彿那麼做,看起來會很無辜。我只是搖搖頭,她以為我很好騙嗎?
她嗲聲嗲氣的用一副校長的語氣對我說:「唉呀,是你啊。哈囉,西羅。沒想到會在這兒遇見你。」
「妳沒想到?」我說,「我的意思是,剛才那場小演出,不是為我 演的嗎?」
她本想說「什麼?」,意思是「你這話是啥意思?」,但我忍不住咳笑一聲。我不會讓她輕鬆過關的,安德也很清楚這點。她調整衣衫不整的T恤,試圖擠出笑容。
我真的可以看到她的腦筋四處飛轉,打開各個抽屜,翻找墊子底下,搜遍口袋,想找個能對付我的辦法。
最後她轉向那傢伙,說道:「呃……道奇,這是我兒子,西羅。」
那傢伙的眼睛瞠到都凸出來了, 像憋住一大口嗝氣似的。「 兒子?」他說,「妳沒跟我說過妳有兒子。」
老媽的大實話顯然很不中聽。
她咬牙勉強笑道:「我當然提過呀!」她轉身站到男人面前,我看不到她的臉,但我太了解她了,安德一定是用她那對美麗的眼睛對他的腦袋作法,那是她的終極絕招,老媽能用那種眼神拔掉一個人的指甲,讓每個人變得服服貼貼。
那傢伙開始點頭說:「噢,對齁,那個兒子!當然當然!」他伸手想跟我握手,「你好啊,小傢伙!」
小傢伙!
有沒有搞錯。小傢伙?!
我算啥——小狗還什麼的嗎?這些大傢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平時沒事拿他們渾身筋肉的魁梧體格遮住我們的視線也就罷了,難道還要把我們當成小可愛嗎?
我故意讓他的手懸在空中,不予回應。一會兒後,他自討沒趣的聳聳肩,把手插到腰上(狀似本來就是要插腰的),然後說:「呃,我想我該走了,如果要準備今晚……呃……去那個……嗯,妳知道的。」
安德甚至沒看他,只是回道:「好啦,那就再見了吧。」
兩人雙雙揚起手,彷彿要做童子軍宣誓,接著安德轉身踏步離開,我仍能聞到她身上飄著那傢伙的古龍水味。那男的是怎樣,泡到古龍水裡了嗎?
安德抓住我的臂膀,裝出模範母親的樣子說:「唉呀……今天學校怎麼樣呀?」當我是很好哄的小可愛。
我寬宏大量,裝做沒事的微微笑說:「很有趣。我們討論了一些多年來,學者都無法解釋的謎題。」
「好酷——喔,例如什麼謎題?」老媽喜歡覺得自己生出一個坐在班級前排的聰明小孩。看到「蹭鼻子」事件後,你大概很難想像,但整體而言,安德把當媽媽這件事看得過於嚴肅,彷彿我是她的期末報告,就算犧牲掉我們其中一人,她也一定要拿A。
「噢,妳知道嘛。」我說:「諸如如何建造金字塔啦……恐龍遇到什麼事啦……或像安德‧麥克恩泰這樣的左翼瘋子,怎麼會跟警察約會之類的謎題。」
她當即翻臉,你都可以聽到模範母親的面具,碎在人行道上的聲音。她把嘴脣噘到鼻孔裡,怒目看我。「他不是警察!」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
「人家是副警長!」
「哦。了不起。」
她瞪眼大嘆一聲,朝我射來了一枚空氣飛鏢,我迅速矮身躲避。接著安德說:「西羅……福來德……麥克恩泰!你在法庭上待過那麼久時間,應該知道警員跟警長的區別吧!」
安德又要訓話了。這是她轉移話題最愛用的招數之一,我氣定神閒的任由她數落,反正我也攔不了。
「假如你有用心,就應該記得,至少在新斯科舍省,警長和副警長是治安人員,而非警務人員,他們是在法庭系統中工作的,負責執行法官的意旨,維護法庭秩序,護送犯人出入獄所之類的職務。反之,警員則負責調查犯罪、逮捕、處罰違返交通的人、在街上巡邏、處分噪音問題等等。」
她乾笑幾聲說: 「你絕對不會看到警長在街上親身參與那類事務。」
這太容易反擊了。
我說:「我覺得看來很像是在親自參與。」
這話刺到她痛處,老媽把嘴抿得死緊,活像氣球上的結。「這位先生,你給我聽好。」她說,「你不能那樣跟我說話,我是你母親,所以你嘴巴最好放尊重點!」
她竟然講出這種話?叫我?嘴巴放尊重?她感覺不出這話有多麼諷刺嗎?是誰會跟饒舌歌手一樣飆髒話?是誰三度藐視法庭?還有,噢,對了——是誰剛才用嘴巴去蹭某位警長的耳朵?
是不是!
「我是說真的!」她表示,「所以你最好放聰明點,對了,」——她走在前方,這樣就不必看我的臉了——「你得幫我辦一件小事,伊克博檔案的事實陳述書得在明早之前寫好。」
我得先打住,解釋一下。
你大概發現了,安德這個人超級帶種,不僅有膽量、正義感、勇氣、拚勁,她的膽氣濃到都要從耳朵裡噴出來了。不是真的噴啦——但至少大部分時間如此——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了。
有時那樣很好。
比如說,若非安德鼓起勇氣把胖房東告上法庭,老柴德先生和他那二十二隻貓只怕要露宿街頭了。
安德若沒種去告潔淨乾洗店,只怕他們還是會把不怎麼潔淨的汙染物倒到港口裡。
還有,老實告訴你,要不是安德有膽氣獨自扶養孩子、讀法律學校、讓母子兩人有飯吃,不太惹麻煩,那麼今天的我,大概會住在寄養家庭了。我要強調的是「不太」兩個字。
安德的帶種也有不好的一面。
例如,被我活逮她跟男人在大街上親熱,竟然還有臉跟我說,我必須整晚待在家裡幫她工作。
拜託好不好,說真的,應該被禁足的人,不是我吧。
我突然感受到綠巨人浩克要爆裂襯衫前的狂怒了,我澈底抓狂的說:「休想,安德!那是妳的工作!」
「本來是,現在變成你的了。」語氣彷若送我禮物。
「為什麼?」
「因為我沒法做,我很忙。」
「我就不忙嗎?相信我,我還有比坐在家裡,幫妳整理法律文件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哦,是嗎?例如什麼?」她轉頭狐疑的看著我,像是逮著我做壞事。
我絕不會讓她翻盤得逞,她這招在法庭上也許有用,但在這裡休想奏效。
「少來,」我表示,「我絕不說,妳先講。妳今晚到底什麼事那麼重要,讓妳無法親自寫那份陳述書?」
她撥弄手上的戒指,伸出手,檢視自己的指甲。(你會以為她斑駁的黑色指甲油,是故意弄出來的。)安德清清喉嚨,「呃,我有……嗯……」
「停,別說,我來猜。」我說,「我今晚,有,呃,一點小事。」
她開始在皮包裡找菸。「不對!」她說,「不是那樣。你怎會那麼想?只是呃……唉呀,對不起。等我一下,我點個菸……這真是個壞習慣……我真應該……」
我再也忍不住了,便說:「妳別再拖拖拉拉了行嗎?你我心知肚明,妳今晚要跟那個傢伙出去!」
她從菸上抬眼睨著我,舔舔手指,噗一聲把火柴掐熄。看她的表情,我猜她把火柴當成我的頭了。
我說:「妳何不請雅圖拉幫妳寫陳述書?她是律師,是妳的合夥人,去請她寫。」
她彈掉菸上的灰,垂眼看著街道,好像突然不確定她的公車在哪裡。安德說:「我不想那麼做,你知道我不喜歡打擾她。」
最好是工作進度再次落後,然後不去「打擾」她啦!不,雅圖拉一定不喜歡那樣,一點都不會喜歡。律師事務所裡只有她們兩人在管,破舊的小辦公室就在葛庭根街一間炸魚薯條店的上面。她們有太多客戶遇到一堆問題,景況淒涼,因此工作絕不能堆積,這一點雅圖拉很早就知道了,安德怎麼還不懂?
憑什麼我得擔心那些垃圾事?她是母親,是律師耶,我只不過是個孩子。我應該要擔心自己的膚況(我確實挺擔憂的),煩惱女生的事(我也有),學校的課業(我還好,至少沒有很擔心)。這是大人的事,太不公平了。
更不公平的是,我甚至不能讓她看出我的擔心。當時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讓安德擔心我在煩惱,那會使我更加憂慮。我只有一個選項:
按捺住,做自己必須做的事。
我回身開始像《法律與秩序》影集中,對陪審團說話的大牌出庭律師般來回踱步。「我看我有沒有說對,妳要我花一整個晚上,在妳的一份檔案裡,撰寫法律陳述書——沒錯,是妳的檔案——好讓妳跟妳的警察男友出去玩?」
老媽聽了大抓狂。「我跟你說過,他不是警察,還有順便告訴你,人家不是我男朋友!我們只是……呃,朋友而已。」
「好吧。」我說,知道她在撒謊,她若不是被戳中了,絕不會那麼生氣。「我的媒體藝術課有份錄影作業,我今晚要開始做,可是沒關係,妳甭擔心,沒問題。我會幫妳寫陳述書。」
她眼中的詭異橘光熄掉了,鼻孔裡不再滲出有毒的菸氣。安德眼中泛光。
「真的嗎?噢,西西!我就知道我可以信得過你!」她抽出嘴裡的菸,用雙臂環住我的脖子,開始在我臉上亂親一通。我最討厭她這樣了,我若沒被那種尷尬或二手菸的氣味給弄死,也會被她的鼻釘戳掛。
我把她從身上剝開。「好啦好啦好啦,妳別再放閃了,把熱情留給穿警察制服的先生吧。」我說,「我話還沒說完,如果妳答應幫我買新的長滑板,我才幫妳寫陳述書。」我覺得我應該得點好處。
她踉蹌後退,張嘴惱怒的看著我,像是嗆到骨頭,安德甚至發出乾嘔的聲音。
「你是在勒索我嗎?!」她說,「勒索你的親生母親?!」
我停下來想一會兒。「 是啊。」 我接著說, 「 妳那樣講也不算錯。」
她又被那根骨頭噎到了。「不可思議!我簡直……簡直……說不出話!我們是家人耶!家人要相互幫助!」
「沒錯。」我說,「這正是我想說的。我幫助妳撰寫陳述書,讓妳今晚跟警長大人去﹃那個』。妳可用撰寫陳述書的一部分費用,幫我買個滑板。有些人或許稱之為勒索,但我稱之為公平的使用者付費。」
安德露出無招可用時的扭捏動作,她重重抽了口菸,準備破口大罵,但我們倆都知道任她再怎麼飆罵都沒有用,因為她根本站不住腳。
「好。」她說著從嘴角噴出一道菸。「罷了罷了。總有一天,當你回顧此事,一定會跟我此刻一樣感到震驚。你會驚駭的憶起,自己竟然未能感念這份良機,為一個善良的家庭服務,讓他們免於被遣回飽受戰火蹂躪的家園,反而從中謀取私利。你完全沒有顧慮到你的母親為了賜予你現今擁有的生活,做了多少犧牲,她愛你勝過世間任何一切啊。不,那些你全都不在乎,你看到快速致富的機會,便撲了上去。罷了,我相信有一天你會夠成熟,會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寒心。我將耐心的等候你來道歉。」
真愛演,安德會耐心等候才怪。你真該看看她在爆米花爆好時,衝向微波爐的那副德性,就像水裡嗜血爆衝的食人魚。
「你給我把陳述書寫好——要按照我的標準!然後我就可能幫你買個蠢滑板。」
大部分小孩應該會滿意了,但本人不然。我很清楚自己的對手是誰,安德跟所有優秀的律師一樣,一定已經在找破綻了。
我絕不會讓她得逞。
我打開背包,拿出從學校媒體室借來的錄影機,要她重述剛才的允諾,並叫她把手伸出來,確定她的手指沒在背後打勾(譯注:一種手勢,意為「請上帝原諒我撒謊」)。我甚至要一名路過的女孩當證人,並錄影存證。
這下子安德絕對無法賴帳了。
我一路雀躍回家。
我從不知道,原來敲詐勒索這麼有趣。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少年偵探法律事件簿(2):一罪不二審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少年偵探法律事件簿(2):一罪不二審 作者:維姬.葛朗特 / 譯者:柯清心 出版社: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0-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少年偵探法律事件簿(2):一罪不二審
充滿動作、冒險、懸疑、刺激的青少年偵探小說
我是西羅,老是被捲入老媽安德接到的法律委託案件中。果不其然,這次她又給我招惹了大麻煩,害我差點英年早逝。
話說那天原本只是看到一則「救火英雄清潔工解救知名科學家,卻被控過失致死」的新聞報導。哇!富人對窮人的抗爭!這根本是老媽的夢幻官司,她自以為是正義化身,免費幫那位清潔工打官司,還打贏了。而我則打算利用這個案件作為學校作業主題,過程中卻發現前後不一的蹊蹺……
這對非典型母子,這次又會遭遇到什麼棘手案件呢?
西羅又會如何利用他的觀察力與邏輯力破解謎團呢?
【本書特色】
★ 加拿大資源鏈接年度最佳圖書獎優等獎
★ 加拿大亞瑟‧ 艾利斯最佳青少年犯罪小說提名
★ 加拿大馬尼托巴青年讀者選擇獎決選
★ 加拿大兒童圖書中心最佳童書獎
作者簡介:
維姬‧葛朗特(Vicki Grant)
被譽為「超級會說故事的人」(加拿大兒童圖書中心)以及「今日最有趣的作家之一」(溫哥華太陽報)。她曾獲Red Maple FictionAward、亞瑟‧艾利斯推理文學大獎、加拿大廣播公司讀書節獎,並曾入圍愛倫‧坡獎、加拿大圖書館學會年度好書獎等等。她的小說被譯成15種語言,在全球超過20個國家出版。英國名出版——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的編輯Emma Matthewson如此評論她的小說:我已經很久沒有讀到如此尖銳、有趣、大膽的故事。其著作《等價交換》獲得加拿大亞瑟‧艾利斯最佳青少年犯罪小說、入圍愛倫‧坡獎決選名單。
【繪者簡介】
Tseng Feng Art
平面設計師,偶爾利用空餘時間來作畫。喜愛穿梭於臺灣山林間,感受來自大地的純粹,作為繪畫的靈感來源。以尋找臺灣特有元素,創作出具有文化脈絡的作品為目標。希望能將她的美及我對她的想像,傳遞給其他人。
譯者簡介:
柯清心
臺中人,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現任專職翻譯。譯有:《枴杖男孩》、《夏日大作戰》、《我愛,故你在》、《換身》、《兒子的謊言》(幼獅文化出版)等數十部作品。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掐死 按住喉部使窒息至死
那傢伙掐住我的脖子,拿我的頭撞地板,大概是決定不了,到底是要勒死我,還是想把我撞到腦袋開花。
若非如此,便是他厭煩了用一般的殺人方式。
我拚盡全力想甩掉他,但簡直自不量力。我,西羅‧麥克恩泰,人稱「電玩高手」,想撂倒這種大坦克?
想得美。
小蝦米鬥大鯨魚的勝算可能還大一些。老實跟你說,我能讓他眼球突瞠,已經很厲害了,至少表示我不是個澈底的廢物,他還是得花些力氣的。
若是換個時間,我頭側挨一記,八成就倒地不起了。這次本人死撐著不倒,唯一理由就是我太怒了。
我不是生他...
掐死 按住喉部使窒息至死
那傢伙掐住我的脖子,拿我的頭撞地板,大概是決定不了,到底是要勒死我,還是想把我撞到腦袋開花。
若非如此,便是他厭煩了用一般的殺人方式。
我拚盡全力想甩掉他,但簡直自不量力。我,西羅‧麥克恩泰,人稱「電玩高手」,想撂倒這種大坦克?
想得美。
小蝦米鬥大鯨魚的勝算可能還大一些。老實跟你說,我能讓他眼球突瞠,已經很厲害了,至少表示我不是個澈底的廢物,他還是得花些力氣的。
若是換個時間,我頭側挨一記,八成就倒地不起了。這次本人死撐著不倒,唯一理由就是我太怒了。
我不是生他...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善與惡的距離————《一罪不二審》拉出了真假虛實的辯證
◎許建崑(兒童文學文字工作者)
作者維姬《等價交換》獲獎兩年之後,續集《一罪不二審》問世,主角西羅跟著長了兩歲。在這回故事中,媽媽安德結交男朋友道奇,是鎮上的副警長。她忙於約會,要求西羅幫忙撰寫出庭用的「陳述書」。西羅嫉妒「入侵者」,故意去更改副警長的名字為「畢夫」;副警長卻不以為意。抓住機會,有「畢夫」當靠山,西羅動念去「勒索」媽媽,好得到嶄新的滑板。
然而,安德看見報紙上一則新聞:法院打算控告英雄清潔工查克過失殺人。怎麼會從「英雄」...
◎許建崑(兒童文學文字工作者)
作者維姬《等價交換》獲獎兩年之後,續集《一罪不二審》問世,主角西羅跟著長了兩歲。在這回故事中,媽媽安德結交男朋友道奇,是鎮上的副警長。她忙於約會,要求西羅幫忙撰寫出庭用的「陳述書」。西羅嫉妒「入侵者」,故意去更改副警長的名字為「畢夫」;副警長卻不以為意。抓住機會,有「畢夫」當靠山,西羅動念去「勒索」媽媽,好得到嶄新的滑板。
然而,安德看見報紙上一則新聞:法院打算控告英雄清潔工查克過失殺人。怎麼會從「英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掐死
第二章 事實陳述書
第三章 擾亂治安
第四章 童工法
第五章 過失致死
第六章 起訴書
第七章 藐視法庭
第八章 惡意控告
第九章 補償金
第十章 推論無效
第十一章 傳票
第十二章 遊蕩
第十三章 逮捕
第十四章 被害人影響陳述書
第十五章 證明
第十六章 傷害
第十七章 竊盜罪
第十八章 間接證據
第十九章 上訴
第二十章 驅逐
第二十一章 惡意詐騙
第二十二章 竊聽
第二十三章 脅迫
第二十四章 冒名頂替
第二十五章...
第二章 事實陳述書
第三章 擾亂治安
第四章 童工法
第五章 過失致死
第六章 起訴書
第七章 藐視法庭
第八章 惡意控告
第九章 補償金
第十章 推論無效
第十一章 傳票
第十二章 遊蕩
第十三章 逮捕
第十四章 被害人影響陳述書
第十五章 證明
第十六章 傷害
第十七章 竊盜罪
第十八章 間接證據
第十九章 上訴
第二十章 驅逐
第二十一章 惡意詐騙
第二十二章 竊聽
第二十三章 脅迫
第二十四章 冒名頂替
第二十五章...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