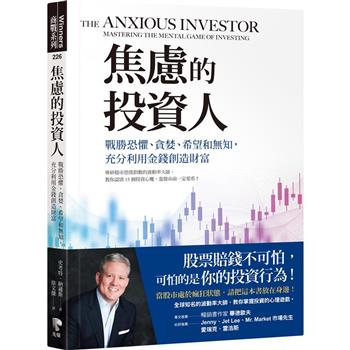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前言】
公民行動的起點,是言論自由 / 陳夏民
在臺灣,每年4月7日的言論自由日已是國定紀念日,用以紀念《自由時代》雜誌總編輯鄭南榕為追求百分之百的自由,而於雜誌社自焚殉道的無畏精神。
鄭南榕所追求的百分之百的自由是什麼呢?最關鍵的就是「言論自由」。如今,身在臺灣,言論自由的空氣彷彿是天經地義,甚至有許多人誤以為言論自由就是可以隨便罵人的權力,直到收到對方的存證信函,才發現自己完全誤認,以致幻想出一個充滿破洞的保護傘,招惹麻煩。
翻開鄭南榕所出版的《自由時代》雜誌的目錄頁,經常可以看見一個文責聲明的小框框:「本刊文責一律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目錄頁數不詳具作者姓名。」這一個小框框,在雜誌早已停刊的今天,依舊體現了百分百言論自由的真諦:我為我這本雜誌所表達的一切,負上全責;也因為這是我所出版的雜誌,我會保護作者,不讓他們遭受國家機器監控,若有任何因為文章而生的訴訟或衝突,都由我來負責。
鄭竹梅曾說:她在以女兒,直系親屬身分,申請並觀看了當年監控父親鄭南榕的情治機關檔案後,發現有一份報告,上頭寫著:「鄭南榕在雜誌上表明本刊文責一律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有悲劇英雄的傾向。」而高達千頁以上的監控檔案,那些鉅細靡遺的瑣碎資料與對鄭南榕及其周邊人士的各式(加上奇怪濾鏡的)詮釋,一方面讀來無比荒謬,卻又有一種奇異的真實感。
對同一句話或同一個人,有不同的解讀,這不也投射出了人類自有語言以來,始終面對著的,無法百分之百溝通理解的困境嗎?
而這樣的困境,在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情況之下,更會助長極權統治者的管控系統,使其透過各式媒介,去製造出美好卻無比真空的假象,透過文字縫隙所蔓生的恐懼,將人民玩弄於股掌之間。例如:甫通過國安法的香港,如今就有許多出版人或創作者開始自我審查,畢竟在沒有明顯界線的規範之下,只要有人皺個眉頭,你的言論就可能招罪。自我審查只會讓恐懼無限擴張,到最後讓人自然而然局限自身表達。
鄭竹梅提到,翻閱那些檔案時,彷彿身陷迷霧,不知道什麼才是真實。畢竟在監控人民的時代,每一個眼線都有自身對受監控者的解讀,有些時候,甚至可能為了「業績」而產生更多虛構的成分。在那樣極端的時空,任何一個人的人生,隨時都可能變成一部悲劇性的短篇小說,說不出足以標榜自身存在與思想的台詞。但也因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鄭南榕會主張:「所有的自由裡,第一個應該爭取的是言論自由,有了言論自由以後,才有可能保住其它的自由。也就是說,爭取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後,我們還有其它諸多種類的自由尚待爭取。」
言論自由,是任何一位公民想要推動、改革社會時的最基本配備。
這也是鄭南榕極力爭取的,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自由。在未得自由之前,鄭南榕便採取行動,透過出版一本又一本的雜誌與叢書,點燃了全臺灣各地企盼真相者的求知心,從出版、印刷、發行、通路和讀者,各地星火串起了一段隱匿於獨裁政權壓迫縫隙的資訊流(information flow),讓更多人寧願在租書店租借包裹在腥羶色雜誌內的《自由時代》雜誌,被認成色色的大人也無所謂,只為獲得雜誌的內容啟迪。在那個分不清楚周邊是否藏著監控者眼線的時代,每一個懷抱著信念的人,只能憑藉直覺與信任努力求生,如履薄冰的扮演這一段如奧運聖火傳遞的中介。數十年後,他們的努力,終於換來我們自由言說的可能。
如今,我們所處的時空背景,甚至比鄭南榕當時所處的更加複雜。畢竟「光是2015一年產生的資訊量,就超過人類有史以來到2014年之資訊量的總和。」(註釋:引用自黃哲翰專文〈數位利維坦君臨的前夕〉,端傳媒),更不用提臺灣、美國在選舉時所遭逢的境外假新聞侵擾,只要想要,任何一個影像單位都可以輕易合成任何一個人出現在任何場合的虛構足跡。所有國家之間的角力,早已不再只是軍事展演秀肌肉,而是透過各式各樣的娛樂手法或科技產品,在每一個人眼下上演,甚至讓我們透過參與娛樂或是貪圖便利,雙手奉上自身珍貴的隱私。更不用提諸多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其實也對消費者的隱私與生活上所享有的各式權利虎視眈眈......
我們生活在一個超級複雜的世界。然而,就算身陷意識形態的迷霧之中,不知道所見所聞何者為真,只要擁有信念,願意為認同的信念背書,並且成為其中介,去說、去談,同時擔負起責任,那麼我們終究有機會去挑戰他者所強加在我們面前的假象,稍微「逼近」真實。
自由的言說,賦予我們探索真實的能力,而正是極權統治者或是有心人士所懼怕的。為此,我們必須繼續表達意志與信念,也必須時時刻刻警惕自己,即便有些人的語言美好如天使的祝福,讓人忍不住身陷其中,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夠讓理智斷線,不經思索的輕信他者。
在鄭南榕殉道三十年後,當我們重新思考言論自由,其積極的意義是讓我們成為中介:我們必須繼續閱讀,繼續表達,繼續負責,繼續去傳遞我們所深信的價值。
不要讓美好未來的種種可能,斷在我們這裡。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讀而自由:安頓身心的12堂公民行動課的圖書 |
 |
讀而自由:安頓身心的12堂公民行動課 作者:陳夏民編者 出版社: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4-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讀而自由:安頓身心的12堂公民行動課
由長期關心社會運動與各項議題的獨立出版人──陳夏民,精心挑選12篇不同議題的選文,分別對應:個體、周遭、世界,由近而遠三個層次,讓讀者可以對在各種資訊滿天飛,新聞版面天天都是議題的時代,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各種狀況,有更深層的理解跟認識,並透過陳夏民在每篇文章所撰寫的:主編思辨,引導讀者有更多思辨的角度看待文章中的主張,每篇選文前皆有介紹引言,讓讀者對文章所討論的議題有基本的認識,在每篇文章最後,有思考練習,激發讀者看文章後磨練自己的思辨力。
【本書特色】
˙本書從個體出發,至生活周遭,再與世界接軌。帶領讀者認識自己的權力,並發現身邊未曾意識到的權力,進而形成足以改變世界的力量。
˙本書探討社會上的各種議題,面向多元,包括:性別、性向、種族、環境保育、公民運動等,藉由閱讀選文引導,為抽象概念注入具體的解析,帶領讀者思辨社會的各種現象。
˙針對各項議題,精心設計開放性的問題,適合師長與學生相互討論,建立獨立的觀點,培養論述的能力。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陳夏民
桃園人,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創作組畢業,曾旅居印尼,現任「逗點文創結社」創辦人暨總編輯、大愛臺《青春愛讀書》選書顧問,與夏宇童共同主持Podcast節目《閱讀夏LaLa》。
著有《失物風景》、《主婦的午後時光》(與攝影師陳藝堂合著)、《讓你咻咻咻的人生編輯術》、《那些乘客教我的事》、《飛踢,醜哭,白鼻毛》;譯有海明威作品《太陽依舊升起》、《我們的時代》、《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海明威短篇傑作選》及菲律賓農村小說《老爸的笑聲》。
臉書專頁:陳夏民,你的人生編輯
作者序
【前言】
公民行動的起點,是言論自由 / 陳夏民
在臺灣,每年4月7日的言論自由日已是國定紀念日,用以紀念《自由時代》雜誌總編輯鄭南榕為追求百分之百的自由,而於雜誌社自焚殉道的無畏精神。
鄭南榕所追求的百分之百的自由是什麼呢?最關鍵的就是「言論自由」。如今,身在臺灣,言論自由的空氣彷彿是天經地義,甚至有許多人誤以為言論自由就是可以隨便罵人的權力,直到收到對方的存證信函,才發現自己完全誤認,以致幻想出一個充滿破洞的保護傘,招惹麻煩。
翻開鄭南榕所出版的《自由時代》雜誌的目錄頁,經常可以看見一個文責...
公民行動的起點,是言論自由 / 陳夏民
在臺灣,每年4月7日的言論自由日已是國定紀念日,用以紀念《自由時代》雜誌總編輯鄭南榕為追求百分之百的自由,而於雜誌社自焚殉道的無畏精神。
鄭南榕所追求的百分之百的自由是什麼呢?最關鍵的就是「言論自由」。如今,身在臺灣,言論自由的空氣彷彿是天經地義,甚至有許多人誤以為言論自由就是可以隨便罵人的權力,直到收到對方的存證信函,才發現自己完全誤認,以致幻想出一個充滿破洞的保護傘,招惹麻煩。
翻開鄭南榕所出版的《自由時代》雜誌的目錄頁,經常可以看見一個文責...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編序 公民行動的起點,是言論自由/陳夏民
PART 1看見個體
01逃難下的婚姻,一位新住民女孩的落地生根
單程機票/陳又津
02從顏色的選擇來思考「刻板印象」帶來的限制
顏色的性別意義,是人類社會賦予的詮釋/苗博雅
03每個人的身體,都值得被自己喜歡、被自己善待
胸部的安放法則/李屏瑤
04誰規定這樣才是MAN?
猛男與宅男的世界盃——男性氣概是什麼?/陳子軒
PART 2看見周遭
05數位的便利,考驗著我們與惡的距離
「線上仇恨」的起源:為何我們在網路上失控?/黃哲斌
06工作需要什麼?自由還是保障?
零工經濟是好經...
PART 1看見個體
01逃難下的婚姻,一位新住民女孩的落地生根
單程機票/陳又津
02從顏色的選擇來思考「刻板印象」帶來的限制
顏色的性別意義,是人類社會賦予的詮釋/苗博雅
03每個人的身體,都值得被自己喜歡、被自己善待
胸部的安放法則/李屏瑤
04誰規定這樣才是MAN?
猛男與宅男的世界盃——男性氣概是什麼?/陳子軒
PART 2看見周遭
05數位的便利,考驗著我們與惡的距離
「線上仇恨」的起源:為何我們在網路上失控?/黃哲斌
06工作需要什麼?自由還是保障?
零工經濟是好經...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