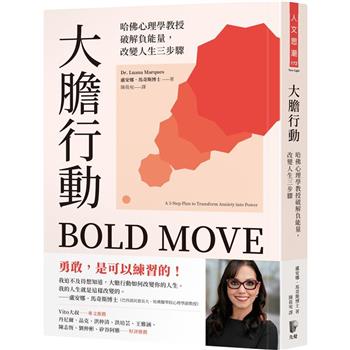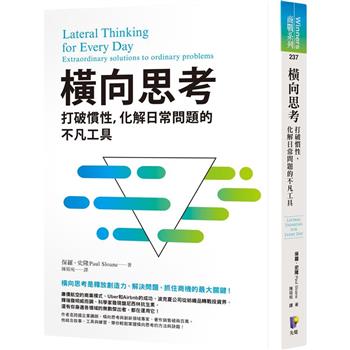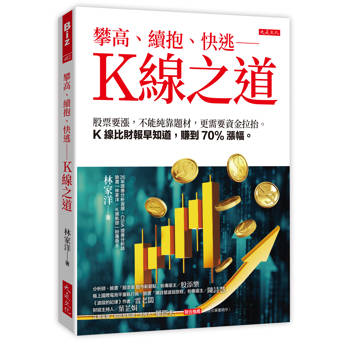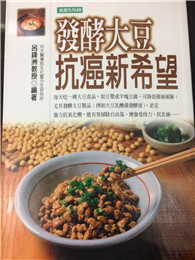畸零之人,畸零之地,畸零的情感……
新銳小說家盧慧心擅寫畸零心事,最扭曲、最平凡的故事全都在她筆下綻放異彩……
新銳小說家盧慧心擅寫畸零心事,最扭曲、最平凡的故事全都在她筆下綻放異彩……
盧慧心,一個新鮮初綻的名字,筆下文字卻熟成迷人,她歷經多年錘鍊、從容打磨,終於在近年間迅速嶄露頭角,兩年內連獲五大文學獎肯定,包括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大獎,並連續兩年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這本集子萃選她從二○○三到二○一五之間的十幾篇作品,也是作者二十三歲到三十五歲間這段人生跨度裡的創作精華。她的小說兼具引人入勝的可讀性與精緻的文學性,在華文文學領域中是不可多得的新穎珠玉。
這本小說集收入的小說,都跟命運有關,而命運有定數也有變數,作者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牽引,是命運最大的變數。金融風暴、戰爭爆發,乍看是飛來橫禍,但其實有前因後果,只有感情真的毫無規則,沒有所謂的「該怎麼樣」,而這些變數,就是人生的滋味吧。
《安靜.肥滿》書裡就是如此充滿著人生的滋味,盧慧心說故事總能另闢蹊徑,緩緩穩穩地創造出一個安靜、自在的小說結界,這裡面收藏著因感情、家庭而毀壞的都會男女,也收藏著貨運工人、拾荒者之子、爆炸案倖存者,以至於遊民浪人的故事,無論鰥寡孤獨、肥胖、憂鬱者皆有所屬。作者深受畸零之人、畸零之地吸引,筆下想要描寫的人物都是世俗眼光中被視為無足輕重的、多餘的,這些人或許與幸福人生相隔遙遠,她卻感覺與他們心靈相通,於是以小說收藏那些多出來的人、多出來的東西所散發出的珍稀光芒。
盧慧心曾說,「寫作是靜態的冒險,每次孤注一擲都是值得的,最壞的可能就是寫出些不怎麼樣的東西,但不論作品傻不傻氣,總伴隨著創造的快樂。」
本書特色
★ 本書獲選文化部一○四年藝術新秀創作。
★ 短篇小說創作,多篇為文學大獎桂冠之作
名人推薦
紀大偉、黃麗群、柯裕棻、賴香吟、隱匿 一致推薦
在過於迷信敘事的此時此刻,掙脫敘事的枷鎖反而可以讓許多藝文工作者突破瓶頸。《安靜.肥滿》讓我覺得清新可喜,……在崩世代度小月的時代,安靜肥滿不是自暴自棄的敘事,而是大智若愚的境界。──紀大偉
「她說故事沒有忿恨也無鄙棄,真實得嚇人。但她常說她自己滿口謊言,說謊成性。她或許真的擅長哄騙,謊言說得那麼真誠,讀著讀著很難不把心掏出來。可她又不讓你流淚,她讓你自己看個明白。」──柯裕棻
平滑乾淨的材質,像上等的大明火琺瑯,或者老瓷器,不惹眼,不冒賊光,我非常希望她能一直一直地寫,在這海上她是一尾奇行的飛魚,只此一隻,別無分號。──黃麗群
「〈一天的收穫〉與〈車手阿白〉皆取材非典型人物,不從明確關係下手,轉攻各種懸宕、捉摸不定的人與人狀態,編寫不在讀者期待之中的劇情。文字以畫面感見長,深諳如何以情境造情緒,勤於探勘尚未被寫到陳腔濫調的情感癢處,加以當代日常生活細節,瞬間感受,直戳讀者共感,對白也特別機靈,小說閱讀總不落入冷場。」──賴香吟


 2016/01/13
2016/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