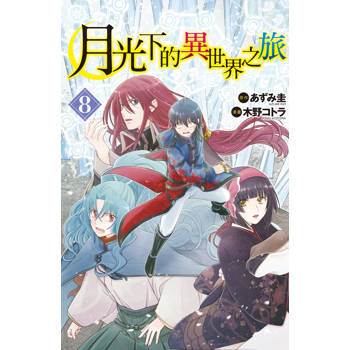顧燕翎長期從事婦女運動、婦女研究,她不只是一個研究學者,也是實踐者,親身參與許多婦女運動,甚至到菲律賓、肯亞奈羅比、俄羅斯聖彼得堡參加國際會議,與世界各地婦女討論女性議題,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為追求女性平等而努力。在偶然的機緣中知道「女書」,這個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還走訪發源地。不論女性主義是主流或非主流,顧燕翎仍堅定的實踐自我核心價值,走出一位女性主義者不凡的行腳。
顧燕翎將女性主義精神實踐在生活中,化身為俠女,仗義執言,在學校為學生爭取權益。當擔任政務官時,她既溫柔又剛強,改變辦公環境,並深入社會底層,關心弱勢、遊民與老人,還關注殯葬這個人人迴避的領域,近身探觸死亡,貼近生命的核心。
她也回歸自身,透過文字找回對文學的初戀,舞動身軀、開口唱歌,體現自在生活,面對疑似生病虛驚的考驗,讓她在生命的細縫中求生,因她最愛的外婆胸懷壯志在時代和性別的因素下,被迫被綁小腳,扮老,侷限人生,這讓顧燕翎更堅持把握每一天豐富自己的人生,開出美麗的花朵。
本書特色
★顧燕翎以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角度切入,用文學的筆寫下生命歷程中不同的經驗,不論是與學生相處、受邀進入台北市府擔任政務官,或是參與女性主義活動、面對病痛的考驗,都可看見她獨樹一格的觀點。
名家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作家平路;名家王瑞香、朱恩伶、范情;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張小虹、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黃長玲、高雄醫學大學語言文化中心講座教授蘇其康 聯合推薦
王瑞香(自由寫作者)
台灣第一位女性主義政務官懷著和初戀(文學)重逢的激情,寫下她人生中於學術、運動、官場等領域裡的獨特經歷與心得。這本近似自傳、側重作者涉身婦運與官場之心路歷程的文集,既看得到上乘的散文(如〈市場:生命的交會點〉)和第一手的婦運記錄(如〈芝加哥之怒〉)與直言不諱的官場觀察(如〈改變成真〉),更有作者在世界各地結緣之婦女的動人故事(如〈拎著水桶坐公車的女人〉),以及她對生命的觀照(如〈生命的縫隙〉),豐富且深刻。
朱恩伶(翻譯工作者)
燕翎的文筆清新,情思細膩,天性樂觀,對女性主義情有獨鍾。在豐富的一生中,她曾積極從事大學教育,熱情參與婦女運動,勇闖政治叢林,體貼關懷弱勢,盡力推動社會改革,留下一位女性主義者不凡的行腳。回首來時路,只見雲淡風輕,往日的點點滴滴悉數化為鮮活動人的故事,洞悉世情,屢屢在生命的縫隙看見光,恰如她所言:「處處意外,卻也處處驚喜。」我在字裡行間,讀到她溫暖、熱情、幽默、深省、睿智、豁達、永不放棄希望的真性情,真是文如其人,躍然紙上。
張小虹(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生命的縫隙無預警乍現,就此打開了台灣知名婦運學者顧燕翎的散文創作新起點。《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從最貼身的人事物寫起,文字精準簡潔、情真意切,滿是閱世的寬厚與理解,處變中的隨緣與自在。這是一本女人寫給女人、女人鼓舞女人的書,讓我們忍不住邊讀邊歡喜讚嘆,原來在生命的每一個轉角處,都可以像她一樣舞蹈歌唱。
蘇其康(高雄醫學大學語言文化中心講座教授)
乍看書名似乎不易摸著邊,但全書三輯「隙縫中看見生命」、「愛上女性主義」和「勇闖政治森林」全都是有深意的經驗談:在日常生活中反映思辨、在旅途中思索歷史、文明和制度,在公部門中推動人性化的公平正義和女性思維,此外,還有奠基環保的生機飲食介紹。這三輯文字雋永、洗鍊中有文學味道,充分反映作者的背景。顧燕翎大學時代唸台大外文系,雖然一度猶豫自己真正的興趣,但文學細胞尚在;當過「大學新聞社」的記者,觀察入微的歷練早已開始,又當過外文系系學會的會長,是我非常敬佩的班上女中豪傑。
四十多年的情誼,面對好文章,讓我們一起欣賞《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10 |
散文 |
$ 237 |
現代散文 |
$ 237 |
文學作品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270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顧燕翎
生於南京,成長於岡山,求學於台北、美國,長住於新竹。
一九七○年代開始投身婦女運動、任教交通大學,曾協同創辦婦女新知基金會、台大婦女研究室、女書店、台灣銀領協會等民間團體。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八年分別以《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性主義經典》獲得聯合報十大好書獎。之後任職台北市政府,擔任公訓中心主任及社會局長,自此熱衷從不同社會角度整合公共政策。二○○六年獲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頒贈家庭價值獎,二○○九年獲得梁實秋散文獎。
顧燕翎
生於南京,成長於岡山,求學於台北、美國,長住於新竹。
一九七○年代開始投身婦女運動、任教交通大學,曾協同創辦婦女新知基金會、台大婦女研究室、女書店、台灣銀領協會等民間團體。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八年分別以《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性主義經典》獲得聯合報十大好書獎。之後任職台北市政府,擔任公訓中心主任及社會局長,自此熱衷從不同社會角度整合公共政策。二○○六年獲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頒贈家庭價值獎,二○○九年獲得梁實秋散文獎。
目錄
名家推薦
自序 鐵杵磨成繡花針
輯一 縫隙中看見生命
初戀文學
三十歲的老太太
足下
她的名字叫罔腰
媽媽桑
生命的縫隙
祈 禱
舞 緣
我舞故我在
乘著歌聲的翅膀
爸爸的老友
望德園便當
我愛台灣
公車上
消失的小火車
拎著水桶坐公車的女人
黃土高原散客行
古城芳鄰
小鎮大會
赤道上
星空的祕密
市場——生命的交會點
觀雲聽風山林間
輯二 愛上女性主義
愛上女性主義
女人、知識與書寫
飛向奈羅比
走過三世紀的老牌女青運動
千里紅線女書情
芝加哥之怒
聖彼得堡夏夜
「超越。愛」的見證
山豬溫泉
環海公路
山在虛無縹緲間
綴連台灣的人
看見
無聲的吶喊
輯三 勇闖政治叢林
跳進兔子洞
生之慾
改變成真
武崗的春天
都市的漂泊者
我只是眼睛看不見
老吾老
與死神握手:創辦樹葬灑葬
驚濤駭浪中創辦海葬
不變的誓詞
酷吏與笨蛋
你也在這裡!
自序 鐵杵磨成繡花針
輯一 縫隙中看見生命
初戀文學
三十歲的老太太
足下
她的名字叫罔腰
媽媽桑
生命的縫隙
祈 禱
舞 緣
我舞故我在
乘著歌聲的翅膀
爸爸的老友
望德園便當
我愛台灣
公車上
消失的小火車
拎著水桶坐公車的女人
黃土高原散客行
古城芳鄰
小鎮大會
赤道上
星空的祕密
市場——生命的交會點
觀雲聽風山林間
輯二 愛上女性主義
愛上女性主義
女人、知識與書寫
飛向奈羅比
走過三世紀的老牌女青運動
千里紅線女書情
芝加哥之怒
聖彼得堡夏夜
「超越。愛」的見證
山豬溫泉
環海公路
山在虛無縹緲間
綴連台灣的人
看見
無聲的吶喊
輯三 勇闖政治叢林
跳進兔子洞
生之慾
改變成真
武崗的春天
都市的漂泊者
我只是眼睛看不見
老吾老
與死神握手:創辦樹葬灑葬
驚濤駭浪中創辦海葬
不變的誓詞
酷吏與笨蛋
你也在這裡!
序
推薦序
「魚與熊掌」兼得的女性主義人生 范情
一九八○年代,女性主義在 台灣方興,但仍為禁忌,婦女研究更是荒漠,顧燕翎是第一代女性主義婦女研究學者。當時女性主義知識多為翻譯作品,或個人生活觀察,她的理論文章獨樹一幟, 邏輯清晰,嚴謹扎實,是想一探女性主義或婦女運動理論奧門的至寶。燕翎追求理論和行動兼具的學問,投身婦女研究是她循規蹈矩人生的第一個大轉折;美國求學 時,慈祥的指導教授,男性,曾對她說,理論和行動兼具的理想學問誰不嚮往,可惜沒有,魚與熊掌無法兼得;結果燕翎找到了有理論和實踐藍圖的女性主義,拒絕 了人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博士學位,改做還未獲學術界認同的婦女研究。轉折成了人生重要的起點,女性主義成為最愛,理論與實踐也貫穿她的志業和生活,從參與婦 女運動、大學校園改革到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主義政務官,以致許多生命的決定。
我一直視燕翎為學術「嚴格標準」的象徵,也以她的積極、 認真、效率為標竿榜樣。從婦女新知基金會到台北女青年會的性別推動小組共事,一九九六年參與燕翎召集的女性主義理論流派寫作,一起做行政院研考會的性別機 制研究,共遊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女書」發源地:江永,以及今年五月參訪芬蘭老年政策與機構,隨年齡增長,也分享生活心得,成為好友。受邀寫序,意外而榮 幸。
《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無論就內容或出書(文學寫作)這件事,都是燕翎的人生理論與實踐成果。書分三輯,我最好奇的是追求自由、平等的女性主義者進入官僚體系,她如何觀察官場,如何做事。
燕 翎最厲害的地方是從「影響人」,而「改變事」。常見官員、委員咄咄逼人、訓斥公務人員,燕翎卻常對我稱讚一些她熟識的政府公務員,她說,我們的公務員經過 高、普考,都是台灣很優秀的人才。為什麼「公務員」成了「冗」的象徵?「公務員心態」是爭功諉過、刻板照章行事、踢皮球的代名詞?燕翎如何以女性主義改變 「人」?
燕翎雖知美國當代女性主義政治學者Kathy Ferguson的研究,認為女性主義和官僚體制不可能相容,燕翎也分析殺死 公務員熱情的表章制度,但她受黑澤明導演一九五二年描寫公務員的電影《生之慾》感動,任職公務員訓練中心主任時,以《生之慾》鼓勵同仁將工作和個人生命意 義相連,不浪費生命,衝出改變。雖然《生之慾》電影中,一個公務員預知死亡前半年徹悟生命而激情改變,最終社會體制與人性依然故我;燕翎則為主角改變後對 人生的滿足而感動,以女性主義關心人的生命立場,欣喜看到人的可能。
走入政治叢林,燕翎以女性主義探照燈引領,只要有可「改革」之 處,就是光的所在,也是她的方向,在當今世道,顯得不合時宜,例如擔任台北市社會局長時,介入人人迴避的殯葬業改革。讀燕翎的〈政治叢林〉文章也如看一幕 幕荒謬戲,「民主」時代,官場升官進爵習氣不變,依法行政,但無人關心法規漏洞,為了防弊,公務人員耗費精力,利益團體維護既得利益,民選首長有四年選票 考量,民意代表與號稱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媒體追求曝光與收視率;燕翎是想做事的人,她的改革或生利成了政治不正確,遭遇難堪如:業者推輪椅、撒尿布、找民意 代表對峙抗議,媒體失焦,長官不悅,加上台灣政黨惡性鬥爭,好的政策無法推行。看到燕翎為了顧念都市邊緣人、盲人、老人、死人(安葬)而委曲求全,我心不 忍,但也佩服。短暫公務員生涯中,幸好在有想法的人才協助下,當議員、官員還在口沫橫飛時,她的政策已輕舟飛渡,獲民眾青睞,完成照顧因社會歧視受害的遊 民、推動回歸自然的樹葬、灑葬、海葬及鼓吹開放明眼人按摩,讓「只是眼睛看不見」的盲人,不局限於按摩業,能獲得個人最大的成長與發展。她以女性主義「互 為主體」的概念關心弱勢,希望世界是能看見他人,去除個人心中的盲點。
燕翎獨立思考與追根究柢的學者習性,讓她在庸碌官場中,思維作 法不同流俗,例如:「女人與盲人,誰才是弱勢?」提議開放明眼弱勢女性按摩,反而與昔日女性主義陣營同志分道;藉「認真誠懇、斤斤計較、算得清清楚楚」, 使既得利益團體的反對聲音喪失立場。在習於「吃大鍋飯」的公務機關中,積極研究管理,檢討每一項業務的成本效益、流程、方法..,突破女性主義者談平等不 談績效,左派把績效看做資本主義流毒,壓搾勞力的工具的禁忌。同以義工身分參與民間團體工作,燕翎常和我互相勉勵,成本概念和效率是生存要件,而我還無法 做好,她已把這個精神帶入政府。
燕翎如好奇的愛麗絲跳進兔子洞,漫遊,透視周遭一張張鬼牌,自述如「白目」般,知其不可而為之;這不是學者理智的分析,而是不理智的改革者熱情。我不解「理性的」燕翎何以能看透現實荒謬,卻未遺棄世界,仍然有改革者的熱情,直到我讀了〈愛上女性主義〉。
遇見女性主義是許多人生命中的重要轉折,理由各有不同,燕翎因重視理論與實踐合一,女性主義讓她發現問題,也幫助解決問題。燕翎是讀書人,因書啟蒙,〈愛上 女性主義〉輯中細數她的啟蒙書籍。而她的女性主義也是五湖四海的,如同「早在十九世紀,不同國籍的女人就不辭舟車勞頓、環繞地球、一次又一次地召開世界婦 女會議,在現代化客輪和飛機尚未問世之前,這樣做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盼望,得儲蓄多久啊!」燕翎也是一直環繞地球奔波,從參加世界女性組織會議到國內各婦女 團體,從僅能藉第三人翻譯的俄羅斯到世界唯一的神祕女性文字「女書」發源地江永,從結識世界婦運領袖到市場縫衣小店的阿婆,她說:「『我』與其他女人相 遇,看見彼此,得到印證,也因而獲得智慧和力量。女人似乎總是在別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翻開婦女史,女人的成長在集體的、婦運層次和個人層次同時進行 著,互相交錯增強。」五湖四海互相支持的姊妹情誼,讓她能在婦女研究備受質疑的年代繼續至今,也穿透許多人生無奈。
燕翎一篇哀悼學生 的文章〈環海公路一三八‧五:一九九三最後的春天〉讓我震撼,她嘆息優秀學生,誤信西方哲學身心分離,導致概念吃掉優秀的年輕人,「憤怒你全盤信了西方哲 學思維傳統的二分法—那些男性哲學家無償占用女性身體和勞務之後的空言,那些企圖轉化血肉之軀為烈士的誑語,果決勇敢地完成了意志和身體的分割,也因此才 有效執行了卡繆所謂的『哲學性自殺』,藉由『處決自己的生命來成就自由意志以及避免異化。』」「你雖倡言以行動克服『異化』,可是當你與肉身對立,以超強 的意志來壓抑肉體的『反叛』和痛苦時,這種與己身為敵的作法不是跟自我最大的疏離嗎?」燕翎的犀利穿透分析,也讓我豁然開朗,她不只有精鍊理論思考,更與 身體自覺、感受、生活與生命結合,因此不因現實環境荒謬不符合理論分析完美而挫敗悲觀。因為有感受,與人與生命連結,才能在清楚意識荒謬、衝突、無解中看 到存活的意義,而有繼續改革的熱情。燕翎的改革隨時隨地,高尚的知識圈、校園,也是戰場;善意者勸她,「不要生氣」、「妳就是不夠溫柔」,惡意攻訐黑函將 她貼上「女性主義者」標籤,她最愛的身分成了汙名的來源。世人不知,女性主義者的溫柔是對生命與人的愛,也是批判世情的基礎。
女性主 義要看見、聽見有形無形的權勢壓迫下被隱匿的人和聲音,燕翎說,「人生的學習之旅中,學會看見是一門重要的功課,隨著境界的提升,我們學會看得更深、更 遠、更敏銳、更包容,變成一個更好、更柔軟的人。」燕翎在忙碌的生活斷裂、縫隙處也看見自己的生命,重拾幼年被壓抑的舞蹈、歌唱與文學寫作。
女性主義者有個金句名言「我的身體,我決定」,在燕翎的生命中獲得最徹底的實踐。一次身體檢查後,面對理性科學的醫學檢驗證據,她聽從自己身體的聲音,給自 己機會,進醫院前,到久別的山林。她不一定能判別事情可能的發展結果,但這一步讓她身心完整。讀到她寫先生從新竹開車到南庄,苦口婆心勸她回台北就醫,認 為妻子居然看樹林不看醫生,行徑荒誕,本末倒置,最後「兩人各自擁抱自己的信念,卻無法說服對方,都流下了眼淚,他獨自下山而去。」我想到電影《時時刻 刻》中,維吉尼雅.吳爾芙想逃離醫生和丈夫安排靜養的鄉下,回到城市,先生尋到火車站阻止,兩人因愛爭執,因愛淚眼放手;燕翎想從都市忙碌中回歸山林,維 吉尼雅感覺鄉間窒息,需求不同,爭取自主的意念一致。女性常常照顧他人,也習慣以受照顧者的需求為主,而當自己成為被照顧者,有多少自決的空間?
燕翎退休後,延續在社會局關注的老人政策,重拾文學寫作初戀,得了梁實秋散文獎,出書,本身就是重要的生命圓夢,也是在自己身上映證老年生活理論實踐。她以 不同於學者論述,回顧生命中許多縫隙和起點,紀錄人與人之間、女性之間、識與不識者交錯的光芒,她真誠面對自己,讓在文化下壓抑的自我得以抒發,我也因此 感覺更親近燕翎的生命,獲得自己生命的力量。
*本文作者范情女士,一九八○年代學新聞、傳播,任記者,初識女性主義。一九九○年完成學業回國,參與台灣婦運,在大學兼課。近年,專注媒體中的婦女性別議題。
自序
鐵杵磨成繡花針
活得長久(前提是也活得健康)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畢生的夢想。
因為對高齡社會公共政策的興趣和對美好社會的嚮往,我對芬蘭這個國家的文化與制度一直很有興趣。讀了不少研究論文、結識了幾位來台訪問的芬蘭學者、自己也寫了一篇有關芬蘭照顧政策的論文之後,便打定主意要登堂入室,探個究竟。和朋友們談起,有同樣興致的人不少,但承諾同行的卻只有兩位,其中一位又只有寒暑假才可以,與芬蘭方面提出的五月在時間上有衝突。大部分的人都會問:要花多少錢?去多少天?去那些地方?這些問題我在實際規畫行程之前並無法確切回答。於是有三、四年的時間,芬蘭行始終停留在空中樓閣的藍圖階段。
直到遇到兩位行動力極強的新朋友,她們什麼也沒多問,便承諾同行,而且分擔了部分旅程的規畫,那位大學任教的也退休了,我有了基本的成員便積極連繫參訪對象、安排路程,也很快招募到理想的人數。在春暖花開、日照最長的五月天到了赫爾新基和優伏斯科拉兩個城市,參訪高齡社會公共政策的研究機構和照顧機構、老年住宅,與專業工作者深談,同時也以自助旅行的方式享受美麗的森林、湖泊、海岸、公園、古蹟和現代化國際都會,大家都深感不虛此行,美夢成真的感覺真好。
另一個比芬蘭夢歷時更長、一度被歲月埋藏的夢想便是我的作家夢。要不是妹妹提醒,我自己已經忘了在高中參加救國團的戰?文藝營之前,初中時代即是一家文學函授班的學員,足證我曾經多麼認真和多早想成為作家。成年後專注於書寫論文和評論,早早荒廢了文學的田地。但身為台灣第一代女性主義者,行走於學術、社會運動、公部門之間,有太多與前人不同的人生故事渴望分享,於是半世紀後重拾文學的鍵盤,花了數年時間,敲打下生命的音符,修修改改,不自量力地交給九歌出版社。九歌是歷史悠久、極富盛名的文學出版社,選稿嚴謹,對於我的嘔心瀝血之作並不全盤接受。回到家來,揣摩編意,再讀文章,覺得有些部分論述性太強,故事性太弱,需要在心靈、情感層面多做溝通,方能動人心弦。
我不想改變我的題材,特別是公部門生涯的冷暖點滴,現代台灣少有文學作品處理這方面的主題,但吳敬梓(《儒林外史》)、李寶嘉(《官場現形記》)、黑澤明(《生之慾》)都曾經以小說或電影的形式從第三者的觀點或嘲諷或悲憫地述說官場的故事,悲觀地看到官場的黑暗和人性的軟弱。我想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文體、以不同的性別身分切入官場,看見轉變的可能。所以又花了一、兩年時間改寫,鐵杵磨得有點?花針的樣子了,方才為九歌接受,也終於有機會出版此生第一本散文集。
慶幸自己仍然有能力快樂織夢,下一場大夢是出版婦運論文集。
顧燕翎 於二○一五年八月
「魚與熊掌」兼得的女性主義人生 范情
一九八○年代,女性主義在 台灣方興,但仍為禁忌,婦女研究更是荒漠,顧燕翎是第一代女性主義婦女研究學者。當時女性主義知識多為翻譯作品,或個人生活觀察,她的理論文章獨樹一幟, 邏輯清晰,嚴謹扎實,是想一探女性主義或婦女運動理論奧門的至寶。燕翎追求理論和行動兼具的學問,投身婦女研究是她循規蹈矩人生的第一個大轉折;美國求學 時,慈祥的指導教授,男性,曾對她說,理論和行動兼具的理想學問誰不嚮往,可惜沒有,魚與熊掌無法兼得;結果燕翎找到了有理論和實踐藍圖的女性主義,拒絕 了人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博士學位,改做還未獲學術界認同的婦女研究。轉折成了人生重要的起點,女性主義成為最愛,理論與實踐也貫穿她的志業和生活,從參與婦 女運動、大學校園改革到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主義政務官,以致許多生命的決定。
我一直視燕翎為學術「嚴格標準」的象徵,也以她的積極、 認真、效率為標竿榜樣。從婦女新知基金會到台北女青年會的性別推動小組共事,一九九六年參與燕翎召集的女性主義理論流派寫作,一起做行政院研考會的性別機 制研究,共遊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女書」發源地:江永,以及今年五月參訪芬蘭老年政策與機構,隨年齡增長,也分享生活心得,成為好友。受邀寫序,意外而榮 幸。
《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無論就內容或出書(文學寫作)這件事,都是燕翎的人生理論與實踐成果。書分三輯,我最好奇的是追求自由、平等的女性主義者進入官僚體系,她如何觀察官場,如何做事。
燕 翎最厲害的地方是從「影響人」,而「改變事」。常見官員、委員咄咄逼人、訓斥公務人員,燕翎卻常對我稱讚一些她熟識的政府公務員,她說,我們的公務員經過 高、普考,都是台灣很優秀的人才。為什麼「公務員」成了「冗」的象徵?「公務員心態」是爭功諉過、刻板照章行事、踢皮球的代名詞?燕翎如何以女性主義改變 「人」?
燕翎雖知美國當代女性主義政治學者Kathy Ferguson的研究,認為女性主義和官僚體制不可能相容,燕翎也分析殺死 公務員熱情的表章制度,但她受黑澤明導演一九五二年描寫公務員的電影《生之慾》感動,任職公務員訓練中心主任時,以《生之慾》鼓勵同仁將工作和個人生命意 義相連,不浪費生命,衝出改變。雖然《生之慾》電影中,一個公務員預知死亡前半年徹悟生命而激情改變,最終社會體制與人性依然故我;燕翎則為主角改變後對 人生的滿足而感動,以女性主義關心人的生命立場,欣喜看到人的可能。
走入政治叢林,燕翎以女性主義探照燈引領,只要有可「改革」之 處,就是光的所在,也是她的方向,在當今世道,顯得不合時宜,例如擔任台北市社會局長時,介入人人迴避的殯葬業改革。讀燕翎的〈政治叢林〉文章也如看一幕 幕荒謬戲,「民主」時代,官場升官進爵習氣不變,依法行政,但無人關心法規漏洞,為了防弊,公務人員耗費精力,利益團體維護既得利益,民選首長有四年選票 考量,民意代表與號稱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媒體追求曝光與收視率;燕翎是想做事的人,她的改革或生利成了政治不正確,遭遇難堪如:業者推輪椅、撒尿布、找民意 代表對峙抗議,媒體失焦,長官不悅,加上台灣政黨惡性鬥爭,好的政策無法推行。看到燕翎為了顧念都市邊緣人、盲人、老人、死人(安葬)而委曲求全,我心不 忍,但也佩服。短暫公務員生涯中,幸好在有想法的人才協助下,當議員、官員還在口沫橫飛時,她的政策已輕舟飛渡,獲民眾青睞,完成照顧因社會歧視受害的遊 民、推動回歸自然的樹葬、灑葬、海葬及鼓吹開放明眼人按摩,讓「只是眼睛看不見」的盲人,不局限於按摩業,能獲得個人最大的成長與發展。她以女性主義「互 為主體」的概念關心弱勢,希望世界是能看見他人,去除個人心中的盲點。
燕翎獨立思考與追根究柢的學者習性,讓她在庸碌官場中,思維作 法不同流俗,例如:「女人與盲人,誰才是弱勢?」提議開放明眼弱勢女性按摩,反而與昔日女性主義陣營同志分道;藉「認真誠懇、斤斤計較、算得清清楚楚」, 使既得利益團體的反對聲音喪失立場。在習於「吃大鍋飯」的公務機關中,積極研究管理,檢討每一項業務的成本效益、流程、方法..,突破女性主義者談平等不 談績效,左派把績效看做資本主義流毒,壓搾勞力的工具的禁忌。同以義工身分參與民間團體工作,燕翎常和我互相勉勵,成本概念和效率是生存要件,而我還無法 做好,她已把這個精神帶入政府。
燕翎如好奇的愛麗絲跳進兔子洞,漫遊,透視周遭一張張鬼牌,自述如「白目」般,知其不可而為之;這不是學者理智的分析,而是不理智的改革者熱情。我不解「理性的」燕翎何以能看透現實荒謬,卻未遺棄世界,仍然有改革者的熱情,直到我讀了〈愛上女性主義〉。
遇見女性主義是許多人生命中的重要轉折,理由各有不同,燕翎因重視理論與實踐合一,女性主義讓她發現問題,也幫助解決問題。燕翎是讀書人,因書啟蒙,〈愛上 女性主義〉輯中細數她的啟蒙書籍。而她的女性主義也是五湖四海的,如同「早在十九世紀,不同國籍的女人就不辭舟車勞頓、環繞地球、一次又一次地召開世界婦 女會議,在現代化客輪和飛機尚未問世之前,這樣做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盼望,得儲蓄多久啊!」燕翎也是一直環繞地球奔波,從參加世界女性組織會議到國內各婦女 團體,從僅能藉第三人翻譯的俄羅斯到世界唯一的神祕女性文字「女書」發源地江永,從結識世界婦運領袖到市場縫衣小店的阿婆,她說:「『我』與其他女人相 遇,看見彼此,得到印證,也因而獲得智慧和力量。女人似乎總是在別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翻開婦女史,女人的成長在集體的、婦運層次和個人層次同時進行 著,互相交錯增強。」五湖四海互相支持的姊妹情誼,讓她能在婦女研究備受質疑的年代繼續至今,也穿透許多人生無奈。
燕翎一篇哀悼學生 的文章〈環海公路一三八‧五:一九九三最後的春天〉讓我震撼,她嘆息優秀學生,誤信西方哲學身心分離,導致概念吃掉優秀的年輕人,「憤怒你全盤信了西方哲 學思維傳統的二分法—那些男性哲學家無償占用女性身體和勞務之後的空言,那些企圖轉化血肉之軀為烈士的誑語,果決勇敢地完成了意志和身體的分割,也因此才 有效執行了卡繆所謂的『哲學性自殺』,藉由『處決自己的生命來成就自由意志以及避免異化。』」「你雖倡言以行動克服『異化』,可是當你與肉身對立,以超強 的意志來壓抑肉體的『反叛』和痛苦時,這種與己身為敵的作法不是跟自我最大的疏離嗎?」燕翎的犀利穿透分析,也讓我豁然開朗,她不只有精鍊理論思考,更與 身體自覺、感受、生活與生命結合,因此不因現實環境荒謬不符合理論分析完美而挫敗悲觀。因為有感受,與人與生命連結,才能在清楚意識荒謬、衝突、無解中看 到存活的意義,而有繼續改革的熱情。燕翎的改革隨時隨地,高尚的知識圈、校園,也是戰場;善意者勸她,「不要生氣」、「妳就是不夠溫柔」,惡意攻訐黑函將 她貼上「女性主義者」標籤,她最愛的身分成了汙名的來源。世人不知,女性主義者的溫柔是對生命與人的愛,也是批判世情的基礎。
女性主 義要看見、聽見有形無形的權勢壓迫下被隱匿的人和聲音,燕翎說,「人生的學習之旅中,學會看見是一門重要的功課,隨著境界的提升,我們學會看得更深、更 遠、更敏銳、更包容,變成一個更好、更柔軟的人。」燕翎在忙碌的生活斷裂、縫隙處也看見自己的生命,重拾幼年被壓抑的舞蹈、歌唱與文學寫作。
女性主義者有個金句名言「我的身體,我決定」,在燕翎的生命中獲得最徹底的實踐。一次身體檢查後,面對理性科學的醫學檢驗證據,她聽從自己身體的聲音,給自 己機會,進醫院前,到久別的山林。她不一定能判別事情可能的發展結果,但這一步讓她身心完整。讀到她寫先生從新竹開車到南庄,苦口婆心勸她回台北就醫,認 為妻子居然看樹林不看醫生,行徑荒誕,本末倒置,最後「兩人各自擁抱自己的信念,卻無法說服對方,都流下了眼淚,他獨自下山而去。」我想到電影《時時刻 刻》中,維吉尼雅.吳爾芙想逃離醫生和丈夫安排靜養的鄉下,回到城市,先生尋到火車站阻止,兩人因愛爭執,因愛淚眼放手;燕翎想從都市忙碌中回歸山林,維 吉尼雅感覺鄉間窒息,需求不同,爭取自主的意念一致。女性常常照顧他人,也習慣以受照顧者的需求為主,而當自己成為被照顧者,有多少自決的空間?
燕翎退休後,延續在社會局關注的老人政策,重拾文學寫作初戀,得了梁實秋散文獎,出書,本身就是重要的生命圓夢,也是在自己身上映證老年生活理論實踐。她以 不同於學者論述,回顧生命中許多縫隙和起點,紀錄人與人之間、女性之間、識與不識者交錯的光芒,她真誠面對自己,讓在文化下壓抑的自我得以抒發,我也因此 感覺更親近燕翎的生命,獲得自己生命的力量。
*本文作者范情女士,一九八○年代學新聞、傳播,任記者,初識女性主義。一九九○年完成學業回國,參與台灣婦運,在大學兼課。近年,專注媒體中的婦女性別議題。
自序
鐵杵磨成繡花針
活得長久(前提是也活得健康)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畢生的夢想。
因為對高齡社會公共政策的興趣和對美好社會的嚮往,我對芬蘭這個國家的文化與制度一直很有興趣。讀了不少研究論文、結識了幾位來台訪問的芬蘭學者、自己也寫了一篇有關芬蘭照顧政策的論文之後,便打定主意要登堂入室,探個究竟。和朋友們談起,有同樣興致的人不少,但承諾同行的卻只有兩位,其中一位又只有寒暑假才可以,與芬蘭方面提出的五月在時間上有衝突。大部分的人都會問:要花多少錢?去多少天?去那些地方?這些問題我在實際規畫行程之前並無法確切回答。於是有三、四年的時間,芬蘭行始終停留在空中樓閣的藍圖階段。
直到遇到兩位行動力極強的新朋友,她們什麼也沒多問,便承諾同行,而且分擔了部分旅程的規畫,那位大學任教的也退休了,我有了基本的成員便積極連繫參訪對象、安排路程,也很快招募到理想的人數。在春暖花開、日照最長的五月天到了赫爾新基和優伏斯科拉兩個城市,參訪高齡社會公共政策的研究機構和照顧機構、老年住宅,與專業工作者深談,同時也以自助旅行的方式享受美麗的森林、湖泊、海岸、公園、古蹟和現代化國際都會,大家都深感不虛此行,美夢成真的感覺真好。
另一個比芬蘭夢歷時更長、一度被歲月埋藏的夢想便是我的作家夢。要不是妹妹提醒,我自己已經忘了在高中參加救國團的戰?文藝營之前,初中時代即是一家文學函授班的學員,足證我曾經多麼認真和多早想成為作家。成年後專注於書寫論文和評論,早早荒廢了文學的田地。但身為台灣第一代女性主義者,行走於學術、社會運動、公部門之間,有太多與前人不同的人生故事渴望分享,於是半世紀後重拾文學的鍵盤,花了數年時間,敲打下生命的音符,修修改改,不自量力地交給九歌出版社。九歌是歷史悠久、極富盛名的文學出版社,選稿嚴謹,對於我的嘔心瀝血之作並不全盤接受。回到家來,揣摩編意,再讀文章,覺得有些部分論述性太強,故事性太弱,需要在心靈、情感層面多做溝通,方能動人心弦。
我不想改變我的題材,特別是公部門生涯的冷暖點滴,現代台灣少有文學作品處理這方面的主題,但吳敬梓(《儒林外史》)、李寶嘉(《官場現形記》)、黑澤明(《生之慾》)都曾經以小說或電影的形式從第三者的觀點或嘲諷或悲憫地述說官場的故事,悲觀地看到官場的黑暗和人性的軟弱。我想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文體、以不同的性別身分切入官場,看見轉變的可能。所以又花了一、兩年時間改寫,鐵杵磨得有點?花針的樣子了,方才為九歌接受,也終於有機會出版此生第一本散文集。
慶幸自己仍然有能力快樂織夢,下一場大夢是出版婦運論文集。
顧燕翎 於二○一五年八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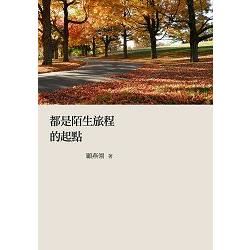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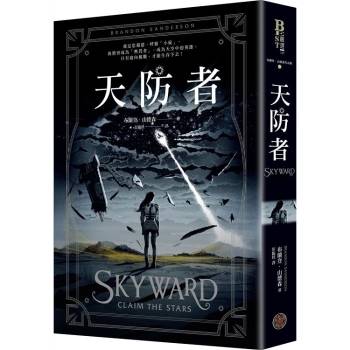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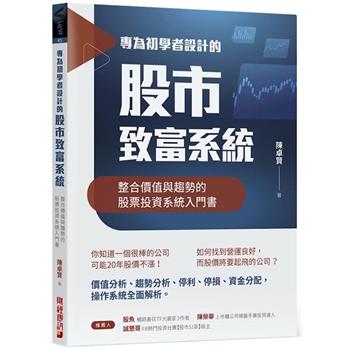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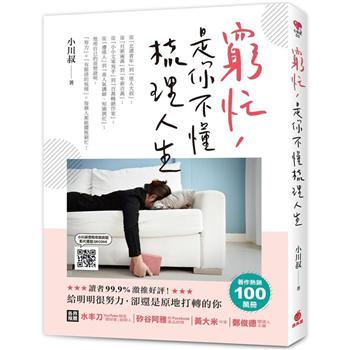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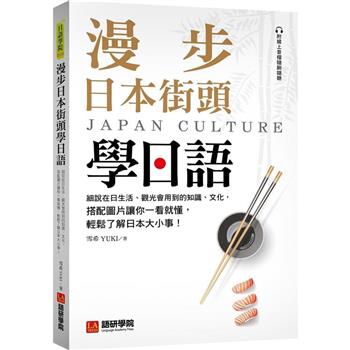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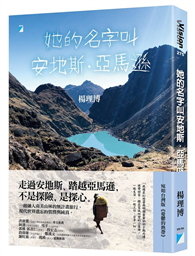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