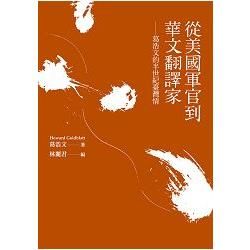中國現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 葛浩文
成功讓莫言站上國際舞臺,獲諾貝爾文學獎
成功讓莫言站上國際舞臺,獲諾貝爾文學獎
回顧這過去五十多年的臺灣,有我成長的痕跡,有學習國語的道路,有多少難忘的回憶,有我翻譯過的臺灣作家與作品,更有許許多多令我敬佩的臺灣人。我熱愛臺灣的種種,經常跟朋友說臺北是我的第二個故鄉。──葛浩文
葛浩文,華文文學界不可忽略的名字,曾翻譯過許多優秀的華文作品,透過他的翻譯,眾多華文作品得以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成功將莫言推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舞臺上,而畢飛宇《玉米》經由他與林麗君的翻譯後,獲得曼氏亞洲文學獎。葛浩文的成就,連著名學者夏志清都不禁盛譽他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
一九六二年,二十三歲的美國年輕軍官踏上這塊被他稱為「寶島」的臺灣,住日式平房,身穿唐衫棉襖,熱愛美食與書店,從軍生涯兩度駐臺,退役後仍戀戀不捨,留臺學中文,一切契機由此開始。
翻譯之路是孤獨的,但他身旁不乏文壇知交,他暱稱黃春明「阿明」、與李昂吃遍世界美食,喜愛他們的作品,也珍視彼此的情誼;他感懷前輩孫陵、周錦、張蘭熙、柏陽的另眼相待,視他們為生命裡溫暖的貴人;與他結識者尚有瘂弦、白先勇、陳若曦、劉紹明、夏志清、王德威等。
葛浩文翻譯作品多不勝數,從書名到內文用字,思索中外不同用語習慣,仔細計較、用心推敲,每一輪的檢視都試以不同視角不斷修正,面對神聖的文字,一絲不苟。二○○九年他與林麗君所譯的朱天文《荒人手記》獲得年度最佳翻譯獎,即是最佳明證。
他從臺灣的土地、生活、友情中積澱大量養分,與臺灣文壇密不可分,視臺灣為「第二故鄉」,這冊結緣半世紀的點滴紀錄,已可視為一部感性與知性兼具的「臺灣文學五十年別史」。
本書特色
★葛浩文曾翻譯過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作品,將其推向國際,為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引介人。其所譯介作品的作者姜戎、蘇童、畢飛宇三人,曾獲曼氏亞洲文學獎。
★書中附有葛浩文對於翻譯的看法與心得,頗值得一覷。
名人推薦
李昂作序推薦:
書中詳細地談到了與臺灣的結緣,將許多作品譯介到國際舞臺,可以說是另外一部臺灣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英語世界的臺灣文學面相,其重要性可見一斑,也會是研究這個階段的臺灣文學必用的參考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