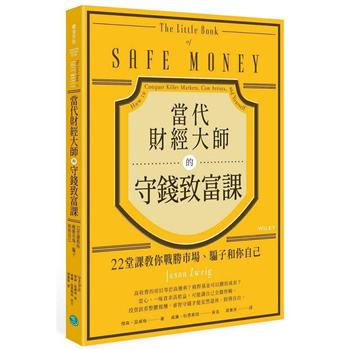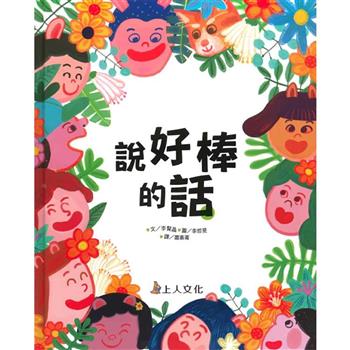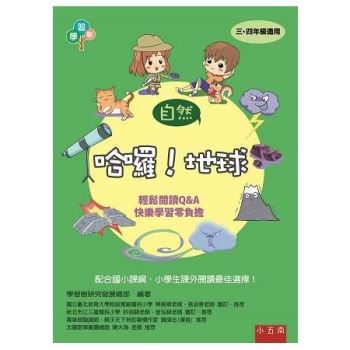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戲金戲土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75 |
小說 |
電子書 |
$ 175 |
小說 |
電子書 |
$ 175 |
小說 |
$ 198 |
文學作品 |
$ 198 |
中文現代文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小說 |
$ 225 |
小說 |
$ 225 |
現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在遊行的花車上,天空出現疑似戲神田都元帥的模樣,「戲神……,你們看啦,戲神——」十一、二歲的阿山脫口而出,這場遊行是戲院老闆尤豐喜要為台灣第一部正宗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在宜蘭羅東上映做宣傳。尤豐喜原是職製藥廠的外務員,派駐到花蓮,交遊廣闊,個性海派,招贅入歌仔戲班,帶著戲班巡迴北台灣,火車上巧遇在宜蘭工作的郭月鳳,一見傾心,還把戲院事業從花蓮拓展到宜蘭羅東。
五○年代台語片風光,尤豐喜除了在自己戲院播映,也投資拍攝。年紀漸長的阿山總是在尤豐喜跟前跟後打雜幹活,還要大家叫他「細漢阿布拉」。除了送片,還擅自出鬼點子宣傳電影,讓票房由黑翻紅,甚至連「戲神」在暗中推波助瀾,藉著阿山幫助尤豐喜,化解危機,讓戲院更上層樓。時代改變,觀眾的口味也變了,台語片風光不在,尤豐喜在電影上賺得多也賠得多,到底戲是金,還是土?
看尤豐喜和阿山前後二代,見證台灣電影史的潮起潮落,作者楊麗玲運用紀實、寫實、魔幻的小說手法,加上神鬼靈異、大量史料,包含歌仔戲的起源、台語片的風光,到新電影的崛起,道盡台灣電影的興衰。
本書特色
★ 楊麗玲以宜蘭羅東戲劇之神尤豐喜傳奇的一生為主軸,書寫台灣五零年代電影發展史。
★ 改編成電視劇《阿不拉的三個女人》將在四月十七日於民視播出。
作者簡介
楊麗玲
曾任電影及廣告企劃、報社記者、副刊編輯,現專事寫作、遊藝現代水墨、油畫。曾獲耕莘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央日報文學獎、台灣文學獎、觀光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公視百萬劇本推薦獎、國家文藝基金會小說創作補助、長篇小說專案補助等 。並出版有《失血玫瑰》、《愛情的寬度》、《分手的第一千零一個理由》、《愛染》、《愛情無需偉大》、《變色龍》、《發現一個迷人的世界》、《台北生活好樣的》、《翻滾吧!阿信》、《艋舺戀花恰恰恰》、《山居.鹿小村》……等三十餘部作品。
|

![向大師學繪畫:西方藝術大師名畫復刻版,讓繪畫技巧升級的14堂繪畫課[隨書附贈28支示範影片] 向大師學繪畫:西方藝術大師名畫復刻版,讓繪畫技巧升級的14堂繪畫課[隨書附贈28支示範影片]](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94/2019479578260/2019479578260m.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