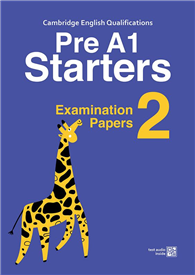在犁分山上,一位刻苦耐勞、勤儉持家的傳統農家子弟甘祿松,為了改善貧困的生活,來回北港、葫蘆墩等地的牛墟販賣牛隻,他將希望寄託在長子甘天龍身上,竭盡心力供他學醫。
當天龍終於不負所望在葫蘆墩開診所濟世行醫,天龍之母阿柔幫他相中了膚白若雪的江惜作為他的妻子。一步一腳印,十多年來,雖然財富不斷的累積,但一成不變的家庭生活,讓他感覺孤獨寂寞。因洽談生意開始涉足查某間,藝妓明秋趁虛而入,和妻子相異的種種,竟引出天龍潛藏的熱情與風流,卻也讓甘家從此進入風雨多變的紛亂歲月……
廖輝英「臺灣百年」經典代表作,原著改拍成電視劇,叫好又叫座。《負君千行淚》以日據時代為背景,故事曲折,人物突出,側寫臺灣百年的變貌,從牛墟的交易情形、學制問題到查某間(妓女戶)和食衣住行等生活細節,均經重重考證。曲折感人的文字特質,高潮迭起的情節,倍添此書無窮的可看性,見證大時代!
本書特色
★ 與《輾轉紅蓮》、《相逢一笑宮前町》、《月影》,合稱為「老臺灣四部曲」。
★ 多次改編成電視劇,深受好評。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負君千行淚(增訂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負君千行淚(增訂新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廖輝英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專事寫作。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小說獎、吳三連文學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及金馬獎改編劇本獎。為傳統女性發聲,作品篇篇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關,擊中社會要害。寫兩性情懷,最能撫平現代人的傷口,公認是社會性最強、共鳴最大、最具現代感的小說家。
她觀察兩性,文走社會各階層,成為最受信賴的「廖老師」。現更專注於青少年問題,關懷社會層面更深廣。著有小說《今夜微雨》、《盲點》、《油蔴菜籽》、《女人香》、《焰火情挑》、《相逢一笑宮前町》、《不歸路》等;愛情散文集《先說愛的人,怎麼可以先放手》、《愛,不是單行道》、《戀愛,請設停損點》、《原諒,為什麼這麼痛?》、《雨,下在平原上》。作品多部被改拍為電影和電視劇。
廖輝英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專事寫作。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小說獎、吳三連文學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及金馬獎改編劇本獎。為傳統女性發聲,作品篇篇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關,擊中社會要害。寫兩性情懷,最能撫平現代人的傷口,公認是社會性最強、共鳴最大、最具現代感的小說家。
她觀察兩性,文走社會各階層,成為最受信賴的「廖老師」。現更專注於青少年問題,關懷社會層面更深廣。著有小說《今夜微雨》、《盲點》、《油蔴菜籽》、《女人香》、《焰火情挑》、《相逢一笑宮前町》、《不歸路》等;愛情散文集《先說愛的人,怎麼可以先放手》、《愛,不是單行道》、《戀愛,請設停損點》、《原諒,為什麼這麼痛?》、《雨,下在平原上》。作品多部被改拍為電影和電視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