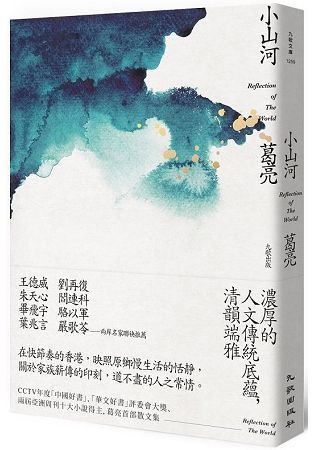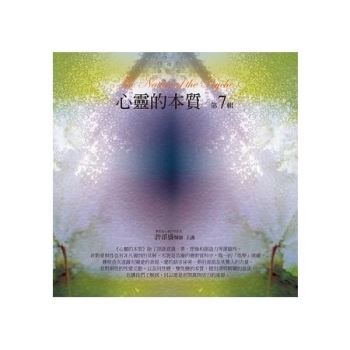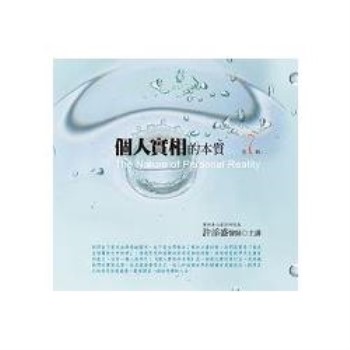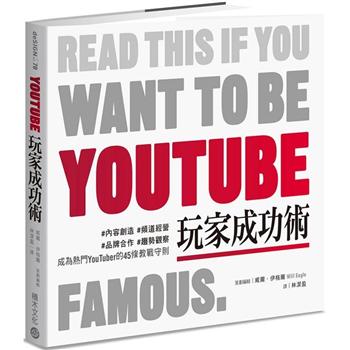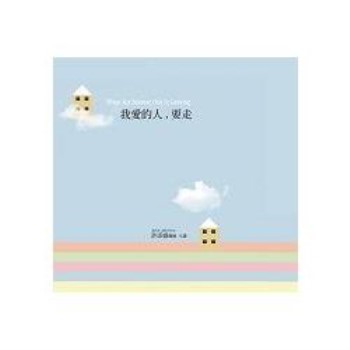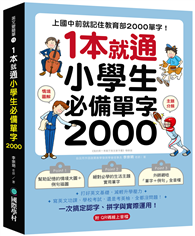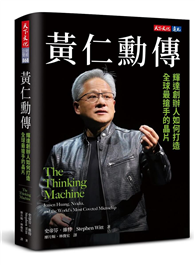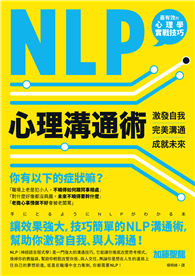拾歲
說起這十年,一時間不知從哪裡開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臺上,遠處是西貢夜色裡的一灣海。明暗間是散落水中的島嶼。淺淺的海浪激蕩,島嶼便是浮動的船。
院落裡燈影闌珊,聖誕樹兀自精神。夜已微涼,姑祖父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坐在籐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願,不願意錯過熱鬧。寧願做這熱鬧裡的佈景,才會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熱鬧卻還是濃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間堆疊。小狗不知倦,將李醫生的雙胞胎留下的玩具叼著,在院落裡巡遊。姑祖母還在絮絮地和母親說話。講的依然是往事。這夜裡,將陳年的事情都釋放出來,稀釋在這城市的空氣裡。
我的家族,與這城市無所謂淵源。出現人生的交迭,只在歷史的關隘。抗戰伊始,祖父輾轉到此,是因了舊派知識份子的良心。終於匆匆地還是離開,這地方不是久居之地。姑祖父母,留下來了。他們都是浪漫的人,革命的浪漫主義,經歷了現實的考驗。姑祖父是香港人,追求姑祖母用的是藝術家的愛國心。建國初期,背棄了家庭來到北京。成就了中央歌劇院一段千里姻緣的佳話。然而,終究是單純真實的人,六○年的時候,雙雙發落到了東北。這其間的艱難,用音樂與樂觀傾軋過去,居然也就水靜風停。終於回到故里,站在羅湖橋上,姑祖父淚眼婆娑,向左望去,招展的旗幟仍紅得悅目。這是十多年後了。
時光荏苒,四十年也總是留下痕跡。變不了的是姑祖母的鄉音。將近半世紀的香港生活,老人家還是地道的老北京的女兒。說起話仍是俐落爽脆,講到興處,仍是朗聲大笑。
舊年我博士畢業,在紅磡體育館舉行了典禮。一家人拍了照片,沖印出來。姑祖母看著笑著,終於有些動容。她指著這巨大的建築說,看,顏色都舊了。我來那會兒,還沒它呢。它現在都這麼老了。
千禧.勸學
我來到香港,在千禧年的尾聲。不算冷的冬日下午,黃昏的光鋪張下來,也有些暖意。下了車,走上了一條叫做「高街」的街道。這條街的陳舊出人意表,窄窄地從山道上蜿蜒下來。兩邊是陡峭的唐樓造成的峽谷,陽光走進來,也被囚禁了聲勢,成了淺淺的一條線。和南京的闊大街道相比,這條街的逼狹讓人有些許的不適。再讀了〈第二爐香〉,發現張愛玲寫到這條街,用了一個詞「崎嶇」,終於有些感歎,張的文字實在是老辣簡省。
與高街垂直的階梯,竟然也是一條街,叫做「興漢道」。咫尺之遙,分佈著幾家文具鋪和影印店。都是在做學生的生意,竟也十分的興旺。這興旺間,暗藏著潛在的競爭。有家叫做「藝美」的,做的是家庭生意。有論文訂裝的一條龍服務,婆婆管收錢,兒子和兒媳則是勞力。孫子是個戴眼鏡的小夥子,還在上學的年紀,負責些零雜的活計。一家人的神情都很勤勉。他們的競爭對手,是個壯年的男子,人稱「肥仔」,設備比他們先進些,店堂也整飭些。但都傳說他其實是個「無良商人」,所以在港大幾年,也並沒怎麼幫襯過他。這條路的盡頭,叫做般咸道。「般咸」是香港的第三任港督George Bonham的姓氏。香港的翻譯,因為受了粵語的影響,減省而生僻,就如同將Beckham譯為「碧咸」,Zidane譯成「施丹」,多少有些不著調。這道路是西區半山上的主要道路,曲折漫長。連接堅道和薄扶林道,座落了許多的名校,像是「聖保羅書院」等等,環繞了香港大學,幾乎帶有一些預備役的性質。
港大在這條街的中段,可以看得見校門口的石牌坊,掩映在綠蔭裡面。和內地高校大門的氣派不同,這座老牌的殖民地大學,有些深山藏古寺的意思。底氣是內裡的,有孫中山,陳寅恪與朱光潛的過往,淵源便也不用多說。
從校門右手的車道上去,便是本部大樓,米色的巴羅克建築。有的是繁複的回廊與凸起的鐘樓。地形不簡單,文學院辦公室在右手的位置,我去報到的時候,竟無端地繞了一個大圈。正門的地方,是陸佑堂,這是港大的禮堂。後來聽過的許多演講,都在這禮堂裡進行。到了學期末的時候,這裡便是全校學生high table(高桌會)的地方。港大的精英教育,落實在細微處。到這一天,少年男女們便嚴格地要盛裝出席,煞有介事。這是一種鍛煉,你要克服你天性的羞澀與膽怯,讓自己在人群中脫穎而出。所以,這禮堂又兼有Dancing Hall的功用。不過,晚近它的著名,卻是因借它拍了電影《色,戒》,作了王力宏和湯唯們演練愛國話劇的佈景。這電影在校園裡細水長流地挑選群眾演員,每每可以看到,幾個本校劇團的學生臉上都笑得很歡樂。那時候,我的學位論文正趕得如火如荼,從辦公室裡出來,疲憊地對他們望一眼,看出他們的歡樂也是加倍的。這禮堂,多少是有些凋落了。堂皇還是堂皇,老舊是骨子裡的。一百年的光陰,外面看不太出來,卻已蝕進了內心裡去。
如此看來,我在這所學校裡的五年,便真正是彈指一揮。細數下來,回憶還是不少。大多都是細節,比方校門附近有一棵樹,孤零零地立著,葉子四季都是少的。這是一棵樸樹,我記得它,是因為他和我喜歡的歌手,是同一個名字。而研究生堂附近的有一棵繁茂的細葉榕,三人合抱的粗大,後來卻被砍掉了。因為它發達的根系,撼動了地基。砍掉以後,如同一張天然的圓桌。又比如,儀禮堂附近,有一叢竹子,上面出沒著一條蛇,傳說是某個香港名人的魂魄。很多古老的學校都有傳說,最盛的是一些鬼故事。港大的此類故事,格調多是淒美優雅的,又有些煙火氣,所以並不怕人。其實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情,偏偏印象很深刻。這些印象,便夾在了教授們的真知灼見與日常的連篇累牘中,被留存了下來。
港大建在山上,這山是太平山。小時候看過一出劇,裡面主題歌中有一句「太平山下不太平,亂世風雲亂世情」,是因為有港戰的背景。我在這山下的歲月,還算是很太平的。香港人有「行山」的傳統,太平山上有一條晨運徑。曾經晨昏顛倒的時候,也仍然看得見黃昏裡頭,有些人在山路上或走或跑。跑的多是些外國人,都大汗淋瀝的。若是個白種人,膚色便變成淺紅色。還有一些菲傭,在山道上遛狗。那狗的毛色便在夕陽裡閃成了火紅。在山頂上,看到過一頭藏獒。並不見兇狠,眼神游離,沒什麼主張的樣子。山頂是好地方,可以眺望到全香港的景致,看得到長江實業,中銀大廈,和IFC,所謂「中環價值」,盡收眼底。沒有霧的時候,也可以遙遙地望見青馬大橋。山頂上看港大,在盤桓的山道交錯間,就好像是島。
香港是一個島,這島上還有喧囂與速度。港大是這島上的另一個島,是真正無車馬喧的清靜地。這裡面的人,便也有了島民的心態。心無旁騖,適合讀書作學問。在經歷了一年的熱鬧之後,也是在這島上,我無知覺間開始了寫作。寫過一個年輕大學教授的浮生六記,叫《無岸之河》。後來又寫了一篇《物質生活》,大約是那時候的生活寫照。寫作之外,做的更多的事,似乎是看電影。看電影是寫作和作論文間的句逗。頻繁密集,卻似乎又無足輕重。港大圖書館,有很多的影碟。我便一邊看,一邊為一個報紙寫電影專欄。寫電影終究不是很過癮的事。看完了奇耶洛夫斯基、法斯賓德、大衛林奇,終於被大島渚的殘酷任性搞壞了胃口,於是用西區柯克的推理片系列作調劑。看完了一部《鳥》,影評寫完,意猶未盡,就又動筆寫了一篇叫做《謎鴉》的小說。
那以後,寫下去,卻多是關於自己家鄉的城市,南京。
癸未.人事
二○○三年,是世界的多事之秋。美國太空梭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在著陸前於德克薩斯州上空解體。機組人員共七人全部罹難。伊拉克危機造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反戰示威活動。第一例SARS病例在越南河內出現,並在全球迅速蔓延。第三次海灣戰爭爆發。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理佐蘭.金吉奇(Zoran Djindjic)遭到暗殺。五十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要求實施雙普選。美國華盛頓州爆發瘋牛症,澳大利亞、中國、巴西和日本等國宣佈禁止進口美國牛肉。伊朗發生強烈大地震,三萬人死亡,十萬多人無家可歸,二十多個國家向伊朗派出救援隊與物資援助。
那一年的春天,我拿到了碩士學位。
一月的時候,第一次應聘了一份工作。是一份consultant的職位,具體負責在港跨國企業管理層的語言培訓。
走進中銀大廈,將領帶緊了緊,信心也充分了些。面試的氣氛友好而矜持。印象深刻的是主考的中年韓國男人。說著流利的英文和溫婉的普通話。傾聽與點頭。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安靜,只有秘書在筆記本電腦記錄時飛快的打字聲。也是溫存的,如同蠶食桑的聲響。
這次應聘最後以落敗告終,電話打來,依然是完美得體的抱歉,說希望將來與你有合作的機會。在意料之中,一個學位,或許並不比兩年的工作經驗更加有份量。這是香港的職場,用人唯用。不會有太多的時間給你去歷練與磨合。
二月的時候,在深圳的一間港資出版公司就職。
對我而言,這是新的城市。以前只是經過。它代表的只是羅湖口岸,是南京與香港間的某個過渡。
或許,深圳對於香港人而言,遠不及此。它終於成為香港人消費聖地。朋友對我說,這個角色,曾經由泰國來扮演。金融風暴後,泰國一蹶不振。港人改弦易轍,開始親近祖國最臨近的城市。這裡在一九七九年的時候,還是荒涼的地方。因為一位老人,躊躇滿志地畫了一個圈。由此改變了它的命運。
我想我是喜歡它的。大約因為它的新與闊大。這些年在香港,看了太多逼仄而狹長的天空。這城市的闊大是與南京像的,然而,卻沒有南京的古舊與曲折。歷史於南京像是一道符咒,成敗一蕭何。走在中山大道上,體會了民國子午線的悠長與幽深。法桐葉子將陽光篩在你身上,卻也有一絲涼意。這涼意也是許多年積澱來的。深圳不同,輕裝上陣。每次上班的時候,車經過筆直的深南大道,兩旁是鱗次櫛比的高樓。頭上的天,卻還是遼闊的。沒有高大的樹,有一種稚嫩,卻也是初生牛犢式的。內裡卻是膽略,無顧忌。所謂「深圳速度」,或許也有代價,便是略微地魯莽,不太計較錯對。
這城市始終是年輕。地王,深交所,華強北商圈,都是年輕的身影。我從沒感覺到自己的年輕在一個城市會如此的恰如其分。
我開始了我半年的職業生涯。在最商業的地方做最文化的事情。做故宮藏品系列叢書,與字畫、印鑒與碑拓、明清家俬打交道。工作的過程,倒是心裡很沉靜。同事們,則都是藝術的人。因為做的是出版行,卻沒有很多浮華氣。出版總監是昔日一個著名文學雜誌的編輯。說起她當年對阿城的欣賞,真誠仍溢於言表。說起阿城文字的好,至今還記得她援引的《峽谷》中的例子,說那馬是「直」著腿走來。當時編輯部的人,都說這「直」用得頗為蹊蹺,不是正常馬的所為。唯獨她力排眾議,留下了這點文成金的一字。我短暫的出版生涯,因為這總監的提護,增長了許多的見識。現在想來,是心存感念的。郝明義的理念與呂敬人的設計,也都是那個時候深入其心。多年後,當我自己出版書籍的時候,與編輯間溝通的無阻,也正是靠了那個時候的積累。
四月二日那天,天氣晴好。大巴上人頭湧動。突然有個女人的聲音尖利地響起。然後是她對同伴說,張國榮死了。似乎有很多雙眼睛向一處聚焦過來。這時候,WHO已經發動了SARS全球警報。所以這些眼睛的下方,都有一副口罩。掩藏著訝異的神情。女人的夥伴愣了一下,她的口罩上印著一張微笑的豐潤的唇。這便是無所不在的商業創意。讓SARS的陰影薄弱了一些。然而,這時候卻變得不合時宜。她聲音虛弱地說,開什麼玩笑,愚人節是昨天。所有的人都如釋重負,同時有些譴責地看著製造謠言的女人。女人將報紙遞給了同伴,說,是,真的。我在這同伴身後看得很清楚,報紙標題濃重:「歌星張國榮于香港文華東方酒店跳樓自殺身亡。」很快,電臺印證了這個消息。有人間歇開始抽泣。
「哥哥」對於很多人來說,大約是時代的專屬名詞。他的歌,電影,演唱會,他的隱退,他的情事都潛移默化於許多人的生長。當他終於老去,便以最徹底的方式演繹了浮生若夢。只是,在這身影坍塌之後,所有人等不到了風再起時。
張國榮的故去,與年底另一個巨星的隕落遙相呼應。她是梅豔芳。許多人都記得他們共同寫下香港電影的一則傳奇《胭脂扣》。曾經風華絕代的十二少,耄耋老境下,與天人兩隔的如花重逢,是悲哀卻非悲情。幾乎在這慘澹的年裡成為讖語。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小山河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1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現代散文 |
$ 237 |
現代散文 |
$ 237 |
文學作品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300 |
Book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小山河
★CCTV年度「中國好書」、「華文好書」評委會大獎、兩屆亞洲周刊十大小說得主,葛亮首部散文集。
王德威
朱天心
畢飛宇
葉兆言
劉再復
閻連科
駱以軍
嚴歌苓
──兩岸名家聯袂推薦
近日讀了葛亮的《小山河》,讀罷感嘆:沒想到這位青年作家的文字如此老道,如此精美,如此不同凡響。全書語言所蘊含的詩意與美感,讓我回到古代與近代典雅肅穆的文筆氛圍中。倘若不是作者擁有特別文化底蘊與文學才華,是絕難寫出這樣脫俗的文字的。
──劉再復
小說家葛亮,出身於六朝古都南京,祖父是藝術家葛康俞,太舅公是陳獨秀,鄧稼先則是表叔公,得天獨厚的家族底氣,傳承民國初年濃厚的人文風情,下筆從容,敘事溫厚,細膩典雅,為同輩作家中少見。此為葛亮首部散文集,全書四輯可合稱為「人行世間的光景」,有個人的成長與行走軌跡、對於舊時代及人文掌故的追述、閱讀寫作的心得、觀看電影的體會、觀照生活的種種感悟。寫故城南京、工作求學的香港文化風土,以一雙少年的眼睛去觀看久違的人與事,找尋生活裡最動人肺腑的人之常情。
葛亮從生活、行旅中觀察每座城市的人文風情,六朝煙水氣的南京、中西合璧混搭的香港、新闊的深圳、寥落的河內,「他城」與「我城」互視,異鄉人看故鄉事,讓每座城市的「氣性」鮮活出跳。對於日常、掌故更是入眼入心,談歷史造就南京人的「蘿蔔」性格,《紅樓夢》裡地道老南京腔的遺跡,從海外遇老鄉看民間巫術「問米」、「打小人」,雪暴裡吟唱的藏女、故鄉泥人師傅,兩人對生活的執念,皆是遊走民間的英雄。
民國是個好時代,葛亮以字代畫,工筆描繪一幅色藝皆美的民國百藝圖。鴛鴦蝴蝶派、朱自清、錢鍾書、魯迅、葉靈鳳、蕭紅……其人其事,躍然出紙;談吃則論引周作人吃「苦」要「閒」的隱逸氣息,陸文夫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民初服裝則少不了戀衣狂張愛玲所寫〈更衣記〉,淺談中國因人製衣傳統,看中西文化對時裝定位的差異性。另博覽西洋文學,從譯本中領略「入鄉隨俗」轉譯之美感,或由中外傳記中習得「生活」微末處最能體現時代與城市變遷。從香港電影《華樣年華》、中國電影《茉莉花開》可嗅出兩地對老上海既定印象的歧異與轉變。
生活空間的轉換,反而有躬身返照的機會,對城市的刻畫更能細膩入心,往昔因熟悉而忽略的人文掌故,也能重新自血脈中提煉顯形。葛亮常年浸濡民國文化,文字帶有時代的溫度與風雅,底蘊豐厚,學問自在流淌,在快節奏的生活中,使人領略到慢閱讀的靜謐,以及往昔時光的美好與悠長。
作者簡介:
葛亮
原籍南京。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畢業,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作品出版於兩岸三地,著有小說《北鳶》、《朱雀》、《七聲》、《戲年》、《謎鴉》、《浣熊》,文化隨筆《繪色》、《小山河》,學術論著《此心安處亦吾鄉》等。部分作品譯為英、法、俄、日、韓等國文字。
長篇小說《朱雀》獲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二○一六年以新作《北鳶》再獲此榮譽,並斬獲各項大獎。包括二○一六年度「中國好書」、「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五佳、二○一六年中版十大中文好書等。作者獲頒《南方人物週刊》「二○一六年度中國人物」。
曾獲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臺灣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作品入選「當代小說家書系」、「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二○○八、二○○九、二○一五中國小說排行榜」、「二○一五年度誠品中文選書」。
TOP
章節試閱
拾歲
說起這十年,一時間不知從哪裡開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臺上,遠處是西貢夜色裡的一灣海。明暗間是散落水中的島嶼。淺淺的海浪激蕩,島嶼便是浮動的船。
院落裡燈影闌珊,聖誕樹兀自精神。夜已微涼,姑祖父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坐在籐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願,不願意錯過熱鬧。寧願做這熱鬧裡的佈景,才會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熱鬧卻還是濃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間堆疊。小狗不知倦,將李醫生的雙胞胎留下的玩具叼著,在院落裡巡遊。姑祖母還在絮絮地和母親說話。講的依然是往事。這夜裡,將陳年的事情都釋...
說起這十年,一時間不知從哪裡開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臺上,遠處是西貢夜色裡的一灣海。明暗間是散落水中的島嶼。淺淺的海浪激蕩,島嶼便是浮動的船。
院落裡燈影闌珊,聖誕樹兀自精神。夜已微涼,姑祖父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坐在籐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願,不願意錯過熱鬧。寧願做這熱鬧裡的佈景,才會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熱鬧卻還是濃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間堆疊。小狗不知倦,將李醫生的雙胞胎留下的玩具叼著,在院落裡巡遊。姑祖母還在絮絮地和母親說話。講的依然是往事。這夜裡,將陳年的事情都釋...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一封信
祖父的遺作《據几曾看》原稿中,夾著一幀照相,是端坐的中年女子。照相的一角上,有自來水筆寫著「敏先」二字。這是祖母的字。祖母形容肅穆,目光沉鬱,無一點閨秀氣。華服之下,卻有丈夫的氣概。她懷裡攬著年幼懵懂的孩子,那是我的父親。拍照的時候,未預見家中變故,只是數年之後。祖父在中央大學教授任上染恙,是積勞成疾,終於不治而撒手人寰。從此祖母一人擔起教養子女的重任。時事艱難間,未有過放棄。直至父親兄弟三人大學畢業。次年,祖母身染陳痾,一病不起。臨去世時,只是說,不要走,我走了,家不成家了。因為祖母的...
祖父的遺作《據几曾看》原稿中,夾著一幀照相,是端坐的中年女子。照相的一角上,有自來水筆寫著「敏先」二字。這是祖母的字。祖母形容肅穆,目光沉鬱,無一點閨秀氣。華服之下,卻有丈夫的氣概。她懷裡攬著年幼懵懂的孩子,那是我的父親。拍照的時候,未預見家中變故,只是數年之後。祖父在中央大學教授任上染恙,是積勞成疾,終於不治而撒手人寰。從此祖母一人擔起教養子女的重任。時事艱難間,未有過放棄。直至父親兄弟三人大學畢業。次年,祖母身染陳痾,一病不起。臨去世時,只是說,不要走,我走了,家不成家了。因為祖母的...
»看全部
TOP
目錄
〔自序〕一封信
第一章 人世
拾歲
城池
腔調
氣味
春色
巫問
聲音
第二章 人間
江南
舌尖
霓裳
暫借
書衣
先生
無珠
第三章 行間
諸神
追譯
故事
生活
小說
文學
第四章 光景
出神
經年
滄海
鏡像
世界
伶人
〔後記〕筆記本
第一章 人世
拾歲
城池
腔調
氣味
春色
巫問
聲音
第二章 人間
江南
舌尖
霓裳
暫借
書衣
先生
無珠
第三章 行間
諸神
追譯
故事
生活
小說
文學
第四章 光景
出神
經年
滄海
鏡像
世界
伶人
〔後記〕筆記本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葛亮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ISSN:978986450132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