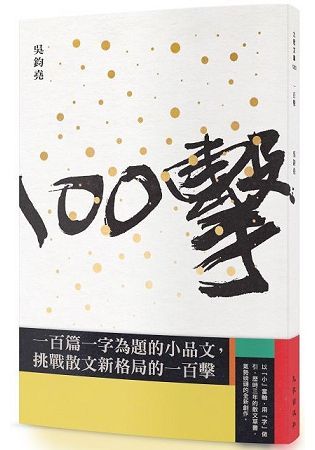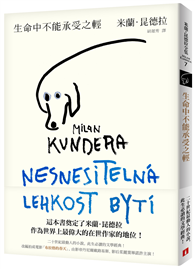一百篇一字為題的小品文,挑戰散文新格局的一百擊
以「小」當軸,用「字」做引,歷時三年餘,吳鈞堯承繼《火殤世紀》、《遺神》、《孿生》等三部小說的厚實,把散文、新詩、小說與歌謠等,納進千餘字的小品文。
短小不等於單薄,小山水亦也可氣勢磅礡,吳鈞堯自陳,《一百擊》是他放掉自我,在靜觀中破壞與建立,發揮「大刀細筆、隨寫成篇」的草書精神。三年多來,一個月僅寫一篇或完成三、四篇,終於一字一階,讓讀者一覽大刀闊斧隨意揮毫,卻句句工筆細膩,行雲流水間,自成一格的文學氣候。
一百個字,點撥一百種人生,記原鄉情感、台北文壇現象,也觸及兩岸觀察。哀悼周公夢蝶而有〈蝶〉,感念星雲大師為文〈驚〉,觀文學紀錄片,寫下對白先勇、瘂弦跟洛夫的欽敬;〈黑〉隱喻學運、〈落〉以世界盃足球賽討論東西文明、〈手〉追憶鄧麗君、〈俠〉從上官鼎的《王道劍》鋪陳武俠台灣、〈爭〉敘台兒莊參訪跟兩岸政治、〈默〉觀吳晟父子同台演出、〈栽〉自述十七年編輯生涯、〈情〉記因余光中而就讀中山大學,〈雷〉、〈雨〉、〈靜〉、〈撞〉等,情感描繪句句靜好,〈移〉、〈濘〉、〈縫〉與〈惜〉,載親情於滄桑流轉。
最末篇〈均〉寫著,「我走進一個字、再出走」。字,本來未曾著相,守握得美好完整,都是為了有一天,用不同面貌與讀者重逢:一旦遇見了,就開始偏心。偏心向你,「你是人間的一個字,以及又一個字」。《一百擊》寫歲月、寫人生,像個文字羅盤,指向時間之河的長與寬。
本書特色
★散文書寫繁多,有以主題、有以形式等,各領風騷。近期台灣散文創作,家族寫作潮流方興未艾,另還有「大散文」以大氣魄寫出長篇小說格局,本書反其道而行,以小品文為主,企圖挑戰散文的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