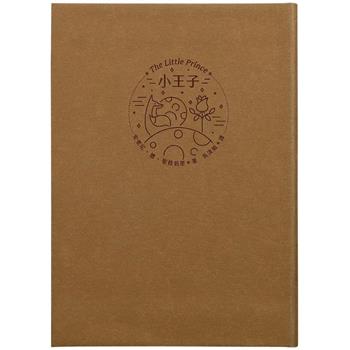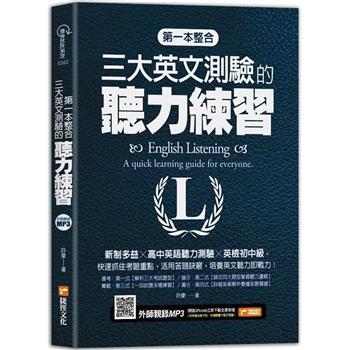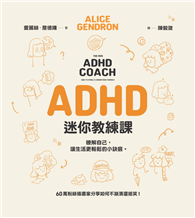曹文軒、甘耀明 作序推薦
則臣在講故事,但沒有放下身段來講,更沒有蹲下來講。他就那麼講——似乎並不特意地給孩子講。但我想孩子會喜歡聽的,因為他無論怎樣講,那個故事卻是一個孩子喜歡的故事。一個神話的、傳說的、魔幻的神祕莫測的故事。──曹文軒
《青雲口》塑造出來小說思維、張力與細節,可以互補徐則臣對都市文學的描摹,更適合一般讀者閱讀。同時這本書的誕生對徐則臣的小說世界觀是重要的拼圖,並且多了不同的閱讀樂趣。文字摹寫現實的火候高妙,那種如閃光燈補光的技巧中總能照見更細微的人生細節,多了與眾不同的力道。──甘耀明
「一千四百二十六條船,首尾繞著青雲河圍成一圈。」
「泱泱大水上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組合:一隻喜鵲飛在前頭探路,兩隻凶猛的老鷹各叼一根繩頭在拉著門板飛,門板上三個人和一隻既像熊又像猩猩的動物彎著腰拚命划水,站在他們前面的是一隻鬍子都白了的貓頭鷹,一邊跺腳拍著翅膀一邊喊,一二加油!一二加油!」
青雲口的天那叫一個藍,青雲口的雲那叫一個白,空氣清新能洗心、洗肺、洗眼睛……外面的人是這樣說的。和充滿霧霾、動物死絕的外面世界相比,青雲口就是桃花源。世代居住於青雲谷的古家小男孩古里,能聽懂且模仿動物的語言,青雲山上似熊似猩的動物,名叫古怪,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日,一千四百二十六條船上頭,搭載了鋼筋水泥混凝土,還有些奇怪的工具,一群西裝革履的不速之客,招搖地闖入淳樸悠閒的青雲口,說要為青雲口的鄉親帶來現代舒適美好的生活。
他們造橋修路,開山炸石,引得山上動物惴惴不安,只有古里與古怪發現,外面的人靜悄悄地在東此角吹不到風的所在,準備大興土木。另一方面,外人為青雲口人而蓋的「青雲口紀念碑」每晚離奇地遭到破壞,引起眾人熱議,一晚,識破詭計的古怪在紀念碑被抓了,前來營救的動物夥伴也一隻隻的被誘捕,為了營救好朋友,小男孩古里學會了貓頭鷹語,與獵人父親上山尋找「棋王」貓頭鷹,與古怪的叔叔「智多星」,展開營救動物的行動。
建築愈蓋愈高,鎮日砰砰轟隆之聲不絕於耳,青雲口的村民與動物都感受到地底有不尋常的動靜,他們將面臨怎樣的巨大災難?
徐則臣從虛幻的世界裡,打造一座現實人性的試煉場,讓商人的利誘與老祖宗有形無形遺產相互衝撞,以開放的視角,讓不同的價值觀彼此影響發酵,不論站在任何一方,自然的反撲,影響皆是全面的,沒人逃得掉。充滿想像力又天馬行空的故事中,人與動物跨越了語言溝通與物種差別的障礙,發展出信賴、互助溫暖情義。這是一部創世又滅世的寓言,隱約透露著哀傷,卻又積極尋找生命的出口與希望,看似奇幻的世界裡,上演的皆是真實的人生。
本書特色:
★小說家徐則臣為青少年而寫的故事。充滿奇幻色彩,以虛寫實,老少咸宜。
★搭配11幅精美插圖。
作者簡介:
徐則臣
一九七八年生於江蘇東海,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現居北京。
著有《午夜之門》、《夜火車》、《跑步穿過中關村》、《居延》、《把大師掛在嘴上》、《到世界去》、《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
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老舍文學獎、短篇小說《如果大雪封門》獲魯迅文學獎,並曾獲莊重文文學獎、春天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
二○○九年赴美國克瑞頓大學做駐校作家。二○一○年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章節試閱
一千四百二十六條船。石壁上一大片劃痕,每條船從洞口裡划進來,古里都用尖角石塊畫一條線。古怪挺著長滿黑毛的大肚子,站在古里身邊幫他數,超過兩百它就亂。人類創造出如此龐大的數字它不能理解,但它願意相信古里,這小子說夢話時算術都一流。古怪沒見過這麼多船,古里也沒見過,整個青雲口的人都不曾見過。一千四百二十六條,首尾相接,沿青雲河繞了一個大圈,第一條船的船頭抵在最後一條船的船幫上。整個船隊像個尾巴來不及長大的逗號。等船上的貨物卸空以後,最後一條船必須挪出個空檔來,第一條進入青雲口的船才能順利地劃入青雲洞口,然後是九曲回腸的青雲洞,如同一截幽暗的盲腸輾轉地連接上外面的世界。
在這樣一個天高雲淡的中午,洞外的世界天是灰的。如果不下雨,那裡的半空中就飄滿粉塵、煙霧和風的混合體;在那裡,你要是能跳得足夠高,然後伸出舌頭,你會同時嘗到鹽、醋、芥末和石頭渣的味兒。你還會聽到雷聲從大地上往高處翻滾,因為那裡喧囂異常,穿體面華美衣服的男人和女人都喜歡扯著嗓子說話。幾年前父親就告訴過古里,那些人把生活弄得像一場沒完沒了的尖叫,跟他們有關的任何東西都必須把聲音放到最大才能被別人聽見。古里沒去過那裡,但這一點很明顯,僅一千四百二十六條船撐篙和划槳的聲音就像山洪在暴發;船上的陌生人還挑起脖子相互搭訕,說粗俗的笑話,整個運輸就成了一場亂糟糟的、浩大的戰爭或逃亡。午睡的青雲谷人全醒了,把頭從窗戶裡伸出來,最博學的人也沒見過這麼多船,也沒見過船上裝載的那麼多的磚瓦琉璃和鋼筋水泥混凝土,還有一些奇怪的工具。
「他們真要把路修到山頂?」古怪揪著腦門上的一撮白毛。
「你相信?」古里抬起頭,青雲山高到了天上去,翅膀小一點的鳥都飛不過去。「放心,沒人找得到你的窩。」
古怪住在一個葫蘆形的山洞裡,洞外有棵大樹,各種藤蔓從枝杈上垂下來,四季有不同野花為牠遮住洞門。半夜裡餓了,古怪睜著半隻眼,迷迷糊糊抓住根粗藤吊上去,晃晃悠悠的時候逮哪抓哪,到手的野果子都能吃。這是牠有生以來的第十二個住處,被凶猛的豹子和老虎追趕過,被狡猾的狐狸和豺狼算計過,也被鼻子都能識路的獵人盯上過,過去的三年就搬了四次。再不會有比葫蘆形的洞穴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總想著逃亡,那你一輩子都得逃亡,古怪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十二是極限。古里說,人類不喜歡十三,不吉利;更不喜歡十四,尤其不吉利。人不喜歡的,牠也可以不喜歡。但是兩公里外有條水泥石階路,已經修到牠站在洞門前就能看到的地方了。有天夜裡,牠夢見那條路在黑暗中拐了一個陡峭的彎,如同凶猛的巨蟒,直奔牠的葫蘆洞。
「來過這裡的只有你。」古怪把兩隻若有所思的雄壯前掌搭到古里肩膀上,按一下。
古里翻個白眼,「瘦得口水都沒了,我都懶得賣你。要沒我,你也就是一頭熊,頂多是隻大猩猩!」
熊還是大猩猩,古怪自己也拿不準。也不需要拿得準,牠是自己就行了。牠生來就是自己,從小長到現在,除了塊頭越來越大,沒變過樣。古里之外,沒人也沒有哪隻動物告訴牠牠是誰。牠是誰是個不需要證實也不需要證偽的問題。開始古里覺得牠長得像熊,後來又覺得牠長得像猩猩,等到給牠取了名字以後,牠是誰也不重要了。牠是古怪就行了。古里給牠取的名字叫「古怪」。古里叫古里,他說古怪這個名字好。那就古怪吧,古怪想,反正人類經常這麼古里古怪的。
古里十二歲,姓古,叫古里。當初爸爸給他取這個名字時,是不是想過再給他生個叫古怪的弟弟?現在古遠峰不打算再生了,青雲口就這麼大,人多了擠不下。生了也養不起,照古里媽媽的抱怨,古遠峰目前的狀態,養活他自己都難:說獵人不像獵人,出門還得背著畫板和素描本,放十天槍能打回來一隻野兔就算高產;說畫家也不像畫家,在家裡鋪開紙作畫時,嘴裡念叨的卻是打獵的那點事。為此媽媽總說,你給兒子取名古里算是取對了,你該改名叫古怪,真是一對親爺兒倆。那是因為古里也愛往山上跑,再熱的天也不睡午覺,一閃眼人就沒了;跟他爸一樣,古里也喜歡那些畫在紙上的動物。就是在爸爸的畫上,古里見到了既像熊又像大猩猩的古怪。
那時候古怪還只是一種野獸,出入在青雲山的叢林和亂石間。古遠峰畫下了牠無數次一閃而過的表情。那時候古怪還很胖,耳朵好使,一旦猛獸和獵人近到牠百米以內,縮在長毛髮裡的短耳朵就會自作主張地抖,睡夢中牠也會醒,然後撒丫子就跑。現在瘦了,腮幫子都陷下去了,進出青雲口的人太多,那些谷外來客開始在山下造房子修路,一天到晚叮叮噹噹,就跟在牠腦門子上幹活兒一樣。最怕的是偶爾開山炸石頭,轟隆一聲巨響,整個青雲山都要蹦一陣子,牠覺得彷彿在夢裡撞到了葫蘆洞的洞頂上,滿眼冒金星,醒來經常能在額頭上摸到一個疼痛的包。
石階山路爬升的速度很快,一級頂著一級,頭天晚上抹好的水泥第二天一早就乾了,堅硬、慘白,什麼人都可以攀著臺階往上走。這才是真正的噩夢,石階路可以在夢裡拐個彎直奔葫蘆洞,人類就可以踩著這些路,耀武揚威地堵在它的洞口前。
因為憂慮和恐懼牠瘦了。
可是外來人的闖入勢不可擋。早先只是零零散散來幾個人,圍著青雲山、青雲谷和青雲河轉一圈,一路指指戳戳、眉開眼笑、頻頻點頭;接下來一群群人同時進來,領頭的後脖子處插著一面三角形的彩旗,舉著一個電動大喇叭,把所有地方都給數據化,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河有多長,動植物分門別類多少科目種屬,拱橋和板橋分別有幾座,房屋有多少,所有人坐到八人一桌的酒席前可以擺多少桌。聽上去頭頭是道,但沒幾個數字是對的。古里就可以保證,單是青雲山之高,就沒人能說出個具體的數,一個人都沒有,學問大到了他爺爺古瘦山那樣也做不到。然後他們突然彎下腰,開始敲敲打打,修補起了房屋、石橋和山路。為什麼呢?他們說,要為青雲口的發展略盡綿薄之力,青雲口的人端上山茶和野菜感謝他們;然後他們說,能不能在谷裡多住幾天啊,你看這山多美、水多清、空氣無比新鮮充滿了負氧離子,還有青雲谷人,善良、淳樸,男人強壯、女人美麗,小孩子見到陌生人都面帶微笑,真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啊,能在這地方過上三五天,死也值了。青雲口人哪能讓他們死呢,那就住下吧。他們住下就不願走了,開始在河邊和山腳下造一座自己的小房子。反正也不占地方,隨他們去。然後,來了一個大肚子男人,掐著腰把青雲口看了一圈,走了;又來了一個肚子更大的男人,看了一圈又走了;來了三個大肚子男人之後,突然來了瘦得風一吹就要倒的女人,她說為了瘦成這樣,花了很多精力和錢。她和大肚子男人們一樣,揮起手,對著青雲山和青雲口劃拉一下,半個山谷都在她懷裡了。她跟他們說的一樣,都是:留下,多錢都留下。她跟他們一樣,在青雲口走走停停時,身後都有一個人幫她打傘,陰天遮風擋雨,晴天防紫外線。再然後就到了現在,古里來葫蘆洞找古怪玩,一歪頭看見青雲口出來一條船,又出來一條船,連出來六條船古里就覺得出事了,他下意識地撿起一塊尖石頭,在葫蘆洞口畫起了豎線,一畫就畫了一千四百二十六條。他和古怪把腿都站麻了。
「你們要把我們趕走!」古怪的聲音突然尖利起來,語速之快古里都沒能反應過來。
「你說什麼?」古里讓它再重複一遍,「慢點兒。」
古怪仍然聲色俱厲,比畫著兩隻毛茸茸的大手,每一個口型和發音到位得都有點兒誇張了:「你──們──要──把──我──們──趕──走!」
古里聽懂了。他基本上掌握了古怪的常用詞匯和發音規律。沒有人相信古里能聽懂這隻既像熊又像猩猩的動物的語言,但古里就是懂了。他還能跟它交流,幾乎和正常人交談一樣流暢。他說不好古怪的語言跟人究竟區別在哪裡,總結不出來,只有聽見了,他才能說出它表達的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一天半夜,他突然醒來,覺得應該跟爸爸說實話,他說:
「爸爸,我能聽懂動物說話。」
古遠峰右手在他腦袋上劃拉了一下,「說夢話呢,兒子?」爸爸說,「有尿沒?沒尿趕快睡覺。」
他就不再提這事了。反正他說了,沒撒謊。不信最好,古怪一直囑咐他,不要告訴任何人他能聽懂它的話。「你們是好人,」古怪說,「但一看見我們,你們就變成壞人了。」
它還是牠。牠跟古里說過,牠們動物都這樣,更凶猛的野獸牠們固然也怕,最怕的還是人。「人不講公平,攥著刀、端著槍就來了。有幾個跑得過子彈?」古怪說,「有的人更壞,挖了陷阱還放炸藥。我們動物打架,憑的是力氣和智慧,所有武器都來自我們的身體。」
也因為這個原因,古里開始幾次遠遠地跟它說話,古怪都裝沒聽見或者聽不懂。那時候古里掌握的詞彙和發音還很少,但隔三差五還是能說出幾個關鍵詞,古怪聽了頗為心驚。要在平常,誰窺見了牠的行蹤,牠先是本能地躲,躲不掉了就會衝上去,一巴掌拍死。對古里,它下不了手,這小東西竟然發出了它的聲音。他對牠遠遠地喊:
「嗨,我,你,朋友,喜歡。」
牠瞥他一眼,繼續躺在石頭山曬太陽、撓癢癢。
古里繼續喊:「我,古里,你,喜歡,朋友。」
牠側起身,有點意思了,這個小人真會說自己的話?它用嚇唬的語氣瓮聲瓮氣地說:「你再說一遍!」
古里以為牠真生氣了,縮著脖子退後幾步,站住了又感到興奮,牠回話了!牠是讓自己再說一遍嗎?「古里,你,喜歡,朋友!」
古怪從石頭上坐起來,戒備心仍在,牠問:「就你一個人?」
古里猜大概就這意思,拍著小胸脯說:「我,古里,一個。」
古怪站起來,往更密的樹林裡走,說:「明天你再來。」
一千四百二十六條船。石壁上一大片劃痕,每條船從洞口裡划進來,古里都用尖角石塊畫一條線。古怪挺著長滿黑毛的大肚子,站在古里身邊幫他數,超過兩百它就亂。人類創造出如此龐大的數字它不能理解,但它願意相信古里,這小子說夢話時算術都一流。古怪沒見過這麼多船,古里也沒見過,整個青雲口的人都不曾見過。一千四百二十六條,首尾相接,沿青雲河繞了一個大圈,第一條船的船頭抵在最後一條船的船幫上。整個船隊像個尾巴來不及長大的逗號。等船上的貨物卸空以後,最後一條船必須挪出個空檔來,第一條進入青雲口的船才能順利地劃入青雲洞...
作者序
後記
有了孩子以後,和每一個決意當個稱職父母的作家一樣,我打算為兒子寫一本書。開始我想寫一本兒子的成長日記,他成長,我記日記。我認真觀察他的每一點變化,在差不多三年的時間裡,我記錄了我耳聞目睹到的每一個「第一次」:出生,第一聲啼哭,第一次吃奶,第一次拉臭臭,第一次睜開眼睛盯著我看,第一次對我揮起小拳頭,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在我身上撒一泡尿,第一次放了個屁把自己嚇著了,第一次坐起來,第一次叫爸爸媽媽,第一次說出主謂賓和標點符號都完整的句子,第一次耍了個小心眼,長出第一顆牙齒……當作家就這點便宜,紙和筆隨時隨地備著,我像個敬業的書記官,忠直地記錄一個生命面對陌生世界的每一點驚喜。記下了也就記下了,翻開專用的記錄本,我常常對那一堆散盡碎銀心生疑慮,我忘了這種記錄是個流水帳,不管多詳盡它也只能是個流水帳。而在我設想中,它應該是一本書。作家的職業病發作,我不能忍受一本沒有結構的書:比如長篇小說,一部可以隨時接續下去的長篇對我來說是不合法的。我過不去。繼而再想,這些「第一次」只對我有意義,每個孩子的都這麼點點滴滴相似地成長起來,別人為什麼要看你家娃娃的流水帳?給兒子寫一本書的念頭出現了障礙。起碼這樣一本書不行,我還是過不去。那麼,得什麼樣的一本書呢?
——童話。當然是童話。
我沒寫過童話。多年的寫作,不管如何現代和後現代,夯實的都是現實主義的底子。我只在現實的、日常的邏輯裡運行故事。但童話不必如此,可以一上來就魔幻,就飛到天上去,它有它的天馬行空的邏輯。這麼說事情就簡單了,我得從我習慣的「現實邏輯」的「真實」中解放出來。二○一三年,我寫完了長篇小說《耶路撒冷》,歷時六年的「現實主義」大山終於從後背上卸下,我有種身輕如燕的快慰。那時候,每天晚上我去人大附中的操場上跑步,跑久了,腳步也有種「超現實」的輕盈,那狀態可能特別「童話」,我就想,不能再等,必須「童話」了。合適的狀態不是說來就來的,但可能說走就走。剛寫完沉重的《耶路撒冷》,我也希望能儘快從《耶路撒冷》沉鬱浩茫的狀態中走出來,換一種思維和想像方式,挑戰多多益善。然後,題為《青雲口》的童話開始了。
開頭寫得很順。一個孩子每天翻看父親畫的動物,根據牠的神態和口型,學會了那只動物的語言。他和那隻自己都分不清是熊還是猩猩的動物成了朋友。他叫古裡,他給朋友取名古怪。他住在青雲谷,牠住在谷邊的青雲山上。有一天,一群山外的不速之客穿過盲腸般的青雲洞,來到了這個化外的桃花源。古里和古怪,他們站在半山腰,看著一條條小船從青雲口吐出來,出來一條,他們在石壁上畫一道線。一共畫了一千四百二十六道線──故事開始了。
開始就停下了。記不清什麼原因停下,一停就是三年。三年裡,每天都弄得自己很忙,但年年除夕檢點,也沒看出忙出什麼所以然來。時光就這麼經不起揮霍。聊可安慰的是,二○一六年上半年寫完了一個小長篇《王城如海》。寫完《王城如海》,突然發現,《青雲口》停下來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王城如海》裡,我寫到一隻詭異的小猴子。牠小到可以藏在主人的上衣口袋裡,但因為對氣味非凡的敏感,一個幽暗複雜的隱祕世界在牠的鼻子底下展開了。在現實主義的北京城,鑽出來一隻超現實的印度小猴子,牠的主人,教授的混血兒子,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聽懂牠在嘰嘰喳喳說什麼的人。他們的交流,給這個現實主義世界的帷幕掀開了超越的一角。
必須承認,寫作《王城如海》時,我一次都沒想過中斷的童話,寫完了回頭看,聳然一驚,這只名叫湯姆的猴子分明是從《青雲口》裡來的。沒有和古裡整天混在一塊兒的古怪,就沒有鼻子靈異的湯姆。古怪停滯在童話的開頭,原來是為等候這只來自印度的小猴子。
《王城如海》結束後,我重新撿起了童話。寫下去我發現,《青雲口》沒有白等,《王城如海》給它提供了筋骨。我似乎也慢慢找到了當初寫作中斷的原因了。說起來很簡單:只寫一個能與人交流的動物故事,再天馬行空、天花亂墜也是不夠的;它得解決我的問題,它得有意義。我無從判斷一個作品的意義可能是什麼,但我知道它對我的意義是什麼。可以飛起來,但它必須是從堅實遼闊的大地上飛起來。無論起降多高飛赴多遠,它都知道大地正以相應的速度升沉和鋪展,它到哪裡大地就會像布匹綿延不絕地鋪陳到哪裡;它們之間有個忠貞的契約般的張力。我需要在《青雲口》中找到這樣一片堅實可靠的大地。在我的理解裡,這片大地將是一個好童話的筋骨。
《王城如海》寫到霧霾。那是因為整個寫作的過程裡北京正被霧霾圍困,而我四歲多的兒子也飽受霧霾之苦,他的小嗓子對霧霾過敏,他在二○一六年曠日持久的霧霾中夜以繼日地咳嗽。霧霾和霧霾的痛苦是我日常生活最重大的內容之一,就算我努力閉目塞聽,絲絲縷縷團狀霧狀塊狀無窮無盡無始無終沒完沒了的霧霾也會穿過門窗的縫隙來到我的稿紙上。無法不寫到它。但我僅僅是寫到而已,不管如何濃墨重彩,作為物理和化學的霧霾非我本意,我更想寫的是人物內心的霧霾。環境惡劣一點不可怕,使使勁兒,假以時日終能夠解決;可怕的是霧霾彌漫了內心,占據了我們的靈魂,那才要命。我一門心思把霧霾往人心裡寫,物理和化學意義上的霧霾被放在一旁。那麼,環境問題究竟會怎樣改變我們的世界?如果這個世界終將被改變,如何改變?路徑可能會有哪些?這個世界,還有哪些東西形如霧霾,正在或者已然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我把一千四百二十六條船算在一個叫創世的谷外資本集團的帳上,他們來到這世上最後一塊沒被污染和侵害的淨土,這世上最後的桃花源。這是我能想到的為數不多的可以迅速改變世界的路徑之一。創世集團要開發旅遊,要大興土木搞房地產。古里和古怪將會一次次看見一千四百二十六條船,他們通過兩個世界唯一的通道,運輸進足以原樣拷貝谷外世界的設備和原料。果然,他們把所謂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帶給青雲谷的同時,也在像美國的香蕉公司毀掉《百年孤獨》中的馬孔多一樣:創世即是末日。
當然不能忘了古怪。事實上整座青雲山上的動物都不能被忘記,因為谷外的世界歷經連年污染與禍害,連像樣的家禽和寵物都絕跡了。創世集團想到了動物園。為什麼不把傳說中的動物們關到籠子裡,讓谷外的世界開開眼呢?旅遊和房地產需要它們,它們才是山清水秀的最佳形象代言。這其中,還有一個能與人類深入交流對話的動物古怪;讓它在劫難逃。
事實正是如此,他們抓住牠,他們抓住牠們。他們轟隆隆地加速度地改變這個世界,直至一場真正的創世紀的洪水來臨。人類和青雲山上的生靈們尋找新的出路,他們發現了真正的青雲口,千百年前,先祖們穿過青雲口來到谷裡,現在,他們要穿過青雲谷,尋找另外一個世界。
經由《王城如海》,我找到了通往《青雲口》的線索。我把故事梗概講給朋友們聽,他們讚嘆故事的同時,普遍質疑,一個童話你搞那麼複雜,確定沒想多?我反問,童話該想多少?他們閉上眼,看見了一張張孩子的臉。他們說:孩子的表情是檢驗童話的唯一標準。對《青雲口》,孩子們張大嘴瞪大眼,什麼霧霾、污染、環保,什麼現代化、城市化、馬孔多,跟他們有半毛錢關係?我就知道會是這結果。必須溫情脈脈,必須美侖美奐,必須天真無邪,必須捏著嗓子說話,必須讓藝術自足地空轉──因為我們擔心愛和真善美受到現實的侵襲,我們必須給它們扣上一個絕緣的玻璃罩子才能放心,就像「楚門的世界」。這恰恰是我不能忍受的。誰說孩子必須在無菌的環境裡才能生長?誰說孩子與成人之間必要有一條認知上的楚河漢界?誰說給孩子看的就只能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才安全?誰說童話只能給孩子們看?誰說孩子就不能在童話的閱讀中培養起關注現實生活的能力?誰說孩子就不應該去閱讀那些需要踮起腳伸手夠一夠的文學?誰說十六歲、二十六歲、三十六歲一直到八十六歲、九十六歲的老人不能看?這樣的疑問我可以列出一大串。
其實不唯童話,幾乎所有文體都被我們養出了一身戰戰兢兢的壞毛病,像家畜那樣馴順、嬌氣,寫出來唯恐不像該文體,不像該文體中的經典長相。似乎經典長著一張自帶游標卡尺的臉,尺寸不合就非我族類。就童話,我是個外行,半路殺出的野狐禪。也好,不懂規矩那就不必謹小慎微去持守,只循著我的路子來,理想中的童話是什麼樣,我就往蒼茫的五官逼近。打開楚門透明的生活籠罩,也打破成人與兒童的界限,放陽光和陰霾同時進來,照亮一張張真實的臉。
於是,有了《青雲口》。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知春里一八○四
後記
有了孩子以後,和每一個決意當個稱職父母的作家一樣,我打算為兒子寫一本書。開始我想寫一本兒子的成長日記,他成長,我記日記。我認真觀察他的每一點變化,在差不多三年的時間裡,我記錄了我耳聞目睹到的每一個「第一次」:出生,第一聲啼哭,第一次吃奶,第一次拉臭臭,第一次睜開眼睛盯著我看,第一次對我揮起小拳頭,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在我身上撒一泡尿,第一次放了個屁把自己嚇著了,第一次坐起來,第一次叫爸爸媽媽,第一次說出主謂賓和標點符號都完整的句子,第一次耍了個小心眼,長出第一顆牙齒……當作家就這點便宜,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