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島有著數不盡的軼事,每段歷史風華翩翩,是小說發想的珍寶庫。
在臺灣歷史的轉折處,能否編織出萬花撩亂的幻境?
五位年輕小說家跳脫傳統,以日治時代為背景舞臺,以「小說接龍」形式為手法,
創作出獨屬於臺灣的「時代小說」。
五位備受矚目的新生代小說家──何敬堯、楊双子、陳又津、瀟湘神、盛浩偉,聯手以臺灣罕見的「小說接龍」形式來進行合寫,主題以「一把鑰匙」作為串聯,各人依照各自的寫作風格,來寫作一篇小說。
全書故事發展的時間逐篇循序漸進,從第二人開始即要接續上一篇故事的走向繼續寫作。故事開始於三○年代,最終章則結束在戰後初期。計畫由何敬堯發起,五位作家一拍即合,主軸定位在歷史和文學,主題聚焦於「臺灣日治時期」與「藝文界」,企望能以嶄新視野,書寫出截然不同的時代故事。
整部小說因以日治時期為舞臺,並以曾創辦《華麗島》雜誌、風格浪漫耽美的日治時代作家西川滿作為關鍵角色,故以「華麗島」一詞鑲入書名,日文意為「鑰匙」的「鍵」字則為副標。
故事的火花意外地從郭松棻家族的一段軼事開始,在一篇〈郭松棻訪談錄〉中提到,呂赫若逃亡前,曾將一串鑰匙交給膠彩畫家郭雪湖,也就是郭松棻的父親。不過,郭松棻始終不知道那串鑰匙有何作用。這則故事的懸疑感讓五位作家印象深刻,隨即一致認同將它作為小說接力的故事核心主線,創作圍繞這串鑰匙依序前進。
五人各自擅長的領域都不同,揮筆寫下的故事都超乎想像,奇趣盎然。何敬堯打頭陣的〈天狗迷亂〉,以來無影去無蹤的妖怪天狗展開謎團,接棒的楊双子筆鋒一轉,寫出𡢃婢晉身的姨娘與千金小姐之間淒美的百合愛情故事〈庭院深深〉。
第三篇則由純文學和輕小說兼擅的陳又津端出了畫家與兩位美少年關係暗潮洶湧的BL小說〈河清海晏〉,氣氛唯美感傷。下一位瀟湘神接招的〈潮靈夜話〉劇情整個超展開,將BL情節中的少年之死朝神祕謀殺案方向推進。
最後一棒盛浩偉偉責任重大,謎團將如何巧妙被解開,關鍵的鑰匙背後又有什麼樣不可思議的故事呢?且看五位作家各自迥異的特色所交織出來的故事如萬花筒般,色彩斑斕相異地魔幻流轉,勾起對那段風華瑰麗的鯤島年代的無限想像。
本書特色
★五位備受矚目的新生代小說家聯手創作
★以臺灣罕見的「小說接龍」形式來進行合寫
★集妖怪、傳奇、BL、百合故事於一體
| FindBook |
有 13 項符合
華麗島軼聞:鍵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6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5 |
二手中文書 |
$ 225 |
小說/文學 |
電子書 |
$ 252 |
奇幻\科幻小說 |
電子書 |
$ 252 |
小說 |
電子書 |
$ 252 |
小說 |
$ 284 |
小說 |
$ 284 |
中文書 |
$ 284 |
現代小說 |
$ 284 |
現代小說 |
$ 284 |
文學作品 |
$ 284 |
中文現代文學 |
$ 317 |
小說 |
$ 360 |
Book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華麗島軼聞:鍵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何敬堯
小說家,一九八五年生。風格橫跨奇幻、歷史、推理。臺中人,臺大外文系、清大臺文所畢業。
榮獲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臺大文學獎,美國佛蒙特藝術中心駐村。
著有懸疑小說《怪物們的迷宮》、時代小說《幻之港》,散文《佛蒙特沒有咖哩》。編寫妖怪百科書《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
楊双子
本名楊若慈,一九八四年生,臺中烏日人,雙胞胎中的姊姊。
百合/歷史/大眾小說創作者,動漫畫次文化與大眾文學觀察者。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教育部碩論獎助,以及文學獎若干。出版品包括學術專書、大眾小說、動漫畫同人誌。近作為《花開時節》、《撈月之人》。現階段全心投入創作臺灣日治時期歷史百合小說。
陳又津
臺北三重人,任職媒體。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二○一○年起,陸續獲得角川華文輕小說決選入圍、新北市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冠軍、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劇本佳作、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等。出版有小說《少女忽必烈》、《準台北人》。網站:dali1986.wix.com/yuchinchen
瀟湘神
本名羅傳樵,一九八二年生,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主食為推理與奇幻。
既是小說創作者,也是實境遊戲設計師。著有《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帝國大學赤雨騷亂》,參與《唯妖論》的部分考察,也是實境遊戲《城市邊陲的遁逃者》的原案。目前熱衷於尋找在地創地的各種跨領域可能。
盛浩偉
一九八八年生,台北人。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台灣文學研究所,赴日本東北大學、東京大學交換。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參與編輯電子書評雜誌《祕密讀者》。著有散文集《名為我之物》。
何敬堯
小說家,一九八五年生。風格橫跨奇幻、歷史、推理。臺中人,臺大外文系、清大臺文所畢業。
榮獲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臺大文學獎,美國佛蒙特藝術中心駐村。
著有懸疑小說《怪物們的迷宮》、時代小說《幻之港》,散文《佛蒙特沒有咖哩》。編寫妖怪百科書《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
楊双子
本名楊若慈,一九八四年生,臺中烏日人,雙胞胎中的姊姊。
百合/歷史/大眾小說創作者,動漫畫次文化與大眾文學觀察者。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教育部碩論獎助,以及文學獎若干。出版品包括學術專書、大眾小說、動漫畫同人誌。近作為《花開時節》、《撈月之人》。現階段全心投入創作臺灣日治時期歷史百合小說。
陳又津
臺北三重人,任職媒體。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二○一○年起,陸續獲得角川華文輕小說決選入圍、新北市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冠軍、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劇本佳作、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等。出版有小說《少女忽必烈》、《準台北人》。網站:dali1986.wix.com/yuchinchen
瀟湘神
本名羅傳樵,一九八二年生,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主食為推理與奇幻。
既是小說創作者,也是實境遊戲設計師。著有《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帝國大學赤雨騷亂》,參與《唯妖論》的部分考察,也是實境遊戲《城市邊陲的遁逃者》的原案。目前熱衷於尋找在地創地的各種跨領域可能。
盛浩偉
一九八八年生,台北人。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台灣文學研究所,赴日本東北大學、東京大學交換。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參與編輯電子書評雜誌《祕密讀者》。著有散文集《名為我之物》。
序
序
華麗時代的圓桌會
◎何敬堯
從二〇一三年開始連載的漫畫《文豪野犬》,朝霧カフカ原作、春河35作畫,以「日本文學家」擁有「超能力」的人物設定,讓這些異能者在日本橫濱展開超能力大戰。這部異想天開的作品極為熱門,甚至有了小說、動畫等聯動創作。
諸如中島敦、芥川龍之介、與謝野晶子等知名作家與其作品,皆是取材對象。例如名喚太宰治的角色,他的異能力稱為「人間失格」,能憑接觸就讓對手的異能無效化。
故事設定很大膽恣意,但轉念一想,這種靈活多變的創作,是否也為日本文學家的形象增添更趣味的觀點?
新時代的想像
純文學一向不是日本年輕人的閱讀首選,可是當出版社將太宰治的《人間失格》與中島敦的《山月記》書封換成了春河35繪製的帥氣人像,銷量大幅提升,許多年輕讀者藉此踏入純文學世界。日本向來擅長利用漫畫作品振興觀光,所以當「與謝野晶子紀念館」在二〇一六年與《文豪野犬》合作之後,館方也驚訝發現,本來大多是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參觀者,展覽期間的中小學生參觀人數,竟是去年十倍以上。
文學,能不能有更多不可思議的想像?
日本創作者能以多變觀點翻轉文學形象,這種「改編」的能力,是從日本習以為常的歷史改編創作而來。不管是小說、漫畫或電影,若涉及日本歷史,總會在正史以外創造全新的詮釋空間。
例如夢枕貘小說《陰陽師》,讀者津津樂道安倍晴明與源博雅的友情,但在史實,兩人是否相識卻有待考察。石井步的漫畫《信長協奏曲》,則讓現代日本人三郎與織田信長交換身分,重新演義戰國傳奇。
此種超脫史實的故事創作,正是日本文學中「時代小說」的重要特色。在小說分類上,歷史小說強調史實基礎,注重人物的真實與歷史事件的價值。不過在日本文學發展上,也有「時代小說」的存在。時代小說儘管也涉及歷史,但真實人物、歷史事件並非其核心,而是更側重於以古代為背景來撰寫新穎故事。若觀察當代中國、韓國的通俗文學,依循此理的歷史穿越小說正大行其道。
歷史,能不能有別開生面的創造?
文學與歷史的幻境
世界不一定只能從固定角度觀看,尋覓史實之間的罅縫,擊破既定印象的銅牆,在小說的泥壤上,文學與歷史的嫁接肯定能綻出與眾不同的花種。
猶如天馬行空的《文豪野犬》不斷刺激筆者心緒,回顧臺灣本身,也引發一項疑問:以臺灣歷史為舞臺的時代小說能不能更多?
臺灣島,千百年以來是原住民游耕游獵之地,十七世紀之後相繼接受西方人、漢人、日本人……各種文化的進入。不論是大航海時代抑或清國時代,不同的民族在相互抗衡、交流、融合的過程中,臺灣逐漸成為擁有多元特色的海島國家。而在日本時代的殖民史,臺灣文化、社會更加錯綜複雜。
臺灣島每一段歷史,曼妙風華無與倫比,皆為小說取材的靈感泉源。
島嶼中部的大肚王,曾統領一座龐大的平埔王國,熱蘭遮城的四角稜堡閃耀夕暉,沿岸的清國時代港口傳來漢族水手的吆喝,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展櫃中,藍地黃虎旗摹本兀自鋪展――隱藏在旗面底下的日夜雙面旗真相,還要等待一百年後才會揭曉。
臺灣島有著數不盡的軼事,每段歷史風華翩翩,是小說發想的珍寶庫。在臺灣歷史的轉折處,能否編織出萬花撩亂的幻境?
儘管只是個人荒誕的空想,儘管只是棉薄之力,卻時時刻刻縈繞於心。揮之不去的瘋狂。妄念。就算失敗了又如何?總比什麼事都沒做過還來得好。
癡迷而迫切的盼望,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筆者便在二〇一六年夏季開始策畫一項小說合作的寫作藍圖,想邀請同樣喜愛歷史的作家們,齊心協力,創造出以「歷史和文學」為主軸的合作小說。
很幸運的,能夠陸續邀請到四名文采斐然的作家,共同參與這項有趣企畫。四位作家各有別樹一幟的創作風格:
楊双子,作品《撈月之人》、《花開時節》書寫柔美溫暖的女性情誼。
陳又津,在《少女忽必烈》、《準臺北人》,以輕筆承載臺北城的重量。
瀟湘神,以《臺北城裡妖魔跋扈》架構奇幻史觀,融合推理與民俗。
盛浩偉,《名為我之物》,文筆切剖自我,思索個人與城市的當代價值。
能有這個契機來合作,我們五人都很欣喜。本來以為聯絡將會繁瑣,但往來過程卻一拍即合,彼此聯繫極為順利。
在網路聊天室裡,我們初步有了一些共識,例如,在歷史和文學的主軸上,我們希望將這本小說集的主題,聚焦於「臺灣日治時期」與「藝文界」,企望能以嶄新視野,書寫出截然不同的時代故事。
至於在形式上,我們決定先行討論出一個共通的世界觀,然後在這個大架構之下,每人再各自發展一個中短篇小說,最後集結五篇故事編成一部完整小說。
不久之後,我們便約定在九月二十四號第一次碰面,在臺北古亭的義式屋古拉爵聚餐,討論詳細計畫。
仲秋夜圓桌會
「我想分享一個有趣作品,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小說接龍!」
在古拉爵的角落桌位,一開頭瀟湘神的提案就讓眾人精神振奮,他所舉例的作品是刊登在二〇〇四年的日本雜誌《浮士德》第四期的小說〈對誰來說都不連續〉(誰にも続かない),這部作品就是多位作家以小說接龍所完成的創作。
為什麼會有這部作品呢?其實這是來自《浮士德》的企劃,當時編輯部邀請乙一、北山猛邦、佐籐友哉、瀧本龍彥、西尾維新五位小說家參加在沖繩舉辦的「文藝合宿」,為期四天三夜。每個人除了要繳交一篇小說,更要以小說接力賽方式,共同完成一部小說。
這種具備挑戰性的創作模式,即刻獲得眾人點頭肯定。若只是各自寫各自故事,合作意義將大打折扣。不過若以故事接龍的方式進行,除了能夠增強整體感、連結彼此情節,更能讓不同作家在串聯故事時激盪出意外的火花。
「意外性」與「遊戲性」也是我們這一次「文藝合作」殷殷盼望的目標。
儘管決定故事接龍的創作方式,但是最重要的主線情節,又該如何確定?
正當眾人膠著之際,盛浩偉提及前幾日翻閱的書中,曾讀過一段有著謎題的段落:「那是來自〈郭松棻訪談錄〉的段落,呂赫若逃亡前,曾將一串鑰匙交給膠彩畫家郭雪湖,也就是郭松棻的父親。不過,郭松棻始終不知道那串鑰匙有何作用。」
在盛浩偉的介紹下,夥伴們皆震撼於鑰匙的神祕存在。這串鑰匙從何而來?又有何用途?
這則故事的懸疑感在我們心中鏤下深刻印象,我們隨即一致認同,很適合作為我們故事的核心主線,甚至可以將這則段落,引文作為我們小說合輯的卷首語。我們五人的創作,將圍繞這串鑰匙依序前進。
接下來的工作便簡單了,我們開始擬定基本的合作規則,確保彼此小說的連貫方式,並且分配故事接龍的創作順序與完工時程。最終決定的順序如下:
何敬堯→楊双子→陳又津→瀟湘神→盛浩偉。
每人寫作時間大約兩個月,一個篇章接續下個篇章,依序完成,預定隔年夏季將串連成一部完整作品。
華麗島與鍵
這一卷是,我以深摯的感情,
獻給曾經允許我居住過、生活過,
使我愛上的臺灣
――華麗島的小說集。
《西川滿小說集》(春暉出版社)
初次認識西川滿,是在碩士班一年級的課堂。西川滿對於臺灣文化的熱情以及毀譽參半的文學生涯,瞬間引起筆者的好奇心。越是深入理解西川滿的創作,越對於他所開創的文藝風格深深著迷。從此之後,西川滿的創作觀與美學理念不時迴盪於筆者心中。
因此,在古拉爵的圓桌會議之前,筆者便已經先擬定故事主角之一會是以西川滿作為取材的對象。不過,如同《文豪野犬》的大膽創意,筆者更冀望能夠跳脫史料之外,以西川滿為原型,為角色塑造出另一種迥然不同的形象。
圓桌會議上,夥伴們也相繼提出想書寫的人物、主題,雖然各自關注焦點相異,但我們的熱情卻是毫無二致,越燒越焰。我們期盼這部作品的實驗,能激發出意想不到的妙異火光。
儘管如此,我們的書名卻遲遲未決定。直至二〇一七年八月初,最後的篇章即將完成之前,經過反覆討論,我們決定將這部實驗性質濃厚的小說書名定為「華麗島軼聞」。
華麗島,光之源,是我們居住的臺灣島。西川滿自東京早稻田大學法文科畢業後,便決心返回魂牽夢繞的臺灣,視臺灣為第二故鄉,歡喜華麗之島。終其一生,西川滿創作皆圍繞臺島民俗歷史,「華麗島」一詞也因他的憧憬、歌頌而為人熟知。
此部小說開篇以西川滿作為取材對象,全輯故事幾乎以日治時期為舞臺,故以「華麗島」一詞鑲入書名,致敬這一段風華瑰麗的鯤島年代。
副標題則定為「鍵」(かぎ)。在日文中,「鍵」指稱鑰匙,也是此部小說主線情節會出現的重要物件。
此部小說不僅僅是個人的想像,更因眾位夥伴而成型。圓桌之前,我們的位置平等,我們的夢想一致。感謝夥伴們這幾個月以來協心戮力,筆者在此深深鞠躬。
感恩感謝。
華麗之島,時代遞嬗,這一串輾轉流傳的神秘鑰匙,將開啟何種故事?
華麗時代的圓桌會
◎何敬堯
從二〇一三年開始連載的漫畫《文豪野犬》,朝霧カフカ原作、春河35作畫,以「日本文學家」擁有「超能力」的人物設定,讓這些異能者在日本橫濱展開超能力大戰。這部異想天開的作品極為熱門,甚至有了小說、動畫等聯動創作。
諸如中島敦、芥川龍之介、與謝野晶子等知名作家與其作品,皆是取材對象。例如名喚太宰治的角色,他的異能力稱為「人間失格」,能憑接觸就讓對手的異能無效化。
故事設定很大膽恣意,但轉念一想,這種靈活多變的創作,是否也為日本文學家的形象增添更趣味的觀點?
新時代的想像
純文學一向不是日本年輕人的閱讀首選,可是當出版社將太宰治的《人間失格》與中島敦的《山月記》書封換成了春河35繪製的帥氣人像,銷量大幅提升,許多年輕讀者藉此踏入純文學世界。日本向來擅長利用漫畫作品振興觀光,所以當「與謝野晶子紀念館」在二〇一六年與《文豪野犬》合作之後,館方也驚訝發現,本來大多是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參觀者,展覽期間的中小學生參觀人數,竟是去年十倍以上。
文學,能不能有更多不可思議的想像?
日本創作者能以多變觀點翻轉文學形象,這種「改編」的能力,是從日本習以為常的歷史改編創作而來。不管是小說、漫畫或電影,若涉及日本歷史,總會在正史以外創造全新的詮釋空間。
例如夢枕貘小說《陰陽師》,讀者津津樂道安倍晴明與源博雅的友情,但在史實,兩人是否相識卻有待考察。石井步的漫畫《信長協奏曲》,則讓現代日本人三郎與織田信長交換身分,重新演義戰國傳奇。
此種超脫史實的故事創作,正是日本文學中「時代小說」的重要特色。在小說分類上,歷史小說強調史實基礎,注重人物的真實與歷史事件的價值。不過在日本文學發展上,也有「時代小說」的存在。時代小說儘管也涉及歷史,但真實人物、歷史事件並非其核心,而是更側重於以古代為背景來撰寫新穎故事。若觀察當代中國、韓國的通俗文學,依循此理的歷史穿越小說正大行其道。
歷史,能不能有別開生面的創造?
文學與歷史的幻境
世界不一定只能從固定角度觀看,尋覓史實之間的罅縫,擊破既定印象的銅牆,在小說的泥壤上,文學與歷史的嫁接肯定能綻出與眾不同的花種。
猶如天馬行空的《文豪野犬》不斷刺激筆者心緒,回顧臺灣本身,也引發一項疑問:以臺灣歷史為舞臺的時代小說能不能更多?
臺灣島,千百年以來是原住民游耕游獵之地,十七世紀之後相繼接受西方人、漢人、日本人……各種文化的進入。不論是大航海時代抑或清國時代,不同的民族在相互抗衡、交流、融合的過程中,臺灣逐漸成為擁有多元特色的海島國家。而在日本時代的殖民史,臺灣文化、社會更加錯綜複雜。
臺灣島每一段歷史,曼妙風華無與倫比,皆為小說取材的靈感泉源。
島嶼中部的大肚王,曾統領一座龐大的平埔王國,熱蘭遮城的四角稜堡閃耀夕暉,沿岸的清國時代港口傳來漢族水手的吆喝,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展櫃中,藍地黃虎旗摹本兀自鋪展――隱藏在旗面底下的日夜雙面旗真相,還要等待一百年後才會揭曉。
臺灣島有著數不盡的軼事,每段歷史風華翩翩,是小說發想的珍寶庫。在臺灣歷史的轉折處,能否編織出萬花撩亂的幻境?
儘管只是個人荒誕的空想,儘管只是棉薄之力,卻時時刻刻縈繞於心。揮之不去的瘋狂。妄念。就算失敗了又如何?總比什麼事都沒做過還來得好。
癡迷而迫切的盼望,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筆者便在二〇一六年夏季開始策畫一項小說合作的寫作藍圖,想邀請同樣喜愛歷史的作家們,齊心協力,創造出以「歷史和文學」為主軸的合作小說。
很幸運的,能夠陸續邀請到四名文采斐然的作家,共同參與這項有趣企畫。四位作家各有別樹一幟的創作風格:
楊双子,作品《撈月之人》、《花開時節》書寫柔美溫暖的女性情誼。
陳又津,在《少女忽必烈》、《準臺北人》,以輕筆承載臺北城的重量。
瀟湘神,以《臺北城裡妖魔跋扈》架構奇幻史觀,融合推理與民俗。
盛浩偉,《名為我之物》,文筆切剖自我,思索個人與城市的當代價值。
能有這個契機來合作,我們五人都很欣喜。本來以為聯絡將會繁瑣,但往來過程卻一拍即合,彼此聯繫極為順利。
在網路聊天室裡,我們初步有了一些共識,例如,在歷史和文學的主軸上,我們希望將這本小說集的主題,聚焦於「臺灣日治時期」與「藝文界」,企望能以嶄新視野,書寫出截然不同的時代故事。
至於在形式上,我們決定先行討論出一個共通的世界觀,然後在這個大架構之下,每人再各自發展一個中短篇小說,最後集結五篇故事編成一部完整小說。
不久之後,我們便約定在九月二十四號第一次碰面,在臺北古亭的義式屋古拉爵聚餐,討論詳細計畫。
仲秋夜圓桌會
「我想分享一個有趣作品,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小說接龍!」
在古拉爵的角落桌位,一開頭瀟湘神的提案就讓眾人精神振奮,他所舉例的作品是刊登在二〇〇四年的日本雜誌《浮士德》第四期的小說〈對誰來說都不連續〉(誰にも続かない),這部作品就是多位作家以小說接龍所完成的創作。
為什麼會有這部作品呢?其實這是來自《浮士德》的企劃,當時編輯部邀請乙一、北山猛邦、佐籐友哉、瀧本龍彥、西尾維新五位小說家參加在沖繩舉辦的「文藝合宿」,為期四天三夜。每個人除了要繳交一篇小說,更要以小說接力賽方式,共同完成一部小說。
這種具備挑戰性的創作模式,即刻獲得眾人點頭肯定。若只是各自寫各自故事,合作意義將大打折扣。不過若以故事接龍的方式進行,除了能夠增強整體感、連結彼此情節,更能讓不同作家在串聯故事時激盪出意外的火花。
「意外性」與「遊戲性」也是我們這一次「文藝合作」殷殷盼望的目標。
儘管決定故事接龍的創作方式,但是最重要的主線情節,又該如何確定?
正當眾人膠著之際,盛浩偉提及前幾日翻閱的書中,曾讀過一段有著謎題的段落:「那是來自〈郭松棻訪談錄〉的段落,呂赫若逃亡前,曾將一串鑰匙交給膠彩畫家郭雪湖,也就是郭松棻的父親。不過,郭松棻始終不知道那串鑰匙有何作用。」
在盛浩偉的介紹下,夥伴們皆震撼於鑰匙的神祕存在。這串鑰匙從何而來?又有何用途?
這則故事的懸疑感在我們心中鏤下深刻印象,我們隨即一致認同,很適合作為我們故事的核心主線,甚至可以將這則段落,引文作為我們小說合輯的卷首語。我們五人的創作,將圍繞這串鑰匙依序前進。
接下來的工作便簡單了,我們開始擬定基本的合作規則,確保彼此小說的連貫方式,並且分配故事接龍的創作順序與完工時程。最終決定的順序如下:
何敬堯→楊双子→陳又津→瀟湘神→盛浩偉。
每人寫作時間大約兩個月,一個篇章接續下個篇章,依序完成,預定隔年夏季將串連成一部完整作品。
華麗島與鍵
這一卷是,我以深摯的感情,
獻給曾經允許我居住過、生活過,
使我愛上的臺灣
――華麗島的小說集。
《西川滿小說集》(春暉出版社)
初次認識西川滿,是在碩士班一年級的課堂。西川滿對於臺灣文化的熱情以及毀譽參半的文學生涯,瞬間引起筆者的好奇心。越是深入理解西川滿的創作,越對於他所開創的文藝風格深深著迷。從此之後,西川滿的創作觀與美學理念不時迴盪於筆者心中。
因此,在古拉爵的圓桌會議之前,筆者便已經先擬定故事主角之一會是以西川滿作為取材的對象。不過,如同《文豪野犬》的大膽創意,筆者更冀望能夠跳脫史料之外,以西川滿為原型,為角色塑造出另一種迥然不同的形象。
圓桌會議上,夥伴們也相繼提出想書寫的人物、主題,雖然各自關注焦點相異,但我們的熱情卻是毫無二致,越燒越焰。我們期盼這部作品的實驗,能激發出意想不到的妙異火光。
儘管如此,我們的書名卻遲遲未決定。直至二〇一七年八月初,最後的篇章即將完成之前,經過反覆討論,我們決定將這部實驗性質濃厚的小說書名定為「華麗島軼聞」。
華麗島,光之源,是我們居住的臺灣島。西川滿自東京早稻田大學法文科畢業後,便決心返回魂牽夢繞的臺灣,視臺灣為第二故鄉,歡喜華麗之島。終其一生,西川滿創作皆圍繞臺島民俗歷史,「華麗島」一詞也因他的憧憬、歌頌而為人熟知。
此部小說開篇以西川滿作為取材對象,全輯故事幾乎以日治時期為舞臺,故以「華麗島」一詞鑲入書名,致敬這一段風華瑰麗的鯤島年代。
副標題則定為「鍵」(かぎ)。在日文中,「鍵」指稱鑰匙,也是此部小說主線情節會出現的重要物件。
此部小說不僅僅是個人的想像,更因眾位夥伴而成型。圓桌之前,我們的位置平等,我們的夢想一致。感謝夥伴們這幾個月以來協心戮力,筆者在此深深鞠躬。
感恩感謝。
華麗之島,時代遞嬗,這一串輾轉流傳的神秘鑰匙,將開啟何種故事?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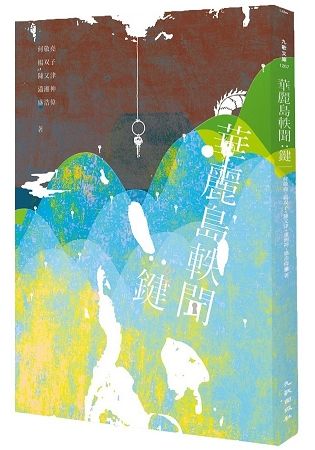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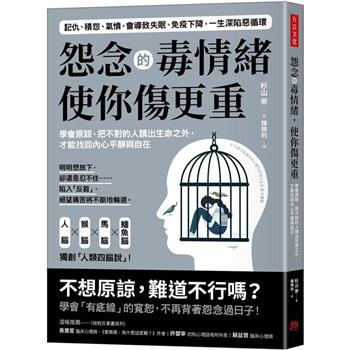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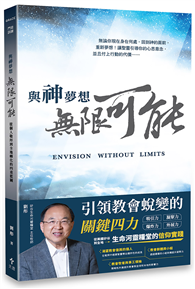







很久沒有接觸到台灣文學的我,在當初看到這本書的企劃同時,便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個時間翻來看看。雖然五位作家大概只認識兩位,但就是這兩位讓我不至於對這本書卻步,他們就是何敬堯和瀟湘神。 敬堯早在《幻之港》時透過朋友的介紹下而認識,知道他對於台灣妖怪和歷史小說很有想法,而他也勇於實踐一本推理小說一本歷史小說的步調,讓讀者從作品知道他對於台灣所投注的情感, 因此吸引了我對於他作品的期待。 瀟湘神在還未見過面的情形下,印象中是個神祕人物,只知道他是奇幻小說作者,並且透過實境遊戲,藉由角色的自由發揮,達成遊戲的目標。亦是透過友人對於他將整個遊戲集結成書,更讓我更加好奇了。在一次講座下,得知他會用遊戲方式主要原因是為了地方意識。用奇幻的角度來結合當地歷史文化,光是這點就讓我想支持他的想法。這兩位作家的理念和我的想法竟如此貼合。 至於其他三位作家,尚未拜讀過他們的作品,但在看完這本書之後,這些作者的確是一時之選。 《華麗搗軼聞:鍵》五位作者分屬的部分頗為精妙。以敬堯作為第一棒,開啟了整個故事的謎團。用「天狗」和「聽香」破解大家族的詛咒,將故事主題「鑰匙」秀出。楊双子的二棒,脫離不了奇幻,以「鬼」為主體,講了另一家族的故事,寫出作者擅長的歷史百合故事,點開「鑰匙」的來源。陳又津不僅反了前者, 也在角色上從百合一下變成BL的情節,「鑰匙」的流轉去向,吸引著讀者的目光。瀟湘接替四棒,把前三篇作了個完整的整合,不僅破解了謀殺案也把整個故事的大謎團一舉道破。看到這裡,為後面的作者捏了一把冷汗。「起」「承」「轉」「合」都有了一定位置,沒想到作者用了「後設」方式來完成,實在太精采了。 合著作品總是困難,尤其是面對著同一個主題時,形成作者和作者間的競作,彼此用文筆來一較高下,如後記所說的「是否有想要陷害下家的時候」。假如說作者沒有陷害,那肯定逼不了另一位使出渾身解數的功力,讀者也不能趁此之便看到完成度更高的作品。而且雖然自己陷害不用收尾的確會讓上家可以盡其所能的迫害,可是下家的見招拆招的功力的確在《華麗搗軼聞:鍵》無庸置疑的好。我認為這不僅是因為作者彼此功力旗鼓相當,更是因為他們對於主題的熟識度、敏感度高才能完成,開始忍不住期待續集作品推出了!很久沒有接觸到台灣文學的我,在當初看到這本書的企劃同時,便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個時間翻來看看。雖然五位作家大概只認識兩位,但就是這兩位讓我不至於對這本書卻步,他們就是何敬堯和瀟湘神。 敬堯早在《幻之港》時透過朋友的介紹下而認識,知道他對於台灣妖怪和歷史小說很有想法,而他也勇於實踐一本推理小說一本歷史小說的步調,讓讀者從作品知道他對於台灣所投注的情感, 因此吸引了我對於他作品的期待。 瀟湘神在還未見過面的情形下,印象中是個神祕人物,只知道他是奇幻小說作者,並且透過實境遊戲,藉由角色的自由發揮,達成遊戲的目標。亦是透過友人對於他將整個遊戲集結成書,更讓我更加好奇了。在一次講座下,得知他會用遊戲方式主要原因是為了地方意識。用奇幻的角度來結合當地歷史文化,光是這點就讓我想支持他的想法。這兩位作家的理念和我的想法竟如此貼合。 至於其他三位作家,尚未拜讀過他們的作品,但在看完這本書之後,這些作者的確是一時之選。 《華麗搗軼聞:鍵》五位作者分屬的部分頗為精妙。以敬堯作為第一棒,開啟了整個故事的謎團。用「天狗」和「聽香」破解大家族的詛咒,將故事主題「鑰匙」秀出。楊双子的二棒,脫離不了奇幻,以「鬼」為主體,講了另一家族的故事,寫出作者擅長的歷史百合故事,點開「鑰匙」的來源。陳又津不僅反了前者, 也在角色上從百合一下變成BL的情節,「鑰匙」的流轉去向,吸引著讀者的目光。瀟湘接替四棒,把前三篇作了個完整的整合,不僅破解了謀殺案也把整個故事的大謎團一舉道破。看到這裡,為後面的作者捏了一把冷汗。「起」「承」「轉」「合」都有了一定位置,沒想到作者用了「後設」方式來完成,實在太精采了。 合著作品總是困難,尤其是面對著同一個主題時,形成作者和作者間的競作,彼此用文筆來一較高下,如後記所說的「是否有想要陷害下家的時候」。假如說作者沒有陷害,那肯定逼不了另一位使出渾身解數的功力,讀者也不能趁此之便看到完成度更高的作品。而且雖然自己陷害不用收尾的確會讓上家可以盡其所能的迫害,可是下家的見招拆招的功力的確在《華麗搗軼聞:鍵》無庸置疑的好。我認為這不僅是因為作者彼此功力旗鼓相當,更是因為他們對於主題的熟識度、敏感度高才能完成,開始忍不住期待續集作品推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