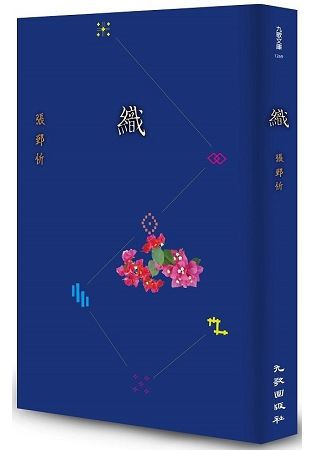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織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24 |
小說 |
電子書 |
$ 224 |
小說 |
$ 253 |
現代小說 |
$ 253 |
10~12月 |
$ 253 |
中文現代文學 |
$ 270 |
小說/文學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小說 |
$ 288 |
小說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家不僅是經緯交錯的座標,也是開放延展的地圖。
將細瑣的家族故事以巧思重新架構,虛實交錯地織出了一張緻密的時代與人生之網……
台灣在一九五〇年代曾經是紡織王國,紡織廠經歷興衰、外移、轉型等,然而目前也尚未出現以紡織為主題的小說,這部小說寫出祖父從台灣到越南的移動,也考察了台灣和越南紡織業交織的一段歷史切片。
主角卉玲正值失業與就業間的徬徨時期,病重的阿公在她某日出門求職後在家中斷氣,錯過見阿公最後一面的她開始陷入多重的迷惘,之後她和家人陪伴阿婆再遊越南,當年阿婆以眷屬身分去探望阿公的場景路線和回憶一一重現,故事就在現在進行式的阿玲觀點、年輕阿公的異鄉心情,以及遠道去探望丈夫的年輕阿婆的越南行經歷,三大視角間交錯進行。
作者張郅忻從小在客家庄長大,阿公阿婆說客語,小嬸說印尼語,大嬸嬸說越南語,妹妹有阿美族血統,生活週遭也有不少越南好姐妹,她過去的作品即十分關注不同出身背景的台灣新移民族群,描繪出多元族群女性和與她們相互對照的生命故事,也打破多數台灣人對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這次,源於對曾於上世紀六、七〇年代的越戰時期被派遣到越南紡織廠工作的祖父生命歷程及家族命運的好奇,張郅忻動念尋根,並提筆創作小說。除了家族史及紡織業歷史外,作者也希望從整理歷史脈絡中,看見新移民的移動,以及在當代台灣家庭中的身影和生命力。《織》以虛擬本質的小說形式為主體,搭配口述歷史與實際走訪台灣及越南胡志明市紡織廠的方式蒐集資料,圍繞紡織、家族、記憶三個子題展開書寫。
如同張郅忻過去的散文風格,不見華麗的詞藻或比喻,卻處處真情流露。小說的敘事也自然細膩卻毫不拖泥帶水,細瑣的家族故事以巧思重新架構,虛實交錯地織出了一張緻密的網,不論是曾在越南打拚時陪伴阿公的紅粉知己,還是在台灣默默守候並養大五個孩子們的阿婆,時代的變遷走來,有生離,也有死別,家族間的羈絆,人生的無奈與不捨,情真意切地娓娓道來,許多段落皆讀來令人感同身受,揪心動容。
本書特色
★ 台灣首部交織台灣與越南紡織故事的小說
★ 作者蒐集口述歷史並實際走訪台灣及越南胡志明市紡織廠,圍繞紡織、家族、記憶三個子題展開書寫
作者簡介
張郅忻
生於新竹。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生命中往返流動的軌跡。曾於人間福報副刊撰寫專欄「安咕安咕」,蘋果日報專欄「長大以後」。著有《我家是聯合國》、《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