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相愛的日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82 |
小說 |
電子書 |
$ 182 |
小說 |
電子書 |
$ 182 |
小說 |
$ 205 |
現代小說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文學作品 |
$ 205 |
中文現代文學 |
$ 221 |
小說/文學 |
$ 229 |
小說 |
$ 234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被稱著愛情的東西在男人與女人之間瘋狂地穿梭,宛如水藻間的塵芥遭攪拌後重新分離與吸附,世界像魚眼中的海底一樣混沌。〈火車裏的天堂〉婚姻成了現代人的替罪羊,當我們否定了自我的時候,我們金蟬脫殼,拿生命的環結誤作自我革新與自我出逃。〈沒有再見〉成了丈夫的妻子、兒子的媽媽的林康,僅有的一點樂趣是每月十號端詳人民幣上好看的微笑。
〈與黃鱔的兩次見面〉給人生來個重新啟蒙,歲月裏堵塞的百結愁腸,似乎開始了一種渙然冰釋,看似解放了,但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幹什麼。〈與阿來生活二十二天〉阿來像水把自己裝在想像的瓶子裡,瓶子的造型就是她的造型,她心中可以裝滿千百種女人,唯獨沒有她自己。〈五月九日和十日〉看凡人在二度婚約裡熱中表現出輕鬆、自然與大度,但實際是撐不住,累透了。
本書為畢飛宇短篇小說系列之三,銳利地透視「城市」熱鬧喧囂卻也灰燼處處一派荒涼。就如畢飛宇透過故事主人翁道出:人的一生,就像人在旅途。其實上哪兒去並不要緊,重要的是,在哪兒都必須生活。強大的文字、輕盈的細節,畢飛宇一腔熱情關注糾纏在生活中,無處脫逃的人物,文字鬆弛有度圓融飽滿,故事情感走向引人入勝,足以滿足讀者無限的閱讀期待。
★ 畢飛宇短篇小說系列之三,系列以「城市」、「鄉村」做主題劃分,此為「城市」系列第二部。
作者簡介
**畢飛宇 ** 一九六四年生於江蘇興化。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教師,後從事新聞工作。八○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文字敘述鮮明,節奏感掌握恰到好處。曾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百花文學獎、郁達夫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 著有《玉米》、《青衣》、《平原》、《造日子》、《推拿》、《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大雨如注》、《充滿瓷器的時代》等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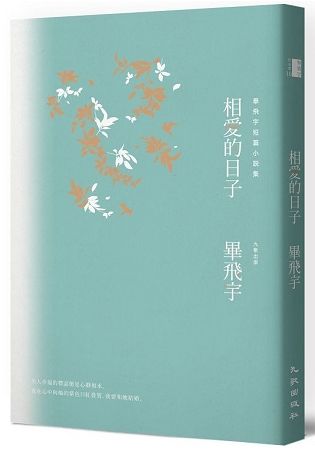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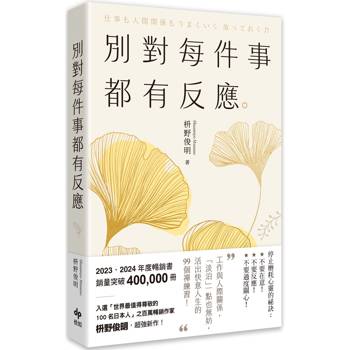

![114年國文──多元型式作文攻略(記帳士版)[記帳士] 114年國文──多元型式作文攻略(記帳士版)[記帳士]](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214)